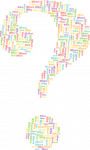中国大反动的衰亡:支持国度主义派和对甲寅派、古代评论派的批判

中国大革命史
第二章大革命的兴起
第七节反对国家主义派和对甲寅派、现代评论派的批判
一、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
“五卅”运动前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同时,也进行了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
国家主义派是地主买办阶级的政治代表,是由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等反动分子组织指挥的极端反革命的政治派别。1922年12月2日,曾琦、李璜等在法国巴黎成立中国青年党,是这个政治派别形成的标志。由于这个组织的名称长期保密,对外活动一直以“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的名目出现,又标榜所谓国家主义,故人们称它为国家主义派。1924年秋,他们开始在国内建立组织,并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作为反革命宣传的主要工具,开展所谓醒狮运动,敌人们又称之为“醒狮派”。
在初期,国家主义派把活动的中心放在法国,竭力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周恩来等旅法中国共产党人,在《少年》、《赤光》等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批驳了他们的谬论,“使国家主义派在勤工俭学学生中完全孤立。进步分子都紧紧围绕在党的周围”。1924年国共合作成立以后,曾琦一伙“预料国内的共产活动必日益加强”,他们“以哀者的心情,抱勇士赴难的决心,准备回国与国际共产党奋斗到底”,“以对付国际共产党在中国的动乱”。从1924年秋起,曾琦等陆续回国,把其活动中心从国外转移到国内。“五卅”运动后,他们在《醒狮》周报等刊物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并发行书籍30余种,到处讲演,扬言要“宣传和平的自卫的国家主义,举该党(指共产党)一切似是而非的邪说,摧陷而廓清之,使之在理论上直无立足之余地”。国家主义派宣扬的谬论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否认我国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他们说,“中国旧式的封建阶级已因政治的平民化而早已消灭,新式的资产阶级又因产业落后而无从发达,因此,中国根本无发生阶级分化及对抗的可能”。污蔑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是“削足适履”,使“本来谐和之各界人士,必因之而大起斗争,驯至社会秩序骚然”,“减杀对外之战斗力”。主张在国家主义旗帜下,“一致趋赴,协力图强”,进行“全民革命”。
2.在国家问题上,宣扬超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观,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说,“国家不是任何人、党派或阶级的工具,而是全民所共同托命的一个总体”,其作用在于“用实力以拥护道德”,“谋群众生活,防止阶级斗争”,“只有全民政治,才能实现国民政治机会均等,经济生活的均等”。主张维护打着共和招牌的北洋军阀政权,“以奠定国基”。
3.在对外关系问题上,宣扬“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非我族类岂得为友”的资产阶级狭隘民族主义,“不赞成依人为活的国际主义”。污蔑社会主义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把孙中山的联俄政策说成是“引狼入室”。他们反对中国人民进行反帝斗争,说“空唬几声打倒帝国主义,不惟表示国民浮浅无知,对于国事没有相当的步骤,反足引起外人的嫉心,一致谋我”。
4.盗用“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反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他们的所谓国贼,就是指领导中国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中国共产党;所谓“强权”,就是指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苏联。他们把中国积弱不振的原因归罪于中国共产党的“倡乱”、“亲俄卖国”和苏联的“侵略”,叫嚷“一刀两断用武力铲除共产党人”。
国家主义派同国民党右派狼狈为奸,疯狂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积极从事反共反苏反革命活动,充当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帮凶走狗,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忠实的弁护士。但由于他们打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幌子,以全民革命、全民政治相标榜,摇唇鼓舌,大造舆论,确曾使一些无知与落后的青年受骗上当。
为了肃清国家主义派的流毒,宣传马克思主义,促进革命运动的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在《新青年》、《中国青年》和《政治周报》等刊物上发表大量文章,对国家主义派的反动谬论和反革命罪行,进行了全面的揭露和严肃的抵制。
1.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批判国家主义派否认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谬论。肖楚女在《显微镜下之醒狮派》一文中指出:只要“私有财产制不废除,资本生产制不改变——一切生产机关不公之于社会而为私人所占有时,阶级是自然要生产出来,而且要分化发展得愈明显的”。他列举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以及工人反抗斗争的大量事实说明,中国和外国一样,不但存在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而且劳资阶级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和斗争。这是每个妇孺都知道的事实,醒狮派却“故意装做不见”,反而“硬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所鼓吹的”。肖楚女质问他们:“醒狮派既言国内尚没有阶级,则又何畏他人之主张阶级斗争?既言尚无资本家,则又何劳醒狮派为资本家着急?”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精辟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同的阶级和阶层,并指出由于它们所处的经济地位的不同,所以对待革命的态度也是各异的。这就从理论和实践上戳穿了国家主义派否认我国当今社会存在着阶级分化和阶级对立的谰言。
对国家主义派宣扬阶级合作、“全民革命”的反动实质,共产党人也作了深刻的揭露,指出这是国家主义派企图使无产阶级“甘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而不努力谋自己阶级利益的斗争”,“使得每个被压迫者,都成为很驯服的甘被剥削者”。这“正足以见他们完全只代表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充当剥削制度的卫道士。共产党人还指出,国家主义派并非反对一切阶级斗争,他们反对的只是工农群众反对地主、资本家的阶级斗争;面对于反革命的阶级斗争,他们不但不反对,而且是狂热的鼓吹者和参加者。他们的全部反革命言行,“正足以见得他们从事于‘阶级斗争’,站在资产阶级地位来反对工人的阶级斗争”。
2.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驳斥国家主义派鼓吹“全民国家”,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肖楚女指出:“阶级一日存在,阶级斗争便一日不会消灭;国家也便一日不得不被有力阶级——得胜阶级用为工具。有产阶级专政,是用国家这个东西保持自己的地位,役使他人——使阶级继续存在。无产阶级专政,是使生产社会化,废除私有财产,将一切生产工具归之于社会公有——使阶级消灭”。国家主义派否认国家的阶级性,宣扬所谓“均平利益”的“全民国家”,纯属欺人之谈,在现实阶级社会中是根本不存在的,“只要拿《醒狮》不及《向导》受摧残之甚和醒狮人不及共产党人有生命的危险二事看,就足够证明国家是‘阶级的’了!”在当今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又有哪一国不是在德谟克拉西面目之下,实行第三阶级——资本主义的专政?
共产党人认为,既然没有超阶级的国家,自然也就无所谓超阶级的爱国思想。恽代英说:“我们心目中的国家,是为了抵御国际资本主义压迫而存在的,我们要全民族自爱自保,是为要使全民族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压迫之下解放出来;要求全民族解放,我们自然更要注意力求那些最受压迫而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工阶级的解放”。国家主义派“提倡那种空洞与实际生活无关的爱国精神”,无非是“想拿这种爱国的空话欺骗无产阶级,妨害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他们真正所爱的“国”,乃是北洋军阀政府,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不但不爱,并非把它推翻不可。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领导人民,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去推翻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以无产阶级为中心组织新国家”,建立“国民革命的革命派的独裁制”。
瞿秋白在驳斥国家主义派捏造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阶段就要搞“一阶级专政”、实行“共产”的谎言时指出:“共产党在国民革命时代并未主张无产阶级独裁制,这是谁都知道的”,他们这种攻击,“和其他攻击一样故意自制其‘共产主义政策’来做对象,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在理论上驳难共产主义政策的能力,所以只好以造谣的伎俩来中伤”。
3.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驳斥国家主义派鼓吹资产阶级
狭隘民族主义,破坏反帝斗争的谬论。共产党人指出,由于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野蛮侵略,不论哪一个国家,只要发生反帝斗争,它就必然“是世界革命运动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因此,“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革命运动,亦不能脱离国际的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相互间之公友公敌的关系而单独发展”。
同样,“中国国民革命必须联合被压迫民族,必须联合无产阶级共同作战,才能有充分的革命力量”。肖楚女用“五卅”运动时各国无产阶级积极援助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大量事实,驳斥国家主义派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非我族类岂得为友”的谬论。
共产党人在驳斥国家主义派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污蔑时指出:
苏联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它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在于“扶助中国民众消灭帝国主义在华的势力并发展民众的革命实力,使中国达到独立与自主的成功”。正因为如此,“中山先生才诚心信俄”,“而欲与之一同来革命”。国家主义派攻击孙中山的联俄政策是“引狼入室”,其用心是十分刻毒的。瞿秋白指出:
“帝国主义者所最恐惧的,便是中国民族与苏联联合战线,而国家主义派所最反对的,也是这一联合战线;大家想想,他们对于帝国主义的功劳多么大!”
4.揭露国家主义派标榜“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口号的反动实质。共产党指出,“醒狮派的外抗强权,是和段祺瑞的“外崇国信’一样的”,是只反苏而不反帝的,因为他们主张“对于外国一切之现成条约,均照旧遵守”,公开声称世界上不存在“国际帝国主义”,甚至叫嚷“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一语,含有干涉他国内部组织之意”。他们所说的“内除国贼”,也是只除共产党而不除军阀的。共产党人认为,国家主义派如此疯狂地反对共产党,成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御用的“单打最革命的共产党的镖手”,是毫不奇怪的,这正是共产党的光荣。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一文中说:“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买办阶级土豪劣伸、安福系、研究系、联治系、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政派。这些敌人,跟着我们政治势力的发展而增强对于我们的压迫,调动他们所有的力量,企图消灭我们”。这是因为“他们唯恐中国革命运动因中国工农及其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之参加而有快的发展,所以拼命的反对共产党”,为的是“维持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政治统治”。国家主义派实际上是卖身投靠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充当其反革命鹰犬。北伐期间,余家菊投在孙传芳门下当金陵军官学校教务长,替孙传芳制定过“三爱主义”;曾琦则斩头分尸的改名王奇,往来宁济之间,参加孙传芳的机要,并为张作霖造过“四民主义”。他们竭力反对中国人民进行北伐战争。当北伐开始胜利进军时,他们就恐吓革命人民说,若北伐军进抵长江流域和华北一带,必然要引起英、日等国的干涉,并编造北伐必败的理由。及至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整个北洋军阀统治发生根本动摇时,他们又演出一场“拥护五色国旗运动”的闹剧。
纵观国家主义派的全部反革命言行,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剖析了它的阶级本质及其反动性。他们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中国,大地主资产阶级“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
国民党左派也参加了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1926年10月1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了《反对国家主义派命令》,指出国家主义派“甘受帝国主义者与军阀官僚豢养,对于本党主义及国民政府之设施,日事诬蔑破坏”,“近且于我国国民革命军势力进展中原之际,益加狂妄,为彼主人帝国主义者张目,倘再优容,其流毒不知伊于胡底”,要求各级党部、党报一致努力反攻,以期扑灭邪说。
在同国家主义派斗争中,共产党人注意区别对待,讲究斗争策略。对其反动头子进行无情揭露,坚决斗争;而对被蒙蔽的青年群众则努力做好团结教育工作。使许多蒙蔽青年觉醒,纷纷声明抛弃国家主义和脱离其团体,有的还要求参加革命组织。
经过多年论战,国家主义派的反动面目彻底暴露了;全国工农革命运动的迅速发展和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更以无情的事实宣告了国家主义派的彻底破产。到1926年下半年,其声势便一落千丈,终于走上了分崩离析的穷途末路。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是大革命时期思想政治战线上的一场重大斗争,它以马克思主义的辉煌胜利而载入史册,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通过这场斗争:(1)中国人民更清楚地认识到,要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就必须分清敌我,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把革命进行到底;(2)既彻底孤立了国家主义派,又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和分裂革命统一战线的阴谋活动,从而维护了革命统一战线,保证了工农运动和北伐战争的顺利发展;(3)进一步广泛深入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锻炼、壮大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威望。
共产党人通过《向导》、《中国青年》、《政治生活》等刊物,批判现代评论派的谬论。针对现代评论派散布对关税会议的幻想,《政治生活》杂志发表文章指出:“政权旁落在媚外军阀的统治阶级手里,什么民众利益都谈不到,……什么自主都行不通,只有推倒旧政权,建立人民的政权,才能实现关税自主”。《中国青年》接连发表文章批驳胡适等人攻击反帝爱国运动的谬论,指出:爱国学生运动“是有目的、有组织、有领袖”的“群众运动”,决非受人“引诱”而“跟着大家去呐喊”;反帝爱国“民众运动之勃兴,根本的原因当然是军阀与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加紧”所至,“这种民众运动是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最大力量”,它使军阀“战心、寒胆”,“虽老牌的帝国主义者英吉利亦叫苦连天”。《中国青年》还揭露胡适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诱惑青年脱离革命运动的险恶用心,指出青年人若“不识世界潮流,不懂社会需要”,一味追求个人志趣,是决不可“铸造”成为“有用人才”的,将来也干不了真正的“救国事业”,告诫青年警惕胡适之类“指导者”用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拖我们青年和他一路下水。”
鲁迅在《语丝》、《莽原》、《猛进》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锋利的杂文,对现代评论派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深刻地揭露了他们充当帝国主义和军阀帮闲、叭儿狗的真面目。他说,胡适、陈源这帮伪君子,常以青年的“导师”、知识界的“领袖”自命,欺骗和愚弄“未经老练的青年”。其实,他们是“媚态的猫”,“比它的主人更厉害的狗”,是“吸人的血还要预先哼哼地发一通议论的蚊子”。他们的反动作用,正像“走在一群胡羊面前”的“山羊”一样,“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其目的是“把青年引向歧途”,“稳妥平静”地“循规蹈矩”地听凭反动派的驱使,“虽死也应该如羊”。鲁迅还指出:“他们是羊,同样也是凶兽;但遇见比它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它更弱的羊时便出现凶兽样”。为了揭穿胡适等人引诱青年学生脱离社会运动而去“整理国故”,埋头于故纸堆的骗局,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一文中写道:“少读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鲁迅对陈西滢、徐志摩这类“恶意闲人”用“流言”替军阀屠杀人民造舆论,却又装出“公允”、“局外人”的假脸孔,作了无情的揭露。他说:“谣诼”、“流言”,“本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它和事实对照,看上去是可笑的,但它造成的结果,“比刀枪更可以惊心动魄”。3月18日的惨案事件“死伤至于三百多人,这网罗之所以布成,其关键就全在于‘流言’的奏了功效”。鲁迅以锐利的笔锋击中了现代评论派的要害,使他们“露出了麒麟皮下的马脚”,让人们看清了这帮“流言家竟如此之下劣”和“阴险”。
这场短兵相接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锻炼了新文化队伍,促进了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鲁迅在这场斗争中,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了思想的伟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