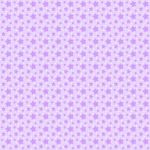太极·师伯(1)
阳光洒在四合院青色的屋顶上,不再是白花花的刺眼,而是把它普照之处都涂上一抹金色,这镶嵌金边的绿树,青瓦和新雨洗过的天鹅绒般的蓝天,加上天空随风悠然飘荡的几片闲云,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秋色图。

师伯坐在小院中的藤椅上,旁边放着一个方凳,登上摆着一个紫砂壶和一个茶碗,地上立着一个八磅大茶瓶,悠然地看着树梢上的白云。这画面和记忆中的很相似,不过坐在椅子上的是老父亲。
师伯家的“四合院”在老城州衙东北,解放前叫衙后街,解放后改名为四新街。这个院子也只是解放前是四合院,后来,翻身的主人把院子里的空地都盖成了低矮的草房,瓦房,从大门走进来,只剩一条两米来宽的路通到堂屋,沿着路便是一个挨着一个的矮房的简陋的门户。听奶奶讲,在以前,这个院子还有后面的院子都是他们胡家的,住的都是他们一家人,不过在他出生时,就只有这院子是他们家的了,父亲不仅把自家经营的运输公司交给了政府,也把后面的院子也交给了人民政府(也许是态度积极,在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他家受到的冲击都比较小),还把刚出生的儿子取名为“新生”。
如今,师伯(那个叫新生的孩子)已经年逾花甲,这人一上年纪,便总是恋旧:在他的记忆里,家在老城北关,出门约莫有二三百米就是学巷街小学,学校往西便是古时的州衙门(解放初期行政公署所在地),顺着政府前的胜利街往南走就是曾经的市中心——大十街;南大街,东大街,西大街都以此为界(因为有胜利街的存在,北大街不在大十街上,它是在东大街的小十街起往北的一条和胜利街平行的一条路)。不过,那里是商业中心,不是他儿时活动的主要区域,他的领地在家北面的护城河附近。在家和北城河之间有个“很大”的企业棉纺厂(大只是与周围的集体小厂和街办合作社相比,市里大型企业大都在西区的五一路上,像什么煤机厂,同发机械厂,通用厂,一内燃,微型电机,九六七六等),顺着厂东边的围墙有条小路,也就是二三百米(和到学校的距离差不多)就到了河边。那时的河边没有硬化绿化,长着高大的白杨树,一到夏天风起时,它便哗啦啦拍起手来;河边野草十分茂盛,夏天秋天能没过膝盖,那时可以割草,放羊;到了冬天,野草枯萎,铺在地上,就像毛毯一样,躺在上面,嘴里衔根草茎,晒太阳,是多么惬意的回忆呀。
河水很深(过去清理河道都是各个单位抽人做的义务劳动,当河水排干后,人们下到河底,一铁锨一铁锨把淤泥挖出来,甩到河堤上,这时你才知道河水满时,足足有几人深),河面上还没有现在“接天莲叶无穷碧”的映日荷花,只有深绿色的河水和觅食的白鹅和花鸭。因为每年都会淹死人(据老人讲,这些淹死鬼要托生,就必须要先找个替死鬼,把他拉到河里淹死才行),胆小的孩子都不去水里玩,只有大孩子才敢去钓鱼,游泳。记得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班上一个胆子大的叫国辉的孩子中午放学去河边玩水,一下子滑到河中心淹死了。他记得很真,那个同学被捞上来时,肚子滚圆,屁股里还夹着一截大便。
稍大后,他跟哥哥便去当时的郊外(现在的新区的市中心)三里桥捉鱼。那条河比城河看起来更大些,但水要比城河浅许多,而且水也更清些,站在岸边,可以看见水里哪里有鱼,然后就卷起裤腿下去抓鱼。在记忆里,三里桥很远,整个河上只有三座可以过车的大桥(两个公路桥和一座铁路桥),但现在这郊外的三里桥已经是穿市区而过,昔日荒芜的河坡摇身变成千亩游园,芳草如茵,树影婆娑,一到春天,鲜花满园,成了市区一道靓丽的风景。
三里桥的清河既然变成了城市的“内河”,便有许多桥跨在它身上来连接东西两部分城市。于是,在千亩游园,有七八座桥梁犹如一道道彩虹架了起来。昔日的荒草湖泊变成了游人如织的千亩游园,师伯也去过几次,想在那儿找个僻静的地方练拳,却发现那里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人,便莫名念起儿时清风徐徐,小河潺潺,树叶哗哗的青草地,在这闹哄哄的人为的绿地,他不能入静。
他跟师傅学拳后,晚上在学校的礼堂里练,白天怕红卫兵造反派撞见,就到护城河北岸的烈士陵园练。过了北大街的护城河桥,就是一所高中,高中后面则是烈士陵园,那里埋葬着100多位革命烈士,苍松翠柏,参天蔽日,除了清明各单位学校组织来扫墓外,平时少有人影。在那个文攻武卫的“革命”年代,“空气在颤抖,仿佛天空在燃烧”,而只有这里有难得的静,师伯就在这里静心揣摩拳术的奥妙。几十年后,他在花甲之年,勇擒歹徒后,有老邻居说他的功夫得力于少年时期在烈士陵园的修炼,还说那便是传说中的“阴阳双修”。他听后只是笑笑。唉!那个地方现在被旁边的中学占了(烈士陵园回来迁到市区,和另外一个陵园合并,并修建了雄伟的纪念碑),现在是中学的操场,希望那里的学子也能“阴阳双修”,锻炼出好身体。别说好身体,能少些近视眼就不错了。
茶淡了,壶里也快没水了。师伯把思绪拉回来,该做饭了。唉!家里少个女人还真不行,中午吃饭时盐就不多了,醋也没了。老伴没去上海儿子那里时,他从来就没操过这个心。
他关上屋门,走出院子。院子里面没什么变化,院子外早已是翻天覆地,他在北关的街道办的企业刃具厂上班的时候,老的州衙就扒掉了,在原址盖了威武雄壮的新的仿古州衙;等他去西面山里的煤矿做保卫科长时,州衙前的胜利街开始拆迁,听说要建一个大型的广场。每次从矿上回来,城市都在不停地换装,好在他住的那条街是个民族聚集区,更主要的是一个姓白的阿訇的亲家是省政府的高官,而拆迁问题又往往是现在社会中一个容易激化的矛盾点,所以,区里历任的领导都是来这里规划规划,却没人去真正执行这些拆迁建设的规划。至于附近的棉织厂和师伯以前工作的刃具厂都彻底改造了,棉织厂被拆了,在原址上修建了新的古城门和古城墙,刃具厂则改建成了一个规范的集贸市场。城区的好多地方都进行了拆迁改造,许多老街荡然无存,代之以各种特色的商业街和新的商业化小区。只是不知道那个魏胡同的“名人”傻花(在物质生活匮乏的年代,孩子们的精神生活也极其贫瘠,连追逐疯癫的傻花的怪异举动都成了一种娱乐。现在,只有傻子才有闲心去看傻花的。),她死后她的房子拆迁后在怎么处理的?他无端想起这个问题,觉得自己也有点不正常了,这是个什么问题呀?!
“晴空一鹤排云上”,秋是一样的秋,可在不同人的眼里,它可能悲寂寥,可能萧条肃杀,可能悲悲切切,也可能美胜春朝,一切都源自你的心情。其实,只要你的心够静,一年四季都能看得到风景,即使是在过去贫穷的年代,虽然没有人工修饰的园林美景,但师伯感觉到微风吹来的野草的清香,看小河欢快地流淌,鱼儿自由的游弋,他认为那是一种美。但今天的变化太快,如同汹涌澎湃的大潮,吞噬着旧有的一切,而人们则都以弄潮儿自居,不停地追逐着一浪高过一浪的潮头,很少有闲心来关注这周边的良辰美景。
就说开学季的秋高气爽,蓝天白云,这些接学生的家长都没有去注意,他们早早来到学校附近,从学校门口一直排到师伯家附近,他们嗅到的则是空气中的一丝不安:刚开学,多地连续发生几起针对中小学生的恶性事件,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学校也发出通知,希望家长有条件尽可能抽时间来接学生,另外学校也采取各种措施来预防不测事件。而师伯是不知道这些的,他只是觉得这乌泱乌泱的人群破坏了秋天的景色,在他眼里,只有秋与非秋的景别,却嗅不到空气中还藏有不安的味道,去小卖部还想着过去,想着跟“傻花”看洋景的事儿……
忽然,人群四散,被各种车辆挤占了一半的道路上,只剩下师伯立在路中间,前面有个人光着膀子挥刀砍车,没人敢上前制止。师伯已经六十出头,个子不高,一米七多点的样子,身材偏瘦;只见他上身穿灰色练功服,下穿灯笼裤,脚蹬黑布鞋,突然间只他一人站在路中间,一下子目标很大。
来人见有人在路中间挡道,便停止砍车,拿刀一指:“闪开!”
其实,师伯已经通过步伐判断了来人:步履踉跄,根基不稳,是一个情绪失控的无功的寻常之人。他一抬手:
“回家去吧,别惹事!”
在凝固的空气中,这不大的声音,中气很足,人们都听得很真。
“滚开!你个老不死的!”来人吼道。
不管什么原因,孩子们马上要放学了,师伯清楚,他不能躲避。他一动不动,大汉愣了一下:“还真有不怕死的老头!”然后,嗷的一声,举刀冲了过来。师伯一不躲,二不闪,垫步拧腰迎了上去,身子依然到了大汉的侧面,他一手抓住大汉的腕子,一手托住他的肘部,然后轻轻一捋,往下一按,大汉顿时失去重心,往前趴去。如果仅仅是小流氓,只需下面腿一伸,脚一绊,把他摔出几米远,来个嘴啃泥就行了。可今天来人手持凶器,情绪失控,他便在大汉前扑之时,松开右手,化作立掌,顺着来人右臂直接封喉。其实不用使太大力气,仅大汉一二百十斤的体重和他往前的冲力,就让来人吃不消的。只见大汉白眼一翻,顿时倒在地上,等他再睁开眼,已经被赶过来的学校保安和一些家长,牢牢地用特制的防暴工具控制住了。
警察赶来,师伯早已不见踪影,他不爱凑热闹,出风头。可在他家附近,他如此漂亮地出手,见义勇为,民警还是很快找到了他,录了笔录。不过,报社,电视台这些媒体再来寻他时,他已经去了上海的儿子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