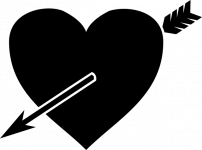李汉荣散文,让心灵回归到纯和中去(三)
有人说他的散文有着鲜明而浓郁的诗化倾向,那是对自然、历史、文化、深层面内涵的叙写。有人说他的散文能带着我们的思想穿越生存现场,触摸那些旧日被掩埋的诗意世界。

李汉荣一个普通的名字,可是这个普通名字背后的文人,却在用他毕生的心血书写着中国那些渐远的思想情怀,无论是山水田园、还是乡村民间;那些渐远的时光记忆在他的文字里表现的淋漓尽致。
他的文字语言诗性、灵动、鲜活……那些富有哲理迷离的情思、理趣和意境。读者都能从他的作品中感受到,还等什么,一起来看看吧!
——题记
1、《无雪的冬天是寂寞的》
寂寞的是小孩,他们只能望着爷爷的满头白发,想象大雪飘飘的时光,想象在雪地上奔跑的情景,想象童话里积雪的小木屋,想象他们从没有见过的雪人的样子。
寂寞的是中学生,他们无法理解“燕山雪花大如席”这夸张来自怎样的现场和意象?他们徒然羡慕着李白,行走在白茫茫的唐朝,吟着这白茫茫的诗;那场大雪在诗里保存了千年,至今仍在课本里飘。而他们只能面对苍白的墙壁,用苍白的想象,填写这苍白的作业。
寂寞的是恋人,除了矫情的咖啡屋和煽情的歌舞厅,他们没有更好的去处,他们不曾在雪野里留下两行神秘的如同在梦境里延伸的脚印,他们不曾为自己的初恋塑造一个憨态可掬的偶像——那被世世代代的青春热爱着的雪人,他们是无缘见上一面了。没有诗意的浪漫和铺垫,没有白雪的映照和见证,初恋,昨天下午刚刚开始的初恋,今天上午很快就进入了灰色的、平铺直叙的婚姻程序。
寂寞的是诗人,他们的语言是如此干枯,小雪这一天没有一片雪,大雪这一天没有一片雪,去年没有一片雪,今年没有一片雪。他们在内心刮起一次次风暴,他们在纸上制造了一场又一场落雪。然而,诗之外,无雪;雪之外,无诗。他们的所谓雪,不过是对雪的缅怀;他们的所谓诗,不过是对诗的悼念。一个无雪的世界,是失去贞操的世界,是失去诗意的世界。雪死了,诗死了,如今的所谓诗,只是写给诗的悼词。
寂寞的是那个在灰的路上散步的人,可以断定他的路上不会有奇迹出现,不会有奇遇出现,他不可能与诗邂逅,不可能与他期待的某个梦一样的情节邂逅。他的不远处,一只狗也在散步,他看见狗的时候,狗也看见了他。那狗看了他一眼,无趣地走开了;他看了狗一眼,也无趣地走开了。他们都没有从对方身上看见冬天的生动景象,他们都没有经历过脱胎换骨的严寒的洗礼,他们都用灰色的外套包裹着灰色的陈旧的灵魂。他们都不能用自己身上的纯粹光芒照亮对方的眼睛和心。他们只能用大致相同的灰色款待对方,实际上是冷落对方。他们互相让对方失望。于是他们急忙走开,继续在灰的路上丈量寂寞的长度。
寂寞的是那些深陷于往事的老人,他蜷缩在记忆的棉袄里,偶尔抬起`头看看近处和远处,又很快收回目光,除了镜子里自己的白发,这个冬天没有别的白色,唤起他对于往昔的纯洁回忆。而多年前结识的那个无忧无虑的白雪的恋人,早已死去,他只能在某片云上想象那纯真的面容。
寂寞的是那位正在赶路的中年人,他从许多年前那个无雪的冬天起程,穿越许多荒滩和市井,走过许多平淡无味的大路和坦途,他一点也不羡慕一路顺风直奔目的地的所谓成功者,那样的成功太没有意思了。他实在渴望在某个早晨醒来,忽然发现:大雪已经封山!世界变成一封密封的信,尚无人拆阅,就等他拆阅。他在大雪里行走,就象在一个巨大秘密里行走,他也变成了秘密中的一个秘密。他多么希望在这白茫茫里迷一次路,就那么走了很长很长的路,却发现又走回起点,从洁白出发,又走回洁白,这样的迷路该是多么美好?然而,如今想迷一次路都已成了奢望,起点和终点都被提前确定,程序和步骤都一目了然。但是,他仍然在心里酿造云酿造雾,最终想酿造一场雪,让大雪封山的壮丽困境出现在人生的中途,在被白雪封存的宇宙里,他迷失,是在纯洁里迷失;他徘徊,是在纯洁里徘徊;他跌倒,是在纯洁里跌倒;他晕眩,是在纯洁里晕眩。总之,在这壮丽的困境里,无论怎样的遭遇都是心灵乐意接受的。于是,他在寂寞单调的长旅,期待着一场大雪。
寂寞的是那放风筝的人,他抛出长长的线,试图派遣风筝在朦胧的远空搜索一点什么东西,结果除了收集了大量的尘埃,别的一无所获。当风筝从天上一头栽下来,像升空失败不得不迫降的宇航员一样委屈地匍倒在他的面前,他和它都无话可说。他缓缓收起了线,冬天貌似有着长长的线索,连接着无穷的悬念,其实,悬念都是你的自做多情,那线寂寞的是那个牧师,他用嘶哑的嗓子反复祈祷的天堂始终不肯出现,他越来越难以找到形象的比喻来诠释纯真的教义,如今很少有自天而降的雪花款款飘上经文的关键段落,以加强神圣的感染力。世界的圣洁是由伟大的白雪塑造的,灵魂的圣洁是由伟大的信仰塑造的。白雪死了,世界何以重现圣洁?信仰死了,灵魂何以重归圣洁?我在那个灰蒙蒙的礼拜日,穿过满街的叫卖声和垃圾堆,走进灰蒙蒙的教堂,恰好遇见那牧师,我感觉这里的神圣感已所剩不多,唯一令我感到神圣的,是牧师头上那稀疏的白发。
寂寞的是那个沉思的人,他的思绪时而深达海底,与鱼鳖同游;时而高接苍冥,与天神共舞。然而他无力设计一缕风,无力改变一片云,无力制造一片雪,无力从错别字和病句拼凑的畅销书里打捞出真理的身影,无力使那憔悴的远山出现一抹灵感的白光。他深陷于对自己的绝望里,如同海,深陷于自己的苦涩里,而那深夜出海的船,却把这苦闷的海看作辽阔的希望,海,于是陷入更深的寂寞和忧郁。
寂寞的是那个哲学家,他的哲学除了拯救这一页页无所事事的白纸,其实连他自己也不能拯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乌鸦更深刻的哲学家了,在白雪飘飘的年代,乌鸦曾经发出不祥的预言。然而最终不得不告别一再误解它们的人类,转身失踪于黑夜。没有先知的提醒,没有圣者的感召,没有纠偏的声音,没有校正的语法,世界在纸醉金迷、自娱自乐里疯狂堕落。没有乌鸦的世界,其实是没有哲学的世界。现在,哲学家面对着没有哲学也不需要哲学的世界,他忽然想起了乌鸦在雪野鸣叫的古典时光。只有白雪与乌鸦能拯救世界——他忽然想到;然而,怎样唤回乌鸦,又怎样复活白雪?他在他的哲学里迷茫了,也许,他必须经历漫长的迷茫,才能真正走进哲学,才能找到失踪的乌鸦和白雪。
寂寞的是那位气象学家,他不能原谅自己,怎么看着看着,就眼睁睁看丢了两个古老的节令——小雪与大雪?他不能原谅自己,看了一辈子的气象,除了令人沮丧的恶劣气象越来越多,怎么竟然再也看不见那伟大的气象,纷纷扬扬的雪的气象?那壮丽的气象究竟躲到哪里去了?
寂寞的是我,我站在童年曾经走过的小路上,忆想着:很久以前,在白茫茫的原野,一个移动的影子,一点点大起来,终于看见了那蓝头巾,终于看见了那冒着热气的通红的脸,终于看见了——从雪的远方朝我走来的母亲,仿佛从天国走来的母亲。
2、《心说》
人安静下来,就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在一间空屋里,惟一陪伴你的,是你的心。这时候,你比什么时候都更加明白:你什么也没有,只有一颗心。不错,还有手。但手是用来抚摸心跳的,疼痛的时候,就用手捂住心口;有时候,我们恨不能把心掏出来,捧给那也向我们敞开胸怀的人。不错,还有腿。但腿是奉了心的指令,去追逐远方的另一颗心,或某一盏灯光。最终,腿返回,腿静止在或深陷在某一次心跳里。不错,还有脑。但脑只是心的一部分,是心的翻译和记录者。心是大海,是长河,脑只是一名勉强称职的水文工作者。心是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脑是它的读者。心是浩瀚无边的宇宙,脑是一位凝神(有时也走神)观望的天文学家。不错,还有胃、肝、肾、胆、肺,还有眼、耳、鼻、口、脸等等。它们都是心的附件。它们是无知的,也是无情的。我们不要忘了,狼也有肝,猪也有胃,鳄鱼也有脸。但它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心——因为,它们没有信仰和深挚的爱情。
我们惟一可宝贵的,是心。
行走在长夜里,星光隐去,萤火虫也被风抢走了灯笼,偶尔,树丛里闪出绿莹莹的狼眼。这时候,惟一能为自己照明的,是那颗心。许多明亮温暖的记忆,如涌动的灯油,点燃了心灯。心是不会迷途的,心,总是朝着光的方向。即便心迷途了,索性就与心坐在一起,坐成一尊雕像。
我有过在峡谷里穿行的经历。四周皆是铁青色的石壁,被僵硬粗暴的面孔包围,我有些恐惧。仿佛是凿好了的墓穴,我如幽灵飘忽其中。埋伏了千年万载的石头,随便飞来一块,我都会变成尘泥。这时候我听见了我的心跳,最温柔最多汁的,我的小小的心,挑战这顽石累累的峡谷,竟是小小的、楚楚跳动的你。
在一大堆险恶的石头里,我再一次发现,我惟一拥有的,是这颗多汁的心。我同时明白,人活着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在一堆冷漠的石头里,尚有一种柔软的东西存在着,它就是:心。我们这一生,就是找心。
于是我终于看见,在峡谷的某处,石头与石头的缝隙,有一片片浅蓝的苔藓,偶尔,还有一些在微风里摇曳得很好看、很凄切的野草。
我终于相信,在峡谷的深处,或远处,肯定生长着更多柔软的事物和柔软的心。
这世界有迷雾,有苦痛,有危险,有墓地,但一茬茬的人还是如潮水般涌入这个世界,所为者何?芽来寻找心。这世界只要还有心在,就有来寻找它的人。当我们离别时,不牵挂别的,只是牵挂三五颗(或更多一些)好的心。当我能含着微笑离去,那不是因为我赚取了金银或什么权柄(这些都要原封不动留下,这些东西本来就是些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东西),而仅仅是,我曾经和那些可爱的人,交换过可爱的心。
奇怪,我看见不少心已遗失在体外的人,仍在奔跑,仍在疯狂,仍在笑。仔细一看,那是衣服在奔跑,躯壳在疯狂,假脸在笑。“良心被狗吃了”是一句口头禅了。只是我们未必明白,除非你放弃或卖掉心,再多的狗也是吃不了你的心的。是自己吃掉了或卖掉了自己的心。人,有时候就是他自己的狗。
守护好自己的心,才算是个人。这道理简单得就像1+1=2。但我们背叛的常常就是最简单的真理。
有时候回忆往事,一想起某个姓名就感到温暖亲切,不因为这个姓名有多大功业多高的名分,而仅仅因为这个姓名是一个好心的人,一个真诚的人;有些姓名也掠过记忆,我总是尽快将它赶走,不让它盘踞我的记忆,这样的姓名令人厌恶,不为别的,只因为拥有这个姓名的那人,他(她)的心不好,藏满了仇恨和邪恶。
我们对一个人的评价,乃是对他心的评价。心,大大地坏了的人,怎么能是好人。“圣人”、“贤人”、“至人”,这些标准似乎都高了一些,不大容易修行到位。那就做个好心人吧。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做个好心人,有一颗好的心,这就很好。
3、《雪界》
一夜大雪重新创造了天地万物。世界变成了一座洁白的宫殿。乌鸦是白色的,狗是白色的,乌黑的煤也变成白色的。坟墓也变成白色的,那隆起的一堆不再让人感到苍凉,倒是显得美丽而别具深意,那宁静的弧线,那微微仰起的姿势,让人感到土地有一种随时站起来的欲望,不断降临和加厚的积雪,使它远远看上去象一只盘卧的鸟,它正在梳理和壮大自己白色的翅膀,它随时会向某个神秘的方向飞去。
雪落在地上,落在石头上,落在树枝上,落在屋顶上,雪落在一切期待着的地方。雪在照料干燥的大地和我们干燥的生活。雪落遍了我们的视野。最后,雪落在雪上,雪仍在落,雪被它自己的白感动着陶醉着,雪落在自己的怀里,雪躺在自己的怀里睡着了。
走在雪里,我们不再说话,雪纷扬着天上的语言,传述着远古的语言。天上的雪也是地上的雪,天上地上已经没有了界限,我们是地上的人也是天上的神。唐朝的雪至今没有化,也永远都不会化,最厚的积雪在诗歌里保存着。落在手心里的雪化了,这使我想起了那世世代代流逝的爱情。真想到云端去看一看,这六角形的花是怎样被严寒催开的?她绽开的那一瞬是怎样的神态?她坠落的过程是垂直的还是倾斜的?从那么陡那么高的天空走下来,她晕眩吗,她恐惧吗?由水变成雾,由雾开成花,这死去活来的过程,这感人的奇迹!柔弱而伟大的精灵,走过漫漫天路,又来到滚滚红尘。落在我睫毛上的这一朵和另一朵以及许多,你们的前生是我的泪水吗?你们找到了我的眼睛,你们想返回我的眼睛。你们化了,变成了我的泪水,仍是我的泪水。除了诞生,没有什么曾经死去。精卫的海仍在为我们酿造盐,杯子里仍是李白的酒李白的月亮。河流一如既往地推动着古老的石头,在任何一个石头上都能找到和我们一样的手纹,去年或很早以前,收藏了你身影的那泓井水,又收藏了我的身影。抬起头来,每一朵雪都在向我空投你的消息,你在远方旷野上塑造的那个无名无姓的雪人,正是来世的我……我不敢望雪了,我望见的都是无家可归的纯洁灵魂。我闭起眼睛,坐在雪上,静静地听雪,静静地听我自己,雪围着我飘落,雪抬着我上升,我变成雪了,除了雪,再没有别的什么,宇宙变成了一朵白雪……
唯一不需要上帝的日子,是下雪的日子。天地是一座白色的教堂,白色供奉着白色,白色礼赞着白色。可以不需要拯救者,白色解放了所有沉沦的颜色。也不需要启示者,白色已启示和解答了一切,白色的语言叙述着心灵最庄严的感动。最高的山顶一律举着明亮的蜡烛,我隐隐看到山顶的远方还有更高的山顶,更高的山顶仍是雪,仍是我们攀援不尽的伟大雪峰。没有上帝的日子,我看到了更多上帝的迹象。精神的眼睛看见的所有远方,都是神性的远方,它等待我们抵达,当我们抵达,才真正发现我们自己,于是我们再一次出发。
唯一不需要爱情的日子,是下雪的日子。有这么多白色的纱巾在向你飘,你不知道该珍藏那一朵凌空而来的祝福。那么空灵的手势,那么柔软的语言,那么纯真的承诺。不顾天高路远飞来的爱,这使我想起古往今来那些水做的女儿们,全都是为了爱,从冥冥中走来又往冥冥中归去。她们来了,把低矮的茅屋改造成朴素的天堂,冷风嗖嗖的峡谷被柔情填满,变成宁静的走廊。她们走了,她们运行在海上,在波浪里叫着我们的名字和村庄的名字,她们漫游在云中,在高高的天空照看着我们的生活,她们是我们的大气层,雨水和雪。
唯一不需要写诗的日子,是下雪的日子。空中飘着的,地上铺展的全是纯粹的诗。树木的笔寂然举着,它想写诗,却被诗感动得不知诗为何物。于是静静站在雪里,站在诗里,好象在说:笔是多余的,在宇宙的纯诗面前,没有诗人,只有读诗的人;也没有读诗的人,只有诗;其实也没有诗,只有雪,只有无边无际的宁静,无边无际的纯真……
4、《野地》
在随便什么时辰,对城市作一次小小的逃亡,到野地去呼吸,去想些什么或什么也不想,就一心一意感受那野地,是我的一门功课。
野地有很多树。柳树、松树、槐树,还有叫不出名字的灌木。不是成材林,也非防风林,结出的果子也不能食用,是一片无用的杂木林。它安于它的无用,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这一片野地,在我眼里,它是这般地有了大用。它不仅供给我清新的空气,也免费让我欣赏鸟儿们的音乐会,且是专场,聆听、鼓掌都是我一人。黄鹂的中音,云雀的高音,麻雀的低音,布谷鸟抑扬有度的诗朗诵,报幕的是斑鸠吧,清清朗朗的几句,全场顿时寂静,接着出场的是鹦鹉,不像是学舌,是野地里自学成才的歌手;路过的燕子也丢下几句清唱,全场哗然,喜鹊拖着长裙出面了,它像是不大谦虚也不留情面的音乐评论家:“叽叽喳喳”——它是说“演出很差”?于是众鸟们议论纷纷,议论一阵就暂归于寂静,奖金是没有的,午餐补助从古至今就没领过。它们四散开去,各自找自己的午餐。
林子的外面长满了草,招引来三五头牛或七八只羊。牛有黑有黄,羊一律的白。羊口细,总是走在前面选那嫩的草,那么认真地咀嚼着,像小学生第一次完成作业。我抚摸一只小羊的猗角,它做出抵我的样子,眼睛里却是异常的天真温良,它是在和我开玩笑,那抵过来的角,握在手里热乎乎的,它一动不动地让我握着,我们彼此交换着体温和爱怜。我顺手递给它一株三叶草,又握了握它的角,说了一声:“好孩子”,却再也说不出下面的话,因为我忽然想起了我穿过的那件羊皮袄。我觉得我对不起这些可爱又可怜的羊,它们是多么纯真的孩子啊。正想着,那头大黑牛走过来,它埋头吃草,就像我埋头写诗,都是物我两忘的境界。一个小土坎它却爬得很吃力,我这才发现它是怀孕的母亲,脖颈上有明显淤着血的疤痕,怀孕期间它仍在负重拉犁?我走过去,急忙牵起缰绳拉它一把,它上来了,感激地望着我,我看见了它眼角的泪痕,我向它点点头,示意它快些吃草,祝福它身体健康、分娩顺利,一路平安。我的心里多少有点苦涩,贴近哪一种生命,都觉得它们很美丽,也很苦涩。我终止了我的联想。我看见,远处那黑牛,仍不时地抬起头望我……
野地的边缘有一小块瓜菜地。包包菜一层一层包着自己内心的秘密,像一位诗人耐心地保存着自己最初的手稿。芹菜仍如古代那么质朴,青青布衣,是平民的样子,也是平民的好菜。红萝卜,通红的小手仍在霜地里找啊找啊,在黑的泥土里它总能找到那么鲜红的颜色。
南瓜不动声色地圆满着自己,据说南瓜在夜晚长得最快,特别是在月夜,那么它一定是照着月亮的样子设计着自己,它把月光里的好情绪都酿成内心里的糖。西瓜像枕头,却无人来枕它做梦,我就睡在这枕头上,果然睡着了,梦见我也变成了一个西瓜,在大街上乱滚,差点碰上了钢铁和刀子,于是我又返回到野地,我掐一掐自己,想尝尝,却感到了痛,于是我醒来,看见西瓜仍然自己枕着自己酣睡。
这时,我隐隐听见了水声,野地的前方是一条河,我看见它微微露出的脊背,白花花的脊背,它摸着黑赶路。是子夜了,月亮悄悄地升起来,月光把野地镀成银色。星星们把各种几何图案拼写在天上,地上有几处小水洼,临摹着天上的图案,也不注意收藏,风吹来,就揉碎了。恰好有几片云小跑着去找月亮,月亮也小跑着躲那些云,云比月亮跑得快,月亮终于被遮住了。
星光照看着野地,有些暗,但很静,偶尔传出几声蝈蝈叫,我能听出它们的雌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