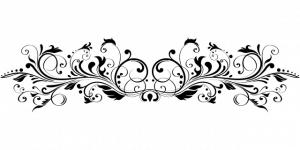老屋开头摘抄
老屋在村子中间,三间庄基,坐南朝北。听说原来是三进房,门房、庭房、楼房,门房和庭房之间还有两对檐的厢厦。[门房、庭房、厢房、楼房都是院里建筑的名称]在我的记忆中只有最前面的门房和最后面的楼房,庭房和厢厦都已拆除,东西两边的墙上掏去柱子的柱缝还在,向我诉说着老屋昔日的辉煌。门房正对着大街,门房到楼房之间有十几丈长。出了门房后门是一座照壁。青砖砌的底座,青瓦盖顶,中间用土坯砌成,干净的泥皮上隐约可见一根根铡碎的麦草撒满墙面,银白色的麦草和昏黄色的泥皮结合在一起仿佛简笔勾勒的沙画。照壁后是一株高大的石榴树,枝繁叶茂。

五月的榴火、八月里青中泛红的石榴挂满枝头。一部分树冠从照壁顶端伸过来。绿荫夹裹着榴火,夹裹着被榴籽撑裂的石榴,向每一位家庭成员和造访的客人含笑招手。过了照壁,东西两边靠墙的地方长满了高大的榆树还有几株参天的白杨。东墙一排树的里侧是一条通向后面楼房的小路。路不是很直,没有铺砖,高出整个院子少许,被全屋人踩踏的又硬又光。半路居中靠墙处伸出一个两米见方的厦顶,墙上装着辘轳,辘轳上黑光黑亮的的铁栓垂向井口。井台用一块大青石做成,中间掏孔,浑然天成。井边一株老桑树,端庄秀丽。
西边靠墙的地方,在树的空隙间堆放着柴草。主要是麦草和包谷杆,还有干树枝,堆放的齐整有序。柴草两侧有两个相距丈余的梯形土堆,那是两孔窖,直径不到一米,深不到三米,用来储藏红芋,还有萝卜、白菜等冬菜。七十年代搞备战,曾将两个窖挖通并和对面的水井相连,做成防空掩体。院子中间很大一块空地,是主人夏日纳凉吃饭的场所。楼房的后面是后院,不长,大概两三丈左右。两株大椿树相距两米,粗可合围,笔直端正,傲然直插霄汉,硕大的树冠将整个院子罩满,靠后墙的地方修着两个猪圈。老屋的每个旮旯都留下了我的足迹,翻过后院的墙,上过屋里的房,爬过院中的树,钻过地下的窖……老屋的兴盛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当时,曾祖父六十岁左右。两个伯祖父,一个叔祖父和我的祖父都正当壮年。
全屋十几口人,六十多亩地,两挂马车,骡马三匹。一心想做财东的祖父辈不满现状,不固步自封,下河北【渭河以北】、出潼关,肩挑贩运,男耕女织,苦挣家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农工商并举。老屋的日子就像开春的麦苗呼呼呼迎风拔节,成为方圆十几里屈指可数的富裕人家。公元一九四九年五月的一天,从渭河过来了几个年轻的军人下了镇长刘某的枪。驻扎在县城和飞机场的国军两个营全体投诚。没听见隆隆的枪炮声,没听见人喊马嘶,改朝换代了。老屋的主人和全村人一样,继续做买卖挣钱,种粮食吃饭,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曾祖父常说共产党来了,土匪少了,世道安宁了。在他说这话的两年后,村里住进了土改工作队。老屋的主人被定为上中农成分,全家十几口人分了三十多亩地,其余的土地都被全村人均分了。接着是初级社、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牲口大车都成了集体财产。赌博了半辈子的曾祖父过手的钱财无法计算,对这一切还是很看得开的。他说钱财是人身上的垢痂,去了倒还轻松,再说了就凭咱这么多劳力,辛苦几年还愁过不上地主日子。曾祖父还是很幸运的,在那饥荒的三年和那场运动到来之前,被全家人风风光光地送到了天堂。据大伯说曾祖父阴宅的对联就是他刻在砖上的,对联的内容是‘千里卧龙来福地,一弯碧水绕明堂’。如果说那饥荒的三年是天灾的话,那场运动就是人祸了。在饥荒的三年里,老屋人拼光了解放前多年的家底和积蓄,吃糠咽菜茹粗啖粝是有的,究竟还没有到吃草根树皮的地步。全屋人风雨同舟共渡难关。曾祖父去世后,我的祖父成了老屋的主事人。
三年饥荒结束后的第一年,政策有些宽松,不甘过贫穷日子的老屋人在他的领导下又做起了过财东日子的梦。利用农闲时间干起了贩卖棉花、加工制售辣椒面的营生。因为利润可观,甚至生产队的工分都不想去挣。又在后院新砌了一个猪圈,连同旧猪圈老屋总共喂养生猪八头。这些后来都成老屋的罪状。公元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开始。在社员大会上,一个贫下中农说老屋人贩卖棉花和制售辣椒面是投机倒把,还质问说;别人一家就养一两头猪,你们竟然养了八头,在家里办起了养猪场,这不是资本主义是什么。那个贫下中农脸上激动得有些扭曲的表情和他的豪言壮语是那么的不容分辩。从此,爷爷经常被拉去批斗,后来,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老屋人过着如履薄冰的日子。一九六八年,上边说西北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在西北地区搞起了民主补课。
一些和老屋的大小人口有过节的人像是遇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借运动之机睚呲必报,认定老屋是漏网地主,老屋的全家大小被升定为地主成分。党支书领着人来了,抬走了老屋的自行车和缝纫机,团支书领着人来了,拉走了老屋的架子车,贫下中农中的积极分子来了,给老屋的面翁和衣柜贴上了封条,大有解放初分浮财的架势。大伯后来说当时下放到村里的一个女干部是个知识分子,晚上来到老屋悄悄告诉爷爷让把封条弄湿慢慢接下,取出要用的东西第二天再原封不动地贴上去,全家才不至于把嘴泥上的。在此后的十几年里,招工参军都没有老屋人的份,更别说入党入团了。就像伯祖父说的全屋人都在夹着尾巴做人。成分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所有老屋人的头上。记得我七三年上学报名回来的时候。
爷爷把我拉到墙角悄悄地问我说‘老师问你啥农你是咋说的’。我说‘我不知道,领我去的某某说咱村都是贫农’。爷爷诡秘的的笑着说‘以后老师问你你就那么说’。大自然中的风雨让老屋的墙皮斑驳陆离,文革的风雨让老屋不堪重负。七十年代初期,老屋的一家大小分为六家,老屋的房子只剩下一进,伯祖父和一个堂叔住着。其他几家陆陆续续重新要了庄基,相继离开了老屋。算起来这时老屋的人口已超过三十人,也到了分房另住的时候。这也许是祖父辈的高明出,全家大小挤在一个屋里也就占集体三间庄基,分开了倒占了近二十间庄基,也去了家大业大之嫌。也许是合久必分之必然。不知道那个贫下中农有没有算过这个帐,过去老屋养了八头猪说是办养猪场,现在分为六家,每家养两头合起来就是十二头,比养猪场还多出几头呢。
想到这里我不禁哑然失笑。老屋像一棵大树,经历了文革的风雨,虽然有创伤,倒是更显得枝繁叶茂,几十年过去了,原来的六家现在已成为十几家,人口已近百人。对于老屋的后人来说,文革是磨难也是历练。政策开放以后,老屋的子孙虽没有大富大贵,倒也把日子过的像模像样,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有的在西安安家落户,有的在大上海开枝散叶。搬出老屋已经三十多年了,老屋也在改革的洪流中发生了沧桑巨变。漂亮的两层小洋楼拔地而起,深长的院子也在乡村改造中被截短,现在只住着堂叔一家,整个村子整齐划一,几乎一个模样。
但每次从那里经过的时候,我总是不由得看上一眼,就是梦也时常在那里发生。对于从老屋走出的众多子孙而言,老屋是根。我想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曾经的老屋,让人无法忘怀。不论是富家的青砖庭院还是贫家的茅屋草舍,不论是乡村的木屋还是城里的高楼大厦,在梦中都会十分的清晰,就是茅屋的椽子和庭院的青砖都会一目了然。众多的这样的老屋在黄土地、黑土地、红土地里盘根错节,就交织成了中华民族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