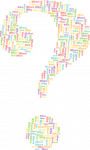梨树下示例
在老屋后院菜园子里,祖父曾种下三棵梨树,确切地说是四棵,其中一棵石头梨较早就被砍了,其它三棵最终也未能幸免,但至少陪伴我们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另外三棵树一棵是雪梨,皮薄肉白如雪极甜;另一棵是萝卜梨,果肉特像白萝卜味甜;还有一棵汀濯人称子梨,皮厚肉硬味淡。

推开老家西横屋的后门,从东到西依次是雪梨、萝卜梨、子梨,雪梨树离横屋后墙最近,子梨树距离最远,三棵树相邻距离大约三米,斜向西北接近一字排开。雪梨最挺拔俊俏;萝卜梨有两个主分叉,一个枝丫直挺干脆,另一个枝丫成45度倾斜后直立向上;子梨枝繁叶茂,像一把撑开的大伞。
这三棵梨树是我童年的见证者和陪伴者,童年许许多多的快乐来自梨树上的果实或梨树下的乐园。不必说旁边碧绿的菜畦,粉色的紫茉莉花,葱绿的香樟树;也不必说鸣蝉在棕叶下长吟,贪吃的花麻虫伏在南瓜花蕊上,轻捷的麻雀忽然从菜畦直窜向墙洞里去了。单是梨树下三十平米的范围,就有无限趣味。有时候,姐弟几个在墙根下垒泥灶台,用断瓦残砖照着二叔垒灶的样子,像模像样地做成缩小版的柴灶,锯一段废弃的扫帚竹筒立在灶尾墙根下当成模子,糊上泥巴,待泥土干了就成了烟囱。我们在小柴灶上用大号的“百雀羚”面油盒子豆子,或用断柄的铝勺煮盐粥,儿时汀濯的“煮食”(过家家煮食游戏)被我们玩成了真实版。
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后院树树梨花竞相开放的样子,偶有大风过后树下散落不少掉落的花瓣。枝头随处可见嘤嘤嗡嗡的蜜蜂在花间飞舞跳跃。夏日某个阴天傍晚,我和弟弟正要爬上西北角的子梨树,忽然看见面前不少蜜蜂杂乱无章地飞舞着,时而又聚在树干上,目光随飞舞的蜜蜂望去,树干上聚拢着黑压压的一片蜜蜂,有些上下翻飞,有些不停地涌动着。我们暗暗吃惊,马上叫来二叔查看情况,二叔做了一番简易的准备,用豆腐帕蒙着半张脸,他用塑料纸包裹着自己,戴上斗笠,戴上白色的劳保手套,只露出一双眼睛。二叔又找来一把带松脂的松木片和一个编织袋以及一个曾当作蜂巢的无耳木桶,他再次来到树下,用火柴点燃几片松木片,熊熊燃烧的火焰里夹带着一股浓浓的黑烟。二叔左手拿起地上的编织袋,将袋口放在蜜蜂聚集处的上方,右手持着火把靠近蜂群下方,浓浓的黑烟驱使蜜蜂向上涌动,蜂群慢慢地向张开的口袋移动着。约莫过了二十分钟,绝大多数的蜜蜂入得口袋,扎起袋口。二叔令我们搬来两张方凳,拎起木桶倒扣在两张方凳的空隙上方。此时提起口袋打开一个口子,蜜蜂开始转移到木桶里原先备好的树枝搭成的架子上,刚开始只有几只,二叔提了提编织袋角,慢慢地上移的蜜蜂越多,直到所有蜜蜂都进入桶里,将编织袋覆在桶口用细绳绕木桶扎了一圈。二叔小心地捧起木桶来到老屋门口,找来几片短木板爬上梯子将木板放在原有墙洞里伸出的细圆木上,再回到地面,左手扶梯,右手环抱着木桶上到高处,小心地去了编织袋,将木桶倒扣在木板台上。至此,这群野蜂就在老屋门口安了家,那个木桶距桶口约一寸处钻有三个小孔,是蜜蜂进出的通道。我们常在蜂桶下观察,不时有蜜蜂进出小孔,也有些侦察蜂从远处飞回,欢快地在蜂巢边跳起了8字舞,之后就有大批的蜜蜂飞去飞回,采回花蜜。隔了不知多久,二叔将蜂巢取下,割了蜂糖再放回原处,再后来不知何时那群蜂消失得无影无踪,也许无蜜可采,它们去了别处,那些蜜甜得咂嘴巴。
每到夏天,水稻收割之后,勤快的姐姐便找来糯谷稻草,糯谷稻草比粳谷稻草往往更颀长且更具韧性,姐姐用稻草编成很粗的秋千索,我们将秋千索挂在梨树的横粗枝上荡秋千。挂秋千索的光荣任务自然由我完成,我像只猴子般带着稻草绳的一端敏捷地爬上萝卜梨树的斜枝丫粗树干,到达第一根横枝上调整好稻草垂下的长度,并将枝上的长半截儿在一细枝前绕粗枝一圈打个结拉开半米左右,在另一根细枝后再绕粗枝一圈并打个结垂下。两端直接绑上或再绑上稻草蒲团,一个简易秋千就做成了。这样的秋千我们可以玩一个夏天,有时玩到饭点还舍不得离开,欢声笑语回荡在树下,那时周围的房子距离较远,也不会吵到邻居。有一次我站在秋千上晃荡,一不注意摔倒在地上,脸磕着地面,站起时感到无比疼痛,旁边的弟弟吓得不行赶紧去告诉父母,父亲过来的时候我也不敢喊疼,实在忍不住了才吐了一口血在地板上,直接去厨房备了一碗盐茶漱口就此作罢。午饭时,我连捣烂的茄子泥也咀嚼不动,往碗里倒了点凉茶泡饭囫囵吞枣了事。
最早熟的是雪梨,梨子熟时也是快乐的时令,从地里劳动回来,我三下五除二爬到高处,在树上先吃一个,再猛摇几下,陆陆续续听到冰雹坠地似的声音,姐弟们开始在地上迅速捡拾梨子。待她们捡完后,我再摇几下,树下又一次忙乱的捡拾。我下得树来,迅速回屋,姐姐已用清凉的井水洗好满满一盆的雪梨,抓起一个,放入齿间,“咔嚓”几声,脆甜入心,凉入肺腑。大家都喜欢摔伤摔裂的梨子,似乎更甜些。雪梨产量不多,一大家子往往吃上三五天就没了,过了些日子,萝卜梨就熟了,萝卜梨斜树干经不住我们爬上爬下,再厚的树皮也能被我们蹭得光亮起来。脆萝卜似的梨子,水分比较多,甜度还行,最好削皮吃,有点像现在常见的丰水梨,颗粒较粗糙,比起丰水梨味道稍逊一些。待到萝卜梨吃完,硬梆梆味道极淡的子梨也差不多熟了,并不怎么受欢迎,牙口不好的真不想啃,梨脐凹陷的凑合能直接吃,母亲偶尔会煮熟一盆子梨,立马变成人见人爱的美味。
园子带给我们无限欢乐,梨树功劳最大。夏天农忙过后,没轮着放牛的时候,我和堂哥常常躲在茂密的子梨树上,那里可以远眺大半个中心村,堂哥是我隔壁班的同学,说话虽不太利索,但他总有许多故事与我分享,有时是一部我没看过的电影,有时是各种奇闻异事,和他在一起时光总是加速地奔跑,快得很。
满树的梨花和满树的梨子都不足以让人惊喜,漏网之“梨”才会让你欣喜若狂。待到秋稻种下耘田除草时,一家人正吃着午饭,习习凉风吹进厅堂,或许是姐姐先吃完饭走出后门偶尔抬眼望树梢,开心地喊出:“树上还有几个熟透了的萝卜梨,快来看”我迅速扔下碗筷,走出门连忙问:“在哪?在哪……”顺着姐姐手指方向,看到树叶掩映着微黄的萝卜梨,找来篱竹,爬将树上,接过姐姐递来的竹子,一步一步接近树梢,直到竹子够得着几个梨子,停下站稳,奋力敲去,“啵~啵~啵”几声梨子落地之后,再搜寻几遍,确信再无漏网的梨子之后,开始带着竹子缓慢往下走。下到距离地面两米多时,撒手将竹子扔下,准备继续往下走,然而树下传来几声惨叫,我赶忙往下看,只见父亲手捂右额连声哀叫往屋内跑去,剩下的一段树干我战战兢兢带着哭腔往下溜,差点摔下。进得屋内,看父亲手捂额头,躺在竹凉床上,哎呦哎呦地叫着,我慌乱极了,不敢去问他伤情。
母亲说姐姐去请村医厚宜了,我惊吓得不知所措,小声地跟母亲问父亲的眼睛会不会瞎掉,母亲说:“要是瞎了你就害死你父亲了。”此时,我看到二楼佛龛前祖母正一手举在前方,一手捻珠,专心念经祈祷父亲的平安。
不多久,厚宜医生就来了,问了些情况,打开手电给父亲做了细致检查,他说万幸只是皮外伤,未伤及眼睛,消毒处理后,没有缝线,做了简单包扎之后又交代母亲一些注意事项。我就这样惶惶不安地过了几天,父亲定期到厚宜诊所检查和换药,直到伤口愈合脱痂。许多年以后,偶尔父亲会提起天气变化时,额头伤口位置会感到隐隐约约地感到莫名奇痒,这时我总感到惴惴不安,我差点亲手毁了父亲的眼睛,万幸的是没有发生更为严重的后果,要知道篱竹的底部基本都是削成尖利的斜劈。
那三棵梨树见证了越来越好的农村生活,见证了院子里的悲欢离合,栽下梨树的祖父没吃过几口梨历尽艰辛溘然长逝。他去世时,距离梨树也就几米远。院子里相继出生了三个堂弟,他们在梨树下从呱呱坠地到呀呀学语,再到树下晨读,梨树们总是默默地陪伴着他们度过快乐的童年。1989年8月某天风雨大作,特大的狂风掀开了不少村人的瓦房,刮跑了不少瓦片,在风雨飘摇中,梨树依然傲立原地,与老屋相互陪伴,相互依存。
又到满树挂梨,飘香满园的季节,老屋还在,屋顶已被换上了带点俗气的蓝色琉璃瓦,屋后再无婆娑的树影,风过再无梨树叶子沙沙的声响。
梨树下的佛龛还在,蒲团前再无祖母的身影,只有天井里父亲栽下的一盆盆山兰越发郁郁葱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