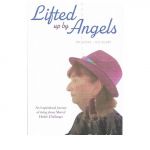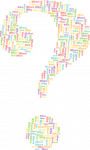只想你好好活着
2016年2月27日,晴好。

听闻长沙多处梅花盛放,正美,我欣然前往。景也需人的欣赏和多情,才俞见生命的不可思议和欢喜。
早春时节,岳麓山,游人如织,黄发垂髫,怡然而乐。我探访幽道,一路上山、下山,感叹风月无主,闲者自得,在最原始的自然馈赠面前,从不分贫富贵贱、老长少幼,只要感官健全,所见所闻,都是生命的享受。猛然想起苏子《前赤壁赋》里他与客的一段思辨之后,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苏子的心态绝不是偏激者的纵声享乐,那活在当下的淡然与珍惜生命的热情,是常人所难权衡的。
行至山脚,手机振动,信息提示。
我避开来往摩肩接踵的人群,寻得一块空地,掏出手机,信息,一般不会有人给我发什么信息,除了10086。
看过信息,如遭五雷轰顶。我艰难穿过人海,飞奔回校,街边的音乐浪潮和阳光,现在,都与我无关。
真希望所有的晴空霹雳都是虚惊一场。
真希望县里医院不收,其实全是误诊。
回校的公交车上,我第一次这样心慌。紧紧抓住手机,等待姨发来确定的医院信息。四十分钟时开时停的车程,仿如世纪。
消息确定,省肿瘤。
我回学校,匆匆带上毛巾洗具,赶到医院,挂号并熟悉环境。
焦急而无所适从的等待时间里,我拿出塞在书包里的《文艺心理学》,一页不过两百字,可强解无味,放弃。
终于等到阿姨舅舅将母亲送来,我迎上去,一阵心酸往肚里吞。那人群里穿得最破旧的、拎着别人用过的送她的破旧的包的、不管穿多少条裤子裤腿总是撑不起来的瘦弱的、46岁便冒出许多白发的、黄黑凹陷带着深深愁容的,便是我母亲。我惊讶于别后一周,母亲的两颊竟然肿大得如此厉害,肿大的淋巴结已让本就松弛的两颊走样,扯开脖子上的高领毛衣,那更是触目惊心。我不孝啊,寒假回家,本也看到母亲一边稍有松弛肿大迹象,我以为那是母亲上了年纪又没有吃什么营养品的原因,便没有过问。若是当时追问与触摸,兴许情况也好过现在。
我母亲,是我二十年来见过最不像个女人的女人。上山下地、挑谷种田,男人干的重活累活,她都干,是件和时宜的衣服,她都穿。她不会偷懒,不会巧干,于是常常吃亏,吃人亏,在这个社会里,说到底也还是吃自己亏。她从没买过衣服,至少从我记事起,从没有过。在她那里,一件衣服只要回到最原始的作用就可以,别人常劝她,你换件好点的衣服吧。她仍旧随便穿,始终学不会,世故。不懂世故是要付出代价的,买东西,别人会杀她黑,排队会被插队,看她一副穷酸模样,便没有好脸色。我也不知道人何来的优越感,弱势群体也是生命,我母亲出一样的钱,买一样的东西,别人得到的是笑脸相迎拱手想送,而我母亲得到的是爱理不理甚至是嫌弃,只因母亲的形象不讨喜。多少伪君子如鱼得水,而老实本分的母亲却处处碰壁。
我父母结婚很晚,生下我时,父亲已经四十岁,母亲嫁过来,家徒四壁。我快要入学时,父亲出去打工,我日日随母亲束薪山中,晨昏暮暝,虫蝈鸟鸣,赚得一身红疹与尘土归家,灶烟四起,抓一条小板凳,坐落黄昏。昏暗灯光中,母亲端来并不美味的饭菜,她的厨艺,一辈子如一次,只能满足抵饱的欲望。可她吃得很满足。我上学前班,没有同学愿意和我玩,他们都愿意去围着穿得好、总是带零食来学校的孩子。我没有文具,没有彩笔,小学课本上的《蓝树叶》在我身上如实上演。同学不愿意把红色蜡笔借给我,我用铅笔涂了一个灰色的太阳。尽管我在学校过得不快乐,但每天仍有期待,只要母亲去干活经过我的学校,她总会在家里烤好一个红薯带给我。那时候,红薯便是我最好的零食。上一年级之后,我努力学习,成绩好本该只是自己的事,却为我带来了玩伴和别人对我父母多一点点的尊重,而那时我早就习惯了一个人玩,自己缝布娃娃,收集石头,玩弄来自舅舅不要了的颜料画画,学书上剪纸,如果天气好,便在屋前竹枝堆上跳来跳去,跳一下可以弹出半米高,那是我的跳跳床。
三年级结束,村里的小学撤销了,因为没有老师愿意来一个山沟沟里教书。我们便要步行翻过大山去别的村里上学。学校的上课时间安排不会因为学生的路途遥远而改变。天还没亮,鸡叫三遍,母亲便起床为我做早饭,不论刮风打雷,晴霜雨雪。那时候我不懂事,不愿意吃母亲带着昨日未解的劳顿和预支今日的辛苦做的早餐,执意要她给我一点钱,去买那五毛钱两个的包子。母亲无奈,只好答应我。之后又打着手电,送我到几里外另一个孩子家。我那时真是不懂母亲的辛苦啊,她做的菜不好吃,她又何尝吃了好吃的呢。每日睡不得安稳觉,听着鸡鸣而起,晚了还怕误了我上课。
儿时守家眼巴巴张望的,便是赶集回来的母亲手里的袋子,里面总会装上一点点的零食,照顾我的贪吃。而若是儿女远游,母亲心心念念的,绝不是子女带来的东西,而是子女的平安健康。
我初中毕业读大学那年,母亲扛着大包小包送我到学校,很显然,她是欣喜的。而不懂事的我,却在一个月内花光了两个月的生活费,身上又没有卡(未到办卡年龄),她在家里急的不知怎样才好,最后在舅舅的帮助下让另一位叔叔给我送来了钱。小时候做错事,是要挨打的。到那个年纪,连骂也几乎没有。但那次,我的自责、内疚与感动,多么希望他们打我一顿,或者骂一句也好。
大学期间,我回家的次数少,通常是到学期末才回家。回家的那天,母亲算好我快要到家的时间,早早地在家门前的路口翘首企盼。待确定远行而来的人是我,便忙着迎过来,帮我抬行李走过那不宜拖地的石子路。
我与她分享的每一件小事情,她都会记在心里,而我通常忘记。她送我上大学的一点见闻,成了此后她对我在校生活想象的总支点。我每谈到一个同学,她都会问,是我见过的那个吗?是睡你上铺的那个吗?我便细细地讲,不是,不是你见过的。她就失望了,沉默了,因为她的回忆已经不起作用,我讲的,她想象不出。去年我拿回去一张优秀实习生的荣誉证书,她开心得看了又看,再三叮嘱我,收好、收好。她开心的,肯定不是一张别人给的证明,而是觉得自己的女儿,有足够的能力应对未来哪怕没有他们的庇护的生活,可以在这个社会立足。
母亲做不好菜,缝不好衣服,我来。没有谁规定这些事情必须由一个母亲做,只是天下的母亲都心甘情愿地劳累和付出,让无知者习以为常地被爱,以为都是理所当然。
处处为我的生活着想的母亲,自己的生活却成了问题。
检查的那几日,我请假带她四处走走。我看过无数人在镜头面前的反应,都没有我母亲的郑重其事,郑重到呆板。不过是随处一张纪念照,本可以轻松随意地面对或不面对镜头就好,可她在镜头前站得如接受检阅的士兵,两手直直地贴在裤腿边,若不是需要面对着她,我早已心酸得落下泪来。
父母二人吃饭,只点一个菜,母亲夹得很慢,父亲几乎不往菜里动筷子,让给母亲吃。那时他们还不知道母亲的病到底有多严重,想着省下钱用来治疗。其实省这一个菜的钱对于医疗费用来说,就是沧海一粟。
送他们回县里的时候,父亲说,回去得借钱,至少是五千。我忍不住告诉他,如果化疗,一次就得上万。父亲一听,深深地叹了口气,再也没说话。我后悔自己这样嘴快,父亲多病缠身,又老了,一路靠超负荷的劳动养家糊口,而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我告诉他需要这么多钱,只会加重他的心理压力让他承受双重难受,而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父亲绝不可以倒下。
舅舅们与我讲,万一我母亲出事了,他们会把我当女儿看待。他们是为我着想。而我现今最需要的,是我的母亲活下去!我四肢健全,有头有脑,以后自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好好生活,人也总有没有父母庇护的时候。此时根本没有心思想这些,我所有的想法,都是母亲得好好活着!活着看我顺利毕业,看我好好工作,穿我挣钱买的衣服,吃我种的菜,住我盖的不再风雨飘摇的房子,活着看那么一天,我终于牵着另一半的手,走到她面前,好好地叫一声,妈!这辈子,您辛苦了!我要让她好好地享受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母亲的幸福。
可是实际上,以上的这些,她还一个都没享受到,却要忍受疾病带来的痛苦、无钱治疗的压力、生死未卜的恐惧、对儿女放心不下的牵挂。她在电话里哽咽,倘若她真走了,怎么放心得下我姐弟俩。我泪如雨下,泣不成声。到这个时候了,母亲想的还是我姐弟。我告诉她,不用担心我,我的书不是白读的,以后我也可以供弟弟上学,你就只要好好养病,钱我可以想办法。话是安抚母亲的。父亲去借钱,邻里都委婉地拒绝,他们害怕将钱借给一个贫困之家是投石入海。虽然我让父亲告诉他们以后全由我来尝还。
就算负债累累,穷得不能有多么好的物质享受。我都没问题。
无论蓬户荆菲,只要有你的倚闾,便成为我的凯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