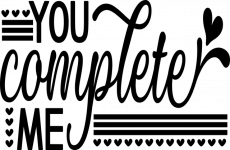《城以北·墙以南》(一)
从郊外搭乘去往市中心的一辆货车上,透过玻璃照射进来的阳光刺在脸上,我正背靠副驾驶座的椅子上眯着眼睡觉。从进去之后我就没再睡过一天能被阳关灼烫的午觉,因此我很享受现在的舒适,而冬季的阳光更甚如此。在渐渐入睡之前,我脑海想着前一刻离走时的感受,我想不清为什么会有点别离的伤感兜兜转转始终撇不开,但我认为撇不开的却是那几个字:“时间太久,我们认识很久;时间太短,我们还未认清”。我用五年的时间写出这句话,正如此句,我跟她的相识,久在久远;短在,彼此未够看清。我看不透五年后的她,因为五年她未曾来过。五年前她将我送到那扇铁门前,含着泪分手,五年后她忘了有一条路是我要去的地方。

我好过一段过往,却化解不了一个心结,哪怕用上五年。我依然还会想起。
……
在扑朔迷离的记忆中,也只有一条胳膊上留下的几许感触,把我带到她的身边。那天是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样子,她上身微倾,一条胳膊撑在柜台上,手掌放在脑袋上,另一只手端着酒杯,当时她就坐在我旁边。酒吧内,恍恍闪闪的灯光射过来、划过去,我喝过一杯,转过头便看到了她,我承认我在她脸上停留的时间绝不少于十秒,而庆幸的是她还未发现的情况下,这让我很欣喜。
女人大概二十六七,脸上似带着阴郁,惆怅地喝着酒,那一抹黯然牵动了我莫名的伤痛。再后来,我又喝着几杯,她也喝着几杯,这几乎是在她拿起酒杯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喝完了我着杯,我并非跟她抬杠但有意抢先她一步喝,我只是觉得这样我便更多的时间观察她喝酒的样子。她酒量似乎比我还好,在我似有微醉时她却并未有什么反应,这也为什么再后便被她发现的原因,然而她并未说什么,这让我更加光明正大的直视她那双眸下深邃的眼珠。她脸上匀了红晕,脸上的反应,让我看了更加陶醉。然而这一切都在一个男人的到来,打破了我欣赏的愉悦。
一个三十好几的男人,他端着酒杯坐在女人的另一边,他就这么像模像样的坐下然后将服务员叫来的一杯酒放到她的面前。
“美女,请你喝一杯酒可以吗?”
他说完这句话,我几乎是羞愧着红着脸移开看她的目光,这么久,我坐在她旁边几乎压根没想到想有请她喝一杯的心思,我几乎后悔死了,然后又想到刚刚她喝我跟着喝得行径却是如此肮脏的想法。所幸的是她分辨不出我有没有脸红。
女人听到旁边男子的呼声,晃悠着撇过头。她几乎转到让我看不到侧脸的角度,然而依然不妨碍我看她那妖娆的身材。
“好啊!那谢谢帅哥了。”
她声音优美而又近乎凄凉,然而说出这句话,整句的语气都各样变了味,我想那是种自嘲的神伤。
女人的回答似乎让男人近乎更加得寸进尺,男人伸出一只手搭在女人露出的肩膀上,白皙的皮肤,精致的锁骨,柔腻的触感,这些都是我想要的,然而这一切却被一个猥琐的大叔做了。在年龄上,我想是可以这么叫他的。
女人饱满而又挺拔的胸脯将衣服涨开,此时男人是站着一手搭在她肩上,然而他一脸显着平和而宁静的眼神却让我无可忍受。
女人似乎也注意到了男人不轨的手,她微微耸肩,摆着送酒入口的那只手想以颇为大的幅度摆脱它。
“美女,有没有兴趣去那里坐坐。”
男人指了指一角的卡座,三男三女围坐在沙发上玩闹,女人瞥了一眼便收回目光,寓意很明显。然而那男人似乎不肯放弃,又劝说几句,离走前不忘瞪了我一眼。酒吧的嘈杂声并不是很大,然而女人在回话的时候却又特意的靠近他耳边咬着说,所以除了他们最后离开前的几句话是我没听到外,大多谈话都被我窃密到,然而我任是深感无奈。但我也表示对于那男子离开前对我瞪眼甚感反感,我并不想他为什么。我只是对他瞪我之前却能够独自获取女人的蜜语而耿耿于怀。
此时酒吧内的人越来越多,嘈杂的声音分不清男人女人。在都市的夜生活中,放肆地释放跟压抑的积蓄成了一种循环节奏。逛逛夜店便成了一种解脱,男人夜晚出来花钱钓女人,于是夜场活动便成了女人最容易赚男人钱的时候。
来酒吧的人,此来的目的大抵之意只有几个,喝酒解闷、解愁,纯粹的借酒;要么玩一夜情,却也纯粹的借欲。然而方式只是在“借”。你可以看到充满着鲜活的生命与不足泄愤的欲,喘息的人,性欲的器官,便是活的就存在着腐的气息。狐媚妖娆的身姿,极尽癫狂的脑袋,或是染色的长发,或有剪短的服饰,便有没清醒的男人女人。声色犬马,大抵之意也不过这样。
从家乡出来后,每晚我都很晚才入眠。当一个人如同影子一样地跟着你、出现在你的梦里的时候,那便说明你不再想她,是的,我并不是很想记起,但是忘记却已扣上枷锁,让我身兼肉体的桎梏还要受到灵魂的冲撞。我并不是第一感受黑夜突袭而带来的荒凉与自我的忏悔,我也并不是第一次夜晚出来晃荡,但进酒吧却是第一次。人越来越多,尚且此时的环境氛围让我有些搞不清,我想回去。我刚准备起身走,但那女人叫住了我,第一次她跟我说话,问我不想知道为什么那男的瞪你吗?我没说话,但我摇了摇头,因为不重要。何况跟他我又不认识。
“就走?不多聊聊。”女人的脸上闪着灯光。灯光划过她的脸从她手中的酒杯划过,又从酒杯反射出另一道光,模模糊糊同周边所有道亮光重叠,同亮光重叠的那一瞬间,我看到了就像在夕阳的余晖里扑翅着的萤火虫,妖艳而美丽。
女人自然没留意到我会这样观察她。她的心全在猜测我这个人身上,我想她会的。她见我一时还没回答,便说还没看够吗?我说我看到了萤火虫。
“这儿哪有什么萤火虫,是说我吗?你肯定是个很会哄女人开心的人。”她朝我笑了笑,示意让我坐下来。
我开始想起第一次跟白薇抓萤火虫的时候。略微残缺的一轮苍白的月亮浮现在我眼前,左边是可以视见的农田,右边是万家灯火的景致。我最后一次见萤火虫是五年前,那也是我刚走出村子的时间。
我坐下来笑了笑,并未解释。
“萤火虫是夏日夜幕下拖曳的流光,是燃烧、灿烂的光芒。”
“很可惜我没见过。”
她的回答让我有点惊愕,我想她肯定失望,而我也会为没能分享自己的快乐的同时让她感到高兴而扫兴。对于让她接受未曾认知过的感受,我想是很难的。于是我便说有机会带她见识,她欣然应头说一言为定。后来我们说了很久,也喝了很多酒,我带她去了我住的房子,几乎进了房间,我便扑倒在床上。当然扑倒的还有她,她一路搀扶着我,近乎用光了所有力,被我扑倒的她毫无反抗之力,之后记不清我干了什么,只知中途胳膊感到疼痛。
次日醒来,阳光透过窗棂刺了进来,我近乎抱着脑袋坐了起来,脑袋一片昏沉而又伴着时有时无的疼痛。充裕的阳光下闹钟反射给我的时间是十点多。在那,衣服整齐的叠放在椅子上,而我又感到被子下赤裸着的身体是自己的,在扑朔迷离的记忆里,胳膊上的疼痛让我知道昨晚是多么的荒唐。她走了,带走了某些却也留下了一些。椅子上,在整齐的衣服旁边有一杯水,水杯下压着留有她写下的纸,纸上几句话便是她留给我醒来思维还畅游在梦中的呓语的证词。从此我记忆里开始有一个叫方洛女人的名字时常出现。
我穿上衣服,打开窗户,坐在床沿上。风吹动着窗帘,卷进一股一股清新的空气,我将方洛给我准备的水喝尽,拿起那张留给我的纸,寥寥几字一眼便可看至末尾,读完闭上眼,沉浸在漫无边际的思绪中,睁开眼我便觉得周围的现实世界黯然失色了。
“写给不要记起方洛的沐晨:记得将我给你做的早餐吃掉,早餐旁边还放有头疼的药,如果头还疼的话记得以热水送服,还有客厅的垃圾我给你打扫了一下,另外我拿走你钱包里的所有现金,就当是为你打扫客厅的劳务费,我知道住得起这房子的至少还不差钱,也就很放心的拿了,我知道你不会介意的,当然你也别愧疚太少。最后,谢谢你给我有种家的感觉。署名:方洛。”
我闭上眼,花了好长时间把自己的心收拢。在她带走的这些钱财中,却还想带走不该遗忘的,我知道她写的意思,但思念存想的我剥夺不了那份不安的悸动。
在这之后,我接到老板的电话,说有一批货要让我跑一趟。来电是下午四点接近五点的时候,而我尚还迷失在这间到处充满着白薇味道的房间里。在我读完她留下写满字迹的纸条之后,我便将她给我亲手做的早餐吃掉,虽然早餐本身并没什么丰富可言,但我吃得津津有味。并为此想到白薇如何将我乱糟糟的房子收拾干净。在沙发上将不太整齐的靠垫一个一个的摆放好,将沙发前的茶几上凌乱的书本以及放有两天多余的饭盒依次整理妥当且在临走前将垃圾桶内一个多礼拜未倒的垃圾跟之前打扫出来垃圾一次性通通带走并扔进楼下的垃圾箱内。
想到这,我几乎迫切的想走到她面前告诉她我并非是个邋遢的人且好好谢谢她,我可以请她在安静又华丽高贵的酒店内吃顿饭以示谢意,当然我得找到她。但她没留下任何电话就走了,并且想让我再也不要找她。
老板定的日期是后天,在走之前的两天,我每天夜晚都会来到这个第一次见到白薇的酒吧,我想见到她,然而时间回不到初遇。我想,我们有一个好好的开始却没能有一个好好的结束。每当走进酒吧,坐在那张空席的椅子旁,我脑海中首先浮现出来的,只有她的身影。接着,青草的芬芳,凉风的酥爽,山丘的弯曲,牧犬的吠声……接踵闯入脑海,而且那般的清晰,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上,我们来到了内蒙。但在一阵马儿羊群奔跑过之后,在那风景空无人影。谁都没有。白薇没有。沐晨也没有。羊群马儿也没有。我所能把握的,仅仅是这空不见人的背景而已。想有同她一起去旅游的想法便同幽谷的回音寻觅不得却难以忘怀。
但是,只要有时间,我总会想起她的面容。五年来我使劲忘记一个女人,却忘不掉;五年后我再想记起一个女人,却找不到。对于经历过让我坠入无尽的忏悔并已无法自拔的我来说,时间也成摇摇欲坠被棱角丝丝磨掉的藤蔓——抓住了却等不起。
一觉醒来,已是老板通知的定期,此时早上七点。我洗了把脸,刮了刮胡子,关上门。此趟又是来回一个礼拜的时间。走到街上,随便的吃了点早点,便打车去往地点。赶到时,十几个队员正等着我,一切也准备就绪,而我要做的也仅是作为一个领队来支配他们将这七辆车开往交货地点。至于送的什么货,我从来不问。也许因为这样使得老板很重用我。早在三年前,我就跟着师傅做,在我苦无投路的时候是师傅接济了我,于是便跟了他三年,在一个月前师傅出车祸死后我便接替了他的工作。一来跟师傅三年却也熟悉工作内容,二来为人机灵,该问不问,比别人多知晓一些处事之道,如此便被现在的老板看重并委以重任。
我坐在副驾驶座上。坐我旁边的主驾驶座上的男子他下身穿着深蓝的牛仔裤,上身灰色外套,面容偏瘦,小周就这样一边打着方向盘一边跟我说着话,然而就在刚刚他却突然对我说跑完这趟就辞职不做了。我比小周大两岁,小周才二十一,他刚干这行才一年多点,而我跟小周相处也才半年不到。他为人憨厚老实,个子不高却也有一米七,身材不壮甚至有些偏瘦然而却是个地道的东北人。他说要辞职不做时,我其实很惊讶,毕竟他才做了不是很久,尚且目前的工作并非很累工资还算挺满意。这样使我很疑惑不解。尚且我挺不愿意他走。我问起他时。
“回家结婚。”他说,“沐哥这几年回过家吗?”
“这么早就结婚。”说到回家脑海中几乎闪电般引发我的思绪,我从没想家,或者说我从没想回家,“五年没回去过了。”
“什么!哥竟然五年没回了。”他说,“哥不回去看下父母吗?”
小周如果注意我,就会看到我脸上牵动出的莫名的情绪,但他并没有。他在惊讶之余看了我一眼之后便又将心思放在了手中的方向盘上,倘若他会察言观色,也许就不会问出这句话。
“五年前死了。”我无比淡然的说出这句话,“老家没什么亲戚了。”
我并未解释父母是如何去世的,那是我脑海中并不想触碰的记忆。在这五年的时间里,我也未曾想试着去触摸,然而在那段空洞的精神世界的岁月中,总有一种东西出现在那接着取而替代以填补空洞部分的方式占据。并且以此占据五年之久。
小周看出我情绪有些伤感,就掏出一盒烟递给我,但他知道我并不抽烟,然而男人在不知道安慰男人的时候除了措手不及也就只剩下缄口不言。我所做的是在制造不安情绪的氛围,而他只是在陪同一起罢了。
在很长一段的行驶过程中,我们都很少开口。他出于前不久彼此不愉快的尴尬氛围刚慢慢缓解下来,所以也不大愿再开口,而我也不想再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