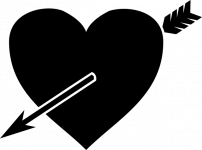领略大师风采,共赏杨朔散文(二)
也许你读过徐志摩的散文:淡雅中带着一抹愁绪;也许你读过张小娴的散文:温婉中带着一丝柔雅;也许你读过鲁迅先生的散文:激仰中带着一股风发。

文人笔下的世界都是多姿多彩、千变万化的。他们用同样的一种方式,却抒发了千万中不同。而这种情怀的载体就是——散文。
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散文集精选作者,他的散文无论是在托物寄情、还是写人、状、物都是诗意浓厚的。初看,带着疑惑,再看了然于心,细看豁然开朗。杨朔杨老,他就是有这种魅力,让你折服在他的文字中,耐人寻味。
——题记
1、《春在朝鲜》
我们并不健忘,还记得美国侵略者那句恶毒话:“把朝鲜变成沙漠!”
他们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我曾亲眼看见大片大片熟透的稻子被敌人浇上汽油,烧在地里;整棵整棵的苹果树被炸弹炸后,横在半山坡上……但是就在昨天烧毁的稻田里,土翻过来,满畦又插上碧绿的秧苗;就在昨天破坏的果树园里,东风一吹,满园摆动着一片彩云似的花朵。
春天突破风雪的重围,来到朝鲜。一位朝鲜无名诗人在我的手册上写道:春天是美好的,为了建设我们像春天一样美好的生活,我们不惜用血汗去浇灌生活!
这几句诗,正表现了朝鲜人民不可征服的意志。我曾经听过朝鲜中央农民同盟副委员长金时哉的报告,讲到美国强盗的滔天罪恶时,他举出几个数目字说:仅仅黄海道一带,被害的农民就有十几万人,平安南道被杀死的牛一共就是两万七千多头。全朝鲜受害的情形,可想而知。人力缺,畜力缺,朝鲜的土地不就荒了?这是敌人的愿望,事实可不如此。
平壤有个农民,叫宋景稷,穿着青袍子,大领子镶着白边,脸上的表情凝滞而刚毅,一望就知道他内心隐藏着绝大的悲痛。他怎能不痛心呢?敌人占领平壤时,他撤到北地,解放后回家一看,全家连亲属二十五口,统统叫敌人残杀了。他家只剩他一个人,但他的背后却有无比的人民力量支持着他。我见到他时,他对我们说:“敌人杀死我的家口,杀不死我的心!我要献出整个生命,跟敌人斗争!”
春天一来,当金日成将军发出号召:“播种就是战争!”宋景稷,以及千千万万像他这样的农民,都投进这个战争里了。壮年男子上了前线,妇女儿童都组织起来,集体下地。白天怕敌机骚扰,地头挖上防空洞;日里做不完,月亮地再去。朝朝夜夜,你时常可以看见一伙一伙的妇女,有的背上背着小孩,拉犁的拉犁,撒种的撒种,后边的妇女站成一溜,背着手,哼着歌,踏着像舞蹈的步子,用两脚培着土。太阳影里,忽然会闪出一群青年战士,一个个生龙活虎似的,浑身充满精力。这是中国志愿军来了。他们身上还带着弹药的气味,脸上蒙着战场的风尘,刚从火线下来,就架起枪,甘心情愿替朝鲜人民当老年,拉起犁耍着欢跑。那些妇女没法表示她们的感谢了,少女们跑进沟去,一霎眼又跑回来,满怀抱着大把的野迎春,“金大莱”花,格格地笑着,一把一把塞到战士们的手里……
有一回,我也从一位少女手里接到过一大捧粉红色的“金大莱”花,不过不是在田野,而是在工厂里。那少女叫闵顺女,才十六岁,是一家纺织工厂的热情劳动者(积极分子)。但她前些时候曾经不大安心做事。翻译同志说:“她一心一意只想参军,替父亲报仇。”原来她父亲是纺织厂的木匠,去年十一月叫美军绑去了,顺女母女跟一个八岁的小兄弟也叫绑去了。美军故意当着她母女的面,把她父亲拖出来。那时她父亲已经被打的浑身是血,不能走路。八岁的小兄弟哭起来,她父亲说:“我就要死了,记住我是怎么死的……”没等话说完,敌人就叫她们母女看着,开枪把她父亲打死,死后还用脚踢!这个仇,顺女记在心里,睡觉也不能忘。头些天动员参军,她带着饭,抢着去报名,可是年纪太小,不合格,急的她什么似的,天天去要求,后来允许她参加工厂武装自卫队,才算安心。现在她亲自订出生产计划,二十天就完成了过去要三十天才能完成的工作。有些工友上前线,送他们走时,顺女说:“你们放心走吧,我们一定完成你们所要完成的任务!”
这就是从美国侵略者造成的血海深仇中锻炼出来的朝鲜工人。他们都明白一个真理:“没有前方就没有后方,没有后方就没有前方!”一座城市刚解放,纺织工厂的电力全部被敌人破坏了。不首先恢复电力,就不能恢复生产。斐东奎带着六个电工进行修复工作,因为当地弄不到粮食,天天半饥半饱。在二十米高的高压线上工作时,敌机轰炸也不下来,五天光景,到底修好了,机器也转了。原班人马,再一个五天,农具工厂的电力也恢复起来了。这些工人,就这样顽强。生产一开始,敌机不到头上,工人决不停手。白天做活,夜晚还去修路。不修路,中朝人民大军如何前进?向祖国,向人民,他们又普遍展开宣誓运动:“不论在任何艰苦情况下,坚决执行祖国所给的使命!”
在一次夜会上,一家谷产工厂热烈招待了我们一群从中国来的朋友。棹子上摆着酒,饼干、白糖、酱油等等。头上的飞机嗡嗡响,炸弹震的房子乱摇,工人们却像山一样镇定,脸色不改。一个工人举起酒杯说:“今天招待客人的东西,非常简陋,不过这是我们工厂恢复后第一批出品,主要是为了保证前线的供给。”
我们的同志立刻擎着杯子站起身说:“请喝这一杯胜利酒!这酒是在敌人轰炸破坏下出的,不但表现了朝鲜人民生产的胜利,也保证了前线战争的胜利!”
春天来到朝鲜。朝鲜人民用血汗浇灌的生活,定会开出美丽的花朵。那些挂着文明幌子的食人生番不能扳着地球倒转,就永远不能毁灭光明灿烂的世界。还记得一夜我乘车路过平壤,瓦砾场上忽然有播音器传出雄壮的歌声。这是“金日成将军之歌”,也是朝鲜人民的战歌。踏着这个战歌,朝鲜人民正在走向人类永久的春天。
2、《戈壁滩上的春天》
四月底了。要在北京,这时候正是百花盛开的好季节。但在戈壁滩上,节气还早着呢。一出嘉峪关,你望吧,满眼是无边的砂石,遍地只有一丛一丛的骆驼草,略略透出点绿意。四处有的是旋风,一股一股的,把黄沙卷起多高,像是平地冒起的大烟,打着转在沙漠上飞跑。说声变天,一起风,半空就飘起雪花来。紧靠戈壁滩的西南边是起伏不断的祁连山,三伏天,山头也披着白雪。
可是不管你走的多远,走到多么荒寒的地方,你也会看见我们人民为祖国所创造的奇迹。就在这戈壁滩上,就在这祁连山下,我们来自祖国各地的人民从地下钻出石油,在沙漠上建设起一座出色的“石油城”。这就是玉门油矿。不信,你黑夜站到个高岗上,张眼一望,戈壁滩上远远近近全是电灯,比天上的星星都密。北面天边亮起一片红光,忽闪忽闪的,是炼油厂在炼油了。你心里定会赞叹说:“多好的地方啊!哪像是在沙漠上呢?”
但我们究竟还是在沙漠上。这里的每块砖,每块石头,每滴石油,都沾着我们人民的汗,都藏着我们人民的生命。我们不能不感谢那些地质勘探队。他们为了继续替祖国寻找石油,骑着骆驼,带着蒙古包和干粮,远远地深入到荒凉的大沙漠里去,多少天见不到个人。只有沙漠上的黄羊,山里的野马,有时惊惊惶惶跟他们打个照面。我见过这样一队人,他们多半是男女青年学生,离开学校门还不久。当中有几个女同志,爱说爱笑,都是江南人。姓邓的年轻队长告诉我说,刚离开上海到西北时,女同志有时嫌饭不干净,宁肯饿一顿,也不吃。罡风吹裂了她们的脸,她们的手。这儿地势又高,空气薄,动一动,就会闷得透不过气来。一种爱祖国的热情使她们什么都忘了。她们也愁,愁的是工作。哪一天勘探成绩不好,你看吧,从野外回来时,一点声音都没有。只要稍微有点成绩,就该拿着成绩到处给人看,笑翻天了。
碰巧有这样事。勘探队的同志正拿着仪器测量地形,一个骑骆驼路过的蒙古人会跳下来问:“你们照出油来没有?”就是在荒漠上,人民对他们的劳动也显得多么关心。他们明白这点,他们情愿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人民的事业。多好的年轻人啊。
我们更该牢记着那成千成万的石油工人。哪儿发现了石油构造,他们就到哪儿去打井钻探。有一回,我随一个叫王登学的小队长远离开那座“石油城”,走进祁连山里。工人们早在荒山里装起机器,架好钻台,正用大钻机日夜不停地打油井。每人都戴着顶闪亮的铝盔,穿着高统牛皮靴子。样子很英武。
我笑着说:“你们这不像战士一样了?”
王登学说:“人家志愿军在朝鲜前线卧冰趴雪的,咱这算什么?”
其实工人们对自然界的战斗也是很艰苦的。腊月天,戈壁滩上飘风扬雪的,石头都冻崩了。通宵通夜,工人们也要在露天地里操纵着钻机。天太冷,用手一摸机器,手套都会沾上了。休息一下吧。还休息呢?志愿军在前方打仗,坦克,汽车,哪样不得汽油?再说咱也是建设祖国嘛,谁顾得上休息?
他们就不休息,就像战士作战一样顽强勇敢。钻工当中也真有战士呢。我见到一个青年,叫蔡广庆,脸红红的,眉眼很俊,一问,才知道他参加过解放战争。现在,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毛主席叫咱到哪,咱就到哪。”在生产战线上,这个转业军人十足显出了他的战斗精神。他对我说:“咱部队下来的,再困难,也没有战斗困难。什么都不怕,学就行。”一听说我是从朝鲜前线回来参观祖国建设的,蔡广庆一把抓住我的手说:“你回去告诉同志们吧,我们要把祁连山打通,戈壁滩打透,叫石油像河一样流,来支援前线,来建设我们的祖国!”
这不只是英雄的豪语,我们的人民正是用这种精神来开发祖国地下的宝藏。这里不但打新井,还修复废井。有多少好油田,叫国民党反动政府给毁坏了。当时敌人只知道要油,乱打井。油忽然会从地里喷出来,一直喷几个星期,油层破坏了,井也废了。都是祖国的财产,谁能丢了不管?老工人刘公之便是修井的能手。修着修着,泥浆从井里喷出来了。喷到手上,脸上,滚烫滚烫的。皮都烧烂了。刘公之这人表面很迟钝,心眼可灵。凭他的经验,他弄明白这是地里淤气顶的泥浆喷,并不是油层。喷就喷吧,喷过去,他带着烫伤照样指挥修井。一口、两口……废井复活了,油像喷泉似的从地下涌出来了。
石油——这要经过我们人民多少劳力,从地底下探出来,炼成不同的油类,才能输送到祖国的各个角落去。一滴油一滴汗,每滴油都是我们祖国所需要的血液啊。我不能忘记一段情景。有一天晚间,我坐着油矿运油的汽车奔跑在西北大道上。一路上,只见运油的大卡车都亮着灯。来来往往,白天黑夜不间断,紧张得很。这情景,倒很像朝鲜战场上黑夜所见的。坐在我旁边的汽车司机是个满精干的小伙子。开着车呜呜地飞跑。我望望车外,公路两旁黑茫茫的,显得很荒远。
我不禁大声说:“开得好快呀!”
司机大声应道:“要奔个目标呢。”
我又问道:“是奔张掖么?”
司机摇摇头喊:“不是,还远着呢。”
我忽然记起上车时,司机位子上放着本日记。我曾经拿起那本日记翻了翻,记得第一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我就俯到司机的耳朵上笑着喊:“你是往社会主义的目标上奔吧?”
司机咧着嘴笑了。我又望望车外,一时觉得大路两旁不再是遥远的边塞,好像满是树,满是花,满是人烟。事实上,春天已经透过骆驼草、芨芨草、红沙柳,悄悄来到戈壁滩上了。但我还看见另一种春天。这不是平常的春天。这是我们人民正在动手创造的灿烂的好光景。
3、《滇池边上的报春花》
自古以来,人们常有个梦想,但愿世间花不谢,叶不落,一年到头永远是春天。这样的境界自然寻不到,只好望着缥缥缈缈的半天空,把梦想寄到云彩里。
究其实,天上也找不到这种好地方。现时我就在云里。飞机正越过一带大山,飞得极高,腾到云彩上头去。往下一看,云头铺得又厚又严,一朵紧挤着一朵,好像滚滚的浪头,使你恍惚觉得正飞在一片白浪滔天的大海上。云彩上头又是碧蓝碧蓝的天,比洗的还干净,别的什么都不见。
可是,赶飞机冲开云雾,稳稳当当落到地面上,我发觉自己真正来到个奇妙的地方,花啊,草啊,叫都叫不上名,终年不断,恰恰是我们梦想的四季长春的世界。不用我点破,谁都猜的着这是昆明了。
人家告诉我说,到昆明来,最好是夏天或是冬天。六七月间,到处热得像蒸笼,昆明的天气却像三四月,不冷不热。要是冬天,你从北地来,满身带着霜雪,一到昆明,准会叫起来:“哎呀!怎么还开花呢?”正开的是茶花。白的,红的,各种各样,色彩那么鲜亮,你见了,心都会乐得发颤。
说起昆明的花木,真正别致。最有名的三种花是茶花、杜鹃花,还有报春花。昆明的四季并不明显,年年按节气春天一露头,山脚下,田边上,就开了各种花,有宝蓝色,有玫瑰红,密密丛丛,满眼都是。花好,开的时候也好,难怪人人都爱这种报春花。还有别的奇花异木:昙花本来是稀罕物件,这儿的昙花却长成大树;象鼻莲(仙人掌一类植物)多半是盆栽,这儿的象鼻莲能长到一丈多高,还开大花;茶花高得可以拴马;有一种豌豆也结在大树上。
其实昆明也并非什么神奇的地方,说穿了,丝毫不怪。这儿属于亚热带,但又坐落在云贵高原上,正当着喜马拉雅山的横断山脉,海拔相当高,北面的高山又挡住了从北方吹来的寒风,几方面条件一调节,自然就冷热均匀,长年都像春天了。
可惜我是秋天来的。茶花刚开,滇池水面上疏疏落落浮着雪白的海菜花,很像睡莲。我喜欢昆明,最喜欢的还是滇池,也叫昆明湖。那天,我上了昆明城外的西山,顺着石磴一直爬到“龙门”高头,倚着石栏杆一望:好啊!这方圆二百里的高原上的大湖,浩浩荡荡,莽莽苍苍,湖心飘着几片渔帆,实在好看。
我偏着身子想坐到石栏杆上,一位同伴急忙伸手一拦说:“别!别!”原来石栏杆外就是直上直下的峭壁,足有几十丈高,紧临着滇池。
另一位同志笑着接嘴说:“你掉下去,就变成传说里的人物了。”跟着指给我看“龙门”附近一个石刻的魁星,又问道:“你看有什么缺陷没有?”
我看不出,经他一指,才发觉那魁星原本是整块石头刻的,只有手里拿的笔是用木头另装上的。于是那位同伴说了个故事。传说古时候有个好人,爱上个姑娘,没能达到心愿,一发恨,就到西山去刻“龙门”。刻了个石魁星,什么都完完全全的,刻到最后,单单没有石头来刻笔。那人追求生活不能圆满,又去追求艺术,谁知又不圆满,伤心到极点,就从“龙门”跳下去,跌死了。可见昆明这地方虽美,先前人的生活可并不完美。曾经充满了痛苦,充满了眼泪。痛苦对少数民族的兄弟姐妹来说更深。云南的民族向来多。那云岭,那怒山,那高黎贡山,哪座山上的杜鹃花不染着我们兄弟民族的血泪?
我见到一个独龙族的姑娘,叫嫒娜,是第三的意思。她只有十八岁,梳着双辫,穿着白色长袍,斜披着一条花格子布披肩,脖子上挂着好些串大大小小的玻璃珠子。见了生人也不怯,老是嘻嘻,嘻嘻,无缘无故就发笑。旁人说话,她从旁边望着你的嘴,嗤地笑了。人家对她说:“你穿的真好看啊!”她用手捂着嘴,缩着肩膀,拚命憋住不笑。人家再问她:“你怎么这样爱笑?”她把脸藏到女伴背后,格格地笑出声来。我让她吃糖,她才不会假客气呢,拿起块樱桃糖,用大拇指和食指捏着,送到嘴边上咂一会,抽出来看看,又咂一会,又抽出来看看,忙个不停,一面还要说话,还要笑。她说她的生活。她的性格那么欢乐,你几乎不能相信她会有什么痛苦。
嫒娜用又急又快的调子说:“我家里有母亲,还有兄妹,都住在大山上。早些年平地叫汉人的地主霸占光了,哪有我们站脚的地方?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在大山上,跟野兽也差不多,就在树林子里盖间草房,屋子当中笼起堆火,一家人围着火睡在地上。全家只有一把刀,砍了树,放火烧烧山,种上包谷,才能有吃的。国民党兵一来,还要给你抢光。没办法,只得挖药材,打野兽。用弓弩打。打到麝香、鹿、熊、野猪、飞鼠一类东西,拿到山下,碰上国民党,也给你抢走。那时候谁见过鞋子?谁穿过正经衣裳?”
说到这里,嫒娜咧开嘴笑了。她把糖完全含到嘴里,腾出手来掩着自己的胸口,歪着头笑道:“你看我现时穿的好不好?”
她说话的口气很怪,总是笑,倒像是谈着跟自己漠不相关的事。实际也不怪,再听下去,你就懂得她的心情了。
嫒娜继续说:“一解放,人民政府每家给了三把锄头,几年光景,我们家开了一百多亩水田,早有稻子吃了。这是几百年几千年也没有的事,好像死了又活了。”
过去的事已经埋葬,这位年轻的独龙姑娘从头到脚都浸到新的欢情里,怎么能怪她老是爱笑?
但是过去的事并不能连根铲掉,痛苦给她刻下了永久不灭的记号。嫒娜的脸上刺满绿色的花点,刺的是朵莲花。我很想问问她文面的原因,又怕碰了她的痛处,不大好问。嫒娜自动告诉我说:“不刺脸,国民党兵见你年轻,就给拉走。刺上花,脸丑了,就不要了。那工夫,谁不害怕当兵的啊!怕死人了。看穿黄衣服的大家都往山上跑。”
我故意问她道:“现在你还怕穿黄衣服的么?”
嫒娜指着自己的前胸反问道:“你说我么?”便用手背一掩嘴,笑出声说:“我还要相赶着找穿黄衣服的呢。”
嫒娜找的自然是解放军。在云南边疆上,我们解放军的战士跟少数民族烧一座山上的柴,喝一条河里的水,多少年来在各民族间造成的隔阂和冤仇逐渐消失,互相建立起手足般的感情。这种感情是从生死斗争里发展起来的。
我想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有一班战士驻扎在边境上一个景颇族的寨子里,隔一条河便是缅甸,那边深山密林里藏着些亡命的蒋军,有时偷过境来打劫人民。这一班战士就为保护人民来的。有一晚上,三百多个匪徒溜过来,突然把寨子围住,天一破亮,开火了。我们只有十几个战士,当时分散开,顶住了敌人。从拂晓足足打到黄昏,战士都坚持在原地上不动,饿了,便拔眼前的野草吃。
班长亲自掌握机枪,一条腿打断,又一条腿也打断,不能动了。
匪徒们觉得这边支持不住,不停地喊:“交枪!交枪!”
班长忍着痛撑起上半身喊:“好,你们过来吧,我们交枪。”
匪徒们涌上来。班长叫“慌什么?你接着吧!”一阵机枪扫过去,扫倒敌人一大片。这时,又一颗子弹飞过来,打中班长的腰。班长松了机枪,歪到地上,还用两手钩着两颗手榴弹的弦,对他的战士喊:“我们要保卫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最后趁着夜色,党的小组长带着人突出包围圈,占了制高点,打了排手榴弹,朝敌人直冲下去。敌人被冲垮了,乱纷纷逃出国境去。
景颇族的农民围着昏迷不醒的班长说:“都是为的我们啊!”
这些兄弟民族对解放军真是爱护得很,有时成群结队敲着象脚鼓,老远来给军队送东西。譬如有一回,庄稼闹虫灾,战士们帮着打虫子,天天雨淋日晒,脊梁曝了层皮,两条腿站在水田里,蚂蟥又咬,膝盖以下咬的满是血泡,糟的不像样子。虫子打完,赶收成时,农民争着尽先把新米送给战士。按景颇族的老规矩,头一把新米应该先供祖宗,给最有德望的老人吃。战士们不肯收,说是不配先吃。农民嚷着说:“不先给你们吃给谁呢?”
在昆明,我看过一次十分出色的晚会。有阿细跳月,有景颇族的长刀舞,有彝族的戽小细鱼舞,有汉族的采茶花灯,还有许多其他民族的歌舞。这些歌舞是那么有色彩,那么有风情,那么欢乐,而又那么热烈,使你永远也不能忘记。晚会演完谢幕时,所有的演员都站到台前,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鲜明漂亮,好看极了。
当地一位朋友拉拉我的衣袖笑着说:“你不是想看看云南有名的报春花么?这不是,就在你眼前。”
眼前这样多不同民族的青年紧靠在一起,五颜六色,神采飞舞,一定很像盛开的报春花。只是报的并非自然界的春天,却是各民族生活里的春天。
只有今天,古人追求不到的圆满东西,我们可以追求到了。
也只有今天,昆明才真正出现了长年不谢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