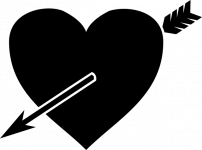为文学而生,迟子建散文欣赏(下)
迟子建认为作家写作应该要依靠心灵的力量,而从读者角度看来,她写作的状态也的确是这样的。她文章中的题材通常都不大,写平凡人平凡事,不紧不慢,娓娓道来。这个喧嚣的时代需要这样的作家。

并非思想不深刻,并非走过的路太少。她所拥有的精神世界很大很大,而浓缩成的写作的世界却很小很小,从而不至于迷失。就像只给读者开一个小缺口,慢慢品味,细水长流。
9、《寻石记》
我们童年所做的游戏,稍微有点新意的,也不外乎让一个小伙伴扮成白军,我们一伙红军四处去抓他。一抓总能抓得到,他不是藏在柴垛后面,就是躲在狗窝里。每次白军被垂头丧气地捉住的时候我都要想:白军真蠢啊,怪不得胜利的是红军呢!
这些游戏玩得腻了,有一天我们突发奇想,想砸家里的石头玩。听说石头能砸出火花,火花在白天看时不明显,须等到夜里来砸,才能把那火花看得真切和灿烂。
一般的人家都有一块大石头,是冬季用来腌酸菜的。夏季时,这石头闲在院子里,人们就把它当成板凳来使了。老人们坐在上面吸烟锅,女人坐在那里补衣裳。有的时候鸡也会跳上去,在上面叽叽咯咯地叫着,好像那石头是它下的蛋似的。
终于有一个傍晚父母去邻居家串门了。我便与几个小伙伴砸家中的那块青石。它方头方脑的,大约有二十斤重吧,我们每砸一下,都要跳起来为着迸射出来的银白色的火花而欢呼一番,直到它被砸碎为止。
次日清晨,我被母亲给从被窝中揪出来。她呵斥我:“你给我去找个一模一样的石头回来,要不我就剁掉你的贱手!”那石头我们家年复一年地用着,成了我们的老熟人了,它的破碎自然要让母亲大发雷霆的。
我就不信我找不到一块石头,那样我不就跟白军一样愚蠢了么!我穿上衣服冲出家门,朝河岸走去,我印象中水里有大石头。刚到河畔,就见邻村的打鱼人在收网,他问我一个小孩子这么早出来干什么?我如实说了,他就告诉我说,河里的石头动不得,石头底下藏着龙,我要是搬了石头,龙就会伸出尖爪子把我钩住。
我想河里的石头动不得,山上峭壁旁的石头应该能让人动的。我朝山上走去。到了那里时,正碰上同村的赤脚医生在采药材。他问我一个小女孩走这么远的路,来这里干什么?我说要搬一块石头回家。他就笑着对我说,峭壁旁的石头动不得,它们是山神胸脯上的一块块肌肉,你动一块,等于在山神身上割了一块肉。
既然石头都有它们自己的来历和用场,我就空着手理直气壮地回家了。
母亲根本就不相信她清晨时的一句气话竟然使我独自出去寻石头,更不相信我听到的这些传说。她嗔怪我说:“我看你不用出去找石头了,你自己就是一块石头!”
我真的是石头么?如果是,我可不想做家中的那块石头。我要做山上的石头听风雨,要做水底的石头亲吻鱼。
10、《我的梦开始的地方》
从中国的版图上看,我的出生地漠河居于最北,大约在北纬53度左右。那是一个小村子,依山傍水,风景优美,每年有多半的时间白雪飘飘。我记忆最深刻的,是那里漫长的寒冷,冬天似乎总也过不完。
我小的时候住在外婆家里,那是一座高大的木刻楞房子,房前屋后是广阔的菜园。短暂的夏季来临的时候,菜园就被种上了各色庄稼和花草,有的是让人吃的东西,如黄瓜、茄子、倭瓜、豆角、苞米等;有的则纯粹是供人观赏的,如矢车菊、爬山虎、大类花(罂栗)等等。当然,也有半是观赏半是入口的植物,如向日葵。一到昼长夜短的夏天,这形形色色的植物就几近疯狂地生长着,它们似乎知道属于它们的日子是微乎其微的。我经常看见的一种情形就是,当某一种植物还在旺盛的生命期的时候,秋霜却不期而至,所有的植物在一夜之间就憔悴了。这种大自然的风云变幻所带来的植物的被迫凋零令人痛心和震撼。
我对人生最初的认识,完全是从自然界的一些变化而感悟来的。比如我从凋零的植物身上看到了生命的脆弱,同时我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到了生命的从容,因为许多衰亡的植物,转年又会焕发出勃勃生机,看上去比前一年似乎更加有朝气。
童年围绕着我的,除了那些可爱的植物,还有亲人和动物。请原谅我把他们并列放在一起来谈。因为在我看来,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的亲人,也许是由于身处民风纯朴的边塞,他们是那么善良、隐忍、宽厚,爱意总是那么不经意地写在他们的脸上,让人觉得生活里到处是融融暖意。我从他们身上,领略最多的就是那种随遇而安的平和与超然,这几乎决定了我成年以后的人生观。
在我的作品中,出现最多的除了故乡的亲人,就是那些从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动物,这些事物在我的故事中是经久不衰的。比如《逝川》中会流泪的鱼;《雾月牛栏》中因为初次见到阳光、怕自己的蹄子把阳光给踩碎了而缩着身子走路的牛;《北极村童话》里的那条名叫“傻子”的狗;《鸭如花》中的那些如花似玉的鸭子等等。
此外,我还对童年时所领略到的那种种奇异的风景情有独钟,譬如铺天盖地的大雪、轰轰烈烈的晚霞、波光荡漾的河水、开满了花朵的土豆地、被麻雀包围的旧窑厂、秋日雨后出现的像繁星一样多的蘑菇、在雪地上飞驰的雪橇、千年不遇的日全食等等,我对它们是怀有热爱之情的,它们进入我的小说,会使我在写作时洋溢着一股充沛的激情。我甚至觉得,这些风景比人物更有感情和光彩,它们出现在我的笔端,仿佛不是一个个汉字在次第呈现,而是一群在大森林中歌唱的夜莺。
在这样一片充满了灵性的土地上,神话和传说几乎到处都是……
也许是因为神话的滋养,我记忆中的房屋、牛栏、猪舍、菜园、坟茔、山川河流、日月星辰等等,它们无一不沾染了神话的色彩和气韵,我笔下的人物也无法逃脱它们的笼罩。我所理解的活生生的人,不是庸常所指的按现实规律生活的人,而是被神灵之光包围的人,那是一群有个性和光彩的人。他们也许会有种种的缺陷,但他们忠实于自己的内心生活,从人性的意义来讲,只有他们才值得永恒的抒写。
还有梦境。也许是我童年生活的环境与大自然紧紧相拥的缘故吧,我特别喜欢做一些色彩斑斓的梦。我听到过的一处河湾,在现实中它是浅蓝色的,可在梦里它却焕发出彩虹一样的妖娆颜色。我在梦里还见过会发光的树,能够飞翔的鱼,狂奔的猎狗和浓云密布的天空。有时也梦见人,这人多半是已经作了古的,我们称之为“鬼”的,他们与我娓娓讲述着生活的故事,一如他们活着。我常想,一个人的一生是在睡眠中度过的,假如你活了八十岁,有四十年是在做梦的,究竟哪一种生活和画面更是真实的人生呢?梦境里的流水和夕阳总是带有某种伤感的意味,梦里的动物有的凶猛有的则温情脉脉。有时我想,梦境也是一种现实,而且,梦境的语言具有永恒性,只要你有呼吸、有思维,它就无休止地出现,给人带来无穷无尽的联想。它们就像盛宴上酒杯碰撞后所发出的清脆温暖的响声,令人回味。
当我童年在故乡北极村生活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认定世界就北极村这么大。当我成年以后到过了许多地方,见到了更多的人和更绚丽的风景之后,我回过头来一想,世界其实还是那么大,它只是一个小的北极村。
11、《锁在深处的蜜》
大兴安岭与内蒙古接壤,草原,牛羊,牧人的歌声,对我来讲,都是邻家的风景,并不陌生。
三年前,为了搜集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素材,我来到了内蒙古。从海拉尔,经达赉湖,至边境的满洲里后向回转,横穿呼伦贝尔大草原,到根河。那是八月,草色已不鲜润了,但广阔的草原和草原上的牛羊,还是让人无比陶醉。天空离大地很近的样子,所以飘拂着的白云,总疑心它们要掉下来。中途歇脚的时候,我在牧民的毡房里喝奶茶,吃手抓羊肉,听他们谈笑,心底渐渐泛起依恋之情,真想把客栈当作家,长住下来。然而,我于草原,不过是个匆匆过客。
我在写作疲惫时,喜欢回忆走过的大自然。呼伦贝尔草原上的风景,就是在这样的时刻,悄悄浮现在我脑海中的。它们初始时是雾气,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它们生长起来了,由轻雾转为浓云,终于,有一天,我想象的世界电闪雷鸣的,我看见了草原,听到了牧歌,一个骑马的蒙古人出现了,中秋节的月亮出来了。就这样,几年前的记忆被唤醒,草原从我的笔端流淌出来了。
如果问我最爱《草原》中的哪个人?我会说:阿荣吉的老婆子!我喜欢这个恋酒的、隐忍的、放牧着羊群的、年年夏天去阿尔泰家牧场唱歌的女人。人生的苦难有多少种,爱情大概就有多少种。在我眼里,她和阿尔泰之间,是发生了伟大的爱情的。这种失意的、辛酸的爱情,内里洋溢的却是质朴、温暖的气息,我喜欢这气息。常有批评家善意地提醒我,对温暖的表达要节制,可在我眼里,对“恶”和“残忍”的表达要节制,而对温暖,是不需要节制的。因为从某种意义来讲,温暖代表着宗教的精神啊。有很多人误解了“温暖”,以为它的背后,是简单的“诗情画意”,其实不然。真正的温暖,是从苍凉和苦难中生成的!能在浮华的人世间,拾取这一脉温暖,让我觉得生命还是灿烂的。
一百四十多年前,达尔文看到一株来自热带雨林的兰花,发现它的花蜜藏在花茎下十二寸的地方,于是预言将有一只有着同等舌头长度的巨蛾,生长在热带雨林。当时很多生物学家认为他这是“疯狂的想法”。可是一百多年后,在热带雨林,野外考察的科学家,发现了巨蛾!通过电视,我看到了摄像机拍到的那个动人的瞬间:一株兰花,在热带雨林的夜晚安闲地开放着,忽然,一只巨蛾,飘飘洒洒地朝兰花飞来。它落到兰花上,将那柔软的、长长的舌头,一点一点地蓄进花蕊,随着那针似的舌头渐渐地探到花蕊深处,我的心狂跳着,因为我知道,巨蛾就要吮到花蜜了!
那锁在深处的蜜,只为一种生灵而生。这样的花蜜,带着股拒世的傲气,让人感动。其实只要是花蜜,不管它藏得多么深,总会有与之相配的生灵发现它。从这个角度来说,任何的写作者,都是幸福的。因为这世上,真正的“酿造”,是不会被埋没和尘封的。
12、《俄罗斯:泥泞中的春天》
俄罗斯当代油画来到哈尔滨,就像邻居的一个农人,用旧式马车载来了一车摞起来的篮子。你拎下一篮:哦,原来是黄熟了的麦穗!再提下一篮:啊,是姹紫嫣红的花朵!当你被花朵的芬芳所陶醉时,又一篮新鲜的水果朝你眨着水灵灵的大眼了。你把篮子一个个从车上卸下,发现那里面还有刚出炉的面包、碧绿的蔬菜、肥嘟嘟的鱼、散发着松香气的劈柴、毛茸茸的小狗、羽毛丽的鸡和闪着银光的瓷盘。
透过这些静物,我们能看到生养了它们的土地、森林、河流、房屋、果园、炉台等人间景致,当然,还能看到烘托了这一切的天上圣景:如火的晚霞、洁白的云朵、蛇一样飞舞的雷电以及星光灿烂的银河。
这就是俄罗斯当代油画给我的第一眼印象,既有扑面而来的热烈奔放的人间烟火气息,又有生就的忧郁和高贵之气。
这些油画创作年代较早的,应该是弗里德曼的《雪融》、索洛金的《契诃夫在叶尼塞河边》、兹韦尔科夫的《多云的天气》、罗基奥诺夫夫妇的《车间里》、瓦伊什利亚的《霍鲁伊镇的泥泞》、苏达科夫的《猎手》以及马克西莫夫的一些作品。这些诞生于苏联解体前的作品,深沉、凝重、大气,你能透过苍凉的画面,感受到这个民族勃勃的心跳,听到他们灵魂深处的歌唱。
一个大国的解体,如同一颗巨石陨落,它弥散的尘埃带给艺术家的精神苦闷可想而知。有一小部分画作用色花哨、轻飘,表现的主题简单、贫乏,细看创作年代,都是苏联刚刚解体的那几年的作品。只有内心世界空虚和寂寞,画家才会使用令人眼花缭乱的色彩,以掩饰内心的不安和焦躁。相反,内心世界饱满丰富的时候,我们能从单一的色彩中感受出夺目的绚丽。
然而俄罗斯毕竟是俄罗斯,它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就如同希施金《在遥远的北方》中描绘的那棵山崖上苍劲的雪松一样,威严而华美,所以画家们很快又能从短暂的骚动中回归传统。就我看到的这些油画来讲,近几年的作品又呈现着博大、深沉的气象了。比如波利卡尔波夫的《春汛》,索罗明·尼古拉的《农村》《林中水洼》《空手而归》,柴尼科夫的《报春花》,阿廖欣的《雪橇》,依力诺娃的《一生》,奥尔洛夫·维克多的《农家花园》等。在这些画作中,我们能看到生机盎然地浸在春水中的树木,晶莹得如孩童眼睛一般的水洼,寒流中温暖的使者———雪橇,以及依偎在农家花园前的、像一顶枝形吊灯一样散发着光明的太阳花。当然,我们也看到了人:穿着白袍子孤寂地坐在沙发上的老女人、依栏而歇的空手而归的猎人、穿着红衣戴着红帽的女驯马师。
我两次去看俄罗斯当代油画展,虽然展厅闷热难当,可我却从这些画作上感受到了如水的清凉。那河畔的轻雾、花朵上的露滴,已经悄悄滑入我心深处。
我最喜欢的,是那幅《霍鲁伊镇的泥泞》,看到它,我的眼睛会湿润。这样的泥泞我再熟悉不过了。一个人的命运同一个国家的命运一样,总是在经历了巨大的磨难后才更加有前行的勇气。能在深重的泥泞中跋涉而行,也是一种幸福啊。俄罗斯的春天,正因为脱胎于这样的泥泞,异常的壮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