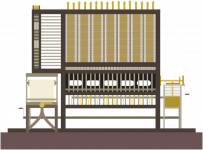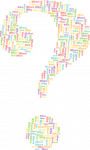千里之行——生命
下了飞机,联系小姨,知道接下来的路程。打了个出租车,从江北飞机场到龙头市车站,花了我整整三十五块,心疼的同时不禁感叹如今纸币实在廉价。算下来,今天单是打的就花了差不多100块钱,所走的路途不过数十里。无奈地摇了摇头,往车站的位置走去。

身上的现金几乎用完,只剩下不到70块钱。在周围打听从龙头市车站到忠县车站所需的费用,大约90块钱。没办法,只能找一个能取钱的银行或者自动取款机。但无奈,人生地不熟,在车站里转了几圈还是找不到能够取钱的地方。怀揣着六十几块钱,实在没有办法在车站里买到客车车票。
走出车站,在周围转了一圈,身边围上来好几个人。就像腐烂的肉块周围,吸引了无数苍蝇。我虽无心情,也无耐心和他们打交道,却也不会恶脸相向。他们都是为了生活,也只是迫不得已的一群人,在这么寒冷的天,还得来为私家面包车招徕顾客,从中赚取一定的佣金。虽然无数次凑上来,一次次询问让人感到不快,却也没有任何理由迁怒。活着,他们也不容易。
和一个女人谈好了价钱,八十块钱,我付给她十块钱,付给司机七十块钱。女人是个四十岁的中年女人,脸上虽没有太多皱纹,却显得风尘仆仆的样子,和大多讨生活的女人差不多,也开始显得老了。她将我带到十字路口边的小巷子里,那儿早已坐了五六个人。有男有女,男的四十几岁,胡子很粗很长,下巴覆盖了一层黝黑的胡须。整个人显得有些魁梧,却也从表面给人一种粗犷的感觉。
我心里有些担心,毕竟人生地不熟,难说不会遇到什么危险的事。亦步亦趋跟在女人的后面,拉着行李箱,警惕地向前走去。她将我带到那个满脸须发的男人面前,谈好了之后让我坐在旁边一个空房子里。外面下着雨,他们坐在两个巨大的雨伞下,前面摆放着三张圆形桌子,几个绿色的塑料凳子。我不敢进去,就在桌子旁坐下来,把行李箱放在旁边。凳子上积了水,刚坐下去便觉得一阵冰冷,连忙站起来,又换了一只凳子。那个满脸胡须的男人看了我一眼,突然笑了,用重庆话说:“这是个儿子哟!”
在他前面是个身穿黑色棉衣的青年女子,大约二十五岁,也跟着他笑。他们看了看我,又笑着说几句重庆话。我听不太懂,只从只言片语中稍微明白他们的意思。大约是说我太胆小之类。我也不争论,坐在不时滴下水来的遮阳伞下,手握着行李箱。我虽知道,在公众地方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但小心总没有错,何况我是只身一人,处在陌生的城市!
我来过重庆两次,但也仅是来过而已。坐着火车来,又坐上火车走。仅仅是在繁华的城市里坐了两次公交车,吃过一次饭,对于重庆,其实丝毫也不了解。
雨水流下来,并不太冷。虽然我只穿了两件衣服,在这个冬日里阴冷着的城市,也没感到多冷。只是雨水的冰寒,远不及内心的凄冷。我所有的烦恼,大约都是金钱带来的。虽说金钱不是万能的,但在此刻,却深刻理解了没钱的痛苦,当真是寸步难行。
车是私家车,人却是很多。一辆不大的面包车里,坐着满满的十个人!后面四个,中间四个,前面是司机和一个女人。我坐在靠近车门的地方,窄窄的空间挤满了人的肢体,空气似乎也被压迫得爆炸。四个人如何也坐不下,于是我旁边的同年男子便朝前坐了坐,几乎蹲在了地上。我侧着身,手扶着车门。没办法,空间太过狭小,连转动脖子都不能,更别谈舒服地坐着了。
在车上又变得昏昏欲睡,于是低垂着头,紧紧靠在车门上,在轻微的颠簸中进入浅浅的梦境。中途醒了一次,那时我旁边的旅客已经到了地方。我走下车,让他下去。他走以后,空间变得好受了些,也能换个舒服的姿势坐了。
窗外,阴雨连绵,几分阴冷,几分萧索。车内则是震耳的DJ热曲,估计是什么网络红歌,我听得并不清楚。满耳中除了暴烈的节奏,什么也听不见。司机是个重庆人,说的话大多我听不懂。车内除了我也都是重庆人,他们的谈话,我只能听懂一两句。
过了一小时,终于到了忠县车站。此时,时间大约是下午三点半。小姨走过来时,我一眼就认出她来。尽管心里觉得诧异,却觉得满心亲近的感觉。她长得好矮,也长胖了些!我心里这样想,也为自己这样的想法感到好笑。人怎么会长矮呢?看着她走过来,到了我身边,才发现我比她高了一整个头!原来是我长高了!她走近来,满脸笑容,说:“来了!”
我拉着行李箱,点了点头:“嗯。”她提着一个粉色小包,朝我看了看,说:“走,去那边坐车。”她说完就准备转身走,我急忙叫住她,说:“车费还差二十呢,总共七十块,我自己给了五十,你帮我给吧。”
她恍然回首,连忙掏出钱包,取出一张二十块的人民币给司机,笑了笑说:“谢谢你啊!”司机也笑了笑,说:“没事。”他启动了引擎,开着车慢慢离开。
小姨带我到一个宾馆的前面,那儿或蹲或站了七八个人。她将我带到那些人中,说:“这是我侄儿。”她又帮我介绍那些人,但说真的,我一个不认识。她说的话,多少带着浓厚的重庆土音,与贵州话还是有些区别,我几乎没听懂。至于那些她村里的人问我话时,我除了迷茫地盯着他们看,随后笑笑,什么也回答不上。
对面有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坐在巨大的背包上。估计是外出做工,刚刚回来。他站起身来,对小姨说:“先带他去吃饭吧。车子还得等等。”
小姨才想起我没吃饭,就带我到一家餐馆。她转过头来,说:“不说还忘了,先带你去吃饭。吃完饭再坐车回去。”
行李箱放在小姨同村人那里,我在餐馆里坐下,拿过来菜单,点了个尖椒肉丝炒菜。小姨说:“要不要个汤?”我说:“不了,吃不完。”其实是真吃不完,说是尖椒肉丝炒菜,比起北方的炒菜分量,多了两倍不止!但她说只有菜不好吃,又让老板做了个豆腐汤。我只吃了两小碗米饭,把菜吃了八成,汤却没有喝上多少。与端出来的时候相比,除了温度,大约没什么变化。
吃饭的时候,我问小姨:“你是专门来接我的吗?”她站在旁边,说:“我都来这里三天了,叔叔的一个女儿死了,亲的,不来不好。”我让她和我一起吃,她摇了摇头,说:“刚吃完,在饭店里吃的。”她说着话,搬来一个绿色的塑料凳子,刚坐下去,又看到她嫂子走过来。站起来,把凳子递给她,说:“你坐!”
我估计得叫她婶婶,或者其他什么称谓。地区不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叫。小姨说的时候带着重庆口音,我却是没有听懂。婶婶站在我面前,看着我吃饭,又用口音很重的地方话问我问题。我听不懂时,小姨就帮我翻译,倒也慢慢适应了些。
餐馆里摆放了三张长条形桌子,我就坐在中间的一张。在我前面,一对母子正准备吃饭。小孩子八九岁的样子,看我一个人吃这么多,又听我说吃不完,就嘿嘿笑了起来。小姨逗他笑,就说:“你要不要一起吃?”他扭着头,和他母亲笑了笑,没有过来。
婶婶出去了,去商量一起租车回去。小姨坐下来,又接着刚才的话说:“她是个姑娘,才十九岁!就这么死了。”
我心中诧异,随即明白她说的是那个叔叔的女儿。吃在口中的饭突然吞不下去,梗在喉咙,生硬尖锐。她只是个未尝人世酸甜的少女,是个比我年轻四岁的女孩子,就这么永远的离开了这个世界。我还活着,她却已永远的死去了。小姨说的时候还有些惋惜,可惜那时我心思烦乱,没有听见她说了什么。至于那个女孩是因为生病还是事故而离开了人世,我并不知道。
生命,有时就是这么残酷,短暂得让只活了二十余年的我也不禁感叹。朝阳易逝,时间就像紧紧握在手中的空气,握得越紧,流失得也就越快。而伴随着的生命,当真是烟花般的耀眼,还只在美丽绽放的瞬间就已永远的黯淡下去,变成一堆冰冷的白骨。
我就这样想,饭也吃不下去了。结完账,花了小姨二十三块钱。和小姨走出餐馆,外面下着的细雨已经停了,乌云却低沉地漂浮在铅灰色的天空。风轻轻地吹,人慢慢地走。流水流过冰冷的地面,干净也开始变得浑浊。寒冬,在南方显得格外阴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