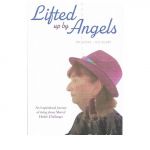槐冢
天气微冷,窗外阳光甚好,我想回家。

家乡这本杂剧,我像是个客串的路人。每次回家,从村子最北边依次路过四条街至村子最南边下车,径直奔到我家。我不大出门,相隔两条街以外的人大多都不认识,村子里面的事物于我而言是一页空白的纸,只那棵老槐树我看得真切,看得明了。
老槐树伫立在村子中心,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光秃秃的树干,只在顶上盘虬卧龙着几根树枝,即使春天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绿叶,样子也怪丑的。因为树干的三分之二处生出了一块巨大的像瘤一样的疙瘩,圆圆的,又像一个挂在树上的鸟窝,突兀得扎眼。粗糙的割手的树皮和树根处一个大三角形的树洞,更让人觉得它影响村容。可它却是村子里老人的忠实听众。
记得小时候,槐树下总是围着一大堆老人,或坐着讲,或站着听。常常是一群人端着饭碗,一边吃饭一边咀嚼着家长里短——庄稼呀,天气呀,村子里发生的大小事呀……间或爆发出一阵阵笑声,震得剧本也哗啦啦地响。偶尔有人路过,就有老人招呼:“饭吃了吗?没吃在这儿给你舀!”
“你吃,你吃,我这也就回家去吃饭啊!”来人忙摆手,乐呵呵得客气回答。
有人被笑声逗引出门,端着碗蹲在门口的石头上,插上三言两语。有这笑声做调味品,不过一顿家常便饭,却被他们吃成了玉盘珍馐的盛宴,锅碗瓢盆的烟火味被演绎到极致。
茶余饭后,奶奶们总是抱着厚厚的鞋底,指上套着银亮亮的顶针,一根又长又粗的针穿上穿下,针上的绳子扯上扯下,“哧哧”作响。这绳子是老人们手工纺制的。几架纺车往树下一摆,轱辘开始在老人们的踩踏下运转,不知转了多少圈,纺出极细的白线来。几个奶奶再把这些细线几根一合,搓成一股一股的——这道工序叫合绳子。合好的绳子韧性极好,是纳鞋底的必备佳具。奶奶们齐坐在槐树下,膝盖上搁着小小的圆形的盛放着各种家什的针线篮,一只手攥着鞋底,一只手提着针上上下下,时不时拿起针在头发里篦两下。从槐芽儿发到槐花开,从槐叶儿落到来年槐挂绿,她们似有纳不完的鞋底,唠不完的话,直纳得满头斑白被时光镀银,直唠得红口白牙沉淀出岁月的旧渍。
小孩子是老人的“跟屁虫”,他们好演打戏,从不“参正”,于是老槐树就成了玩捉迷藏的道具,粗壮的树干藏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是丝毫不在话下的。常有小伙伴躲在树干后,待有别的小伙伴走近,就突然跳出来,作野兽捕食状——“啊呜”一声,张牙舞爪地扑上前来,吓得小伙伴一声惊叫,自己就笑哈哈地跑开,惹得剧本一阵沸腾。闹够了,就都蹲在树下,看着黑漆漆的树洞,七嘴八舌地讨论“这是个什么洞?”有胆大的把手伸进去摸了摸,几秒钟后伸出手来,拍拍手上的灰尘宣布到:“什么都没有!空的!”大家就齐齐唏嘘,里面没有藏着什么宝贝。树洞没有研究价值了,大家就另谋乐处去了。
老槐树立在十字路口,往南一条小土路直蜿蜒向河畔,往北是小学门口的土操场。校门口有两株高大的合欢树,合欢花开时,一片嫣红氤氲,映得破旧的蓝色校门也洋气了不少。每每放学后,我们顺手在树下拾几朵羽状合欢花,到门口操场上商定好,就喜滋滋地奔向河边,踢踢踏踏一阵尘土飞扬后,就听到叮叮咚咚得流水声。
清凌凌的水自夕阳下汩汩而来,披着金光闪闪的薄纱,美得像天边的一抹霞。浅浅的河滩上乱石林立,偶有浣衣的妇女坐在石头上抡着木棒搥打面前的衣服,“啪啪”得声响让剧本都颤了两颤。小孩子才不管呢,脱掉鞋子“扑通”、“扑通”跳进水里,这儿戏两把水,那儿摸几条小鱼,再掀开石头看看有没有螃蟹;一会儿跳到对岸草丛里捉蚱蜢,一会儿又爬到小石桥上叫嚷着,笑闹声不断,直玩到日沉西山,凉意渐起时才回家。
起风了,窗外的云渐渐散了,窗下树叶扑簌簌地落了满地,冬天了,那棵老槐树,会很冷吧?
上次回家去看它,惊觉它更老了——光秃秃的树干,一路冲向云霄都不见它哪怕一根枝桠,像座尖塔笔直地插在一米见方的贫瘠的土地上,瘤一样的疙瘩还在,树洞也在,只是树下的杂剧的主角换了一拨又一拨,直换的今日舞台上空无一人。东南西北,到处都是扎眼的灰白,大片大片的水泥花开得繁华又落寞。北边,小学校已经不存在了,校门口的合欢更是只走了个过场就凋谢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华丽又空荡的村服务中心。
操场也换了装,立了新的篮球杆,羽毛球网,乒乓球台,看起来好玩多了,只是,只是没了好玩的人,再好玩也只是道具罢了。往南,笔直的水泥路延伸到水塔前,这路,多平,多干净,可是,如果有人不小心摔倒了,会很疼的。走到路尽头,左拐,再右拐——当年的桥,已断成两截,小山一样的垃圾堆积在桥上;当年的小河,如今一年四季沉默着,泠泠的风呼啸着,自夕阳下直逼向桥头,渗人得可怕。
热情冷了,人早散了,剧本也发霉了,裹着厚厚的水泥僵硬地就寝了。我站在街口,望着枯槐孤独地像座坟茔一样静默立着——可惜了啊,树洞里有宝贝,无人再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