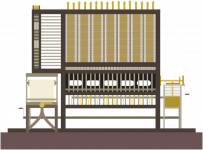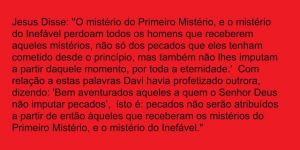外婆题目
我刚记的事儿的时候,外婆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了。小小的个子,瘦骨嶙峋,微驼的背,花白的头发稀少而楛槁,深陷的眼窝,灰暗无神,牙齿集体下岗休息了,只剩一副皮牙壳儿,没有了牙齿的支撑,布满沧桑的脸上沟坎纵横,看上去像八十多岁。

外婆很讲究衣着,一辈子只喜欢穿分蓝色的衣服,宽宽大大的土布芬兰大襟布衫儿,到膝盖以上,缀的小肉扣儿,既精细又支楞,用面浆浆过以后,放在捶布石上,不慌不忙,不紧不慢儿的捶半天,一直捶的板板正正,连布丝都捶成扁的为止,穿在身上不倒褶。两条细的像麻杆一样的小腿儿,穿上肥大的芬兰裤子,脚脖子上扎着一层层的黑带子,大布衫儿下的两条裤腿像灯笼一样,一双不到三寸的小金莲,穿着表姐给她做的精致的绣花鞋,看上去一种别样的美。
外婆扶着凳子才能站起来,颤颤巍巍的身体,走路一手拐棍儿,一手扶墙。
别看外婆沧桑瘦弱,却是个非常勤快还爱干净的人,屋里那土地平打扫的明晃晃的,掉块豆腐都不会沾灰。
外婆屋里除了一个烂木箱子,没有一样像样的家具,那些老掉牙的格朗棒器的旧东西都当成宝贝,放在那个泥巴台子上,摆得整整齐齐,金贵的了不的。
外婆不喜欢小孩儿在她屋里玩儿,她的孙女孙娃一来她家,她就靠在门框上,用拐棍儿指着说:“白来这儿,上外头玩去吧。”
只有我去的时候,二舅家的小表姐才敢和我一起去她屋,外婆一看见,生怕碰着她的那些宝贝疙瘩弄坏了,看得结结实实,小孩子总被好奇心驱使,越不让看就越想看,越不让动,就越想动,还没到跟前,外婆拉着脸说:“唉唉唉!不敢摸啊!上门上玩儿去!”
小表姐故意去摸摸气她,被外婆打一拐棍儿,表姐哭了,我俩那小嘴儿噘的能拴个驴,悻悻地去一边儿,我还不停地白瞪着小眼儿翻着外婆,小声嘟囔着:“真小气篓儿,以后再也不来你家了。”
大妗子耳朵可灵了,听见了笑眯眯地问:“俺小黑妞儿这么乖,谁又惹俺生气了,来上这屋跟妗子玩儿,我就喜欢俺小黑妞儿。”
从小到大一直认为外婆不亲,咋也不象中原人们常说的顺口溜儿:“山老鸹黑幽幽,俺上婆家住一秋,外婆见了真喜欢,妗子见了瞪两眼。”
一直认为大妗子最亲,才不会瞪俩眼呢。所以每次走外婆家,最想见的就是大妗子,大表姐和小舅。
小孩天性都是惦记着吃,就像小猫小狗一样,谁给好吃的,就和谁亲近,每次一到外婆家,大妗子都慌着烙小油馍儿,里边加上芝麻盐,葱花儿,炕的油津津的,一层一层的,外焦里香,还有咸鸡蛋,蛋黄腌成一包油,看着都让人垂涎三尺,吃着津津有味。
大妗子总是笑嘻嘻地说:“乖,慢慢吃,多吃点,吃饱都不想家了,在妗子这儿多住几天。”
吃饱喝足了,抱着亲亲妗子的脸,妗子心里美滋滋的。
外婆从来也不会说一句暖心的话,还抠抠索索的,不舍得做好吃的,一会儿说吃饭掉饭粒儿了,一会又说吃馍掉渣儿了,还老是嫌吃的多,唠叨不休。吃一顿饭,能被她数落的迷三倒四,在外婆面前心里怵怵瞧瞧的,不敢展翅儿。
长大以后不断听母亲说,才慢慢明白,外婆这辈子过的太艰辛了,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也没穿过一件好衣服,吃过一顿像样的饭,才让外婆养成抠门儿的习惯。
外婆年轻的时候,外公脾气暴躁,专横跋扈,外婆一直逆来顺受,言听计从,本来家里有几亩地,也算瓷实实的小疙瘩户,膝下三男二女,大舅已经娶了媳妇,生了孩子,一家人男耕女织,很滋润的小光景儿,外公也不知那根神经短路了,嫌发财慢,带着大舅去打劫,不到三天,不但钱财没抢到,爷儿俩被两颗枪子送进了阎王殿。
外公和大舅死了,撇下老少两代寡妇,家里塌了天,两个小舅和我的母亲都尚未成年,没有了劳动力,没有了当家主事的,加上外人的唾弃和欺负,家庭陷入了困境。
外婆一辈子没操过心,没乾坤,没本事,这个家的重担落在了大妗子的肩上。
大妗子,当时也就二十二岁,一表人才,秉性刚烈,脾气火爆,说话做事特有魄力,带着两个小舅在娘家人的帮助下,艰难的料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
由于生活的困境,大姨很快就嫁人了,母亲也被童养出去了,一直到二舅长大成人结婚以后,这个家才一分三下。
大妗子带着表姐孤儿寡母过生计,小舅舅帮助大妗子种地,大妗子手很巧,常常做些鞋卖,表姐十多岁就会描龙绣凤,做些小卖活儿,小光景也算过得不错,大妗子对外婆也非常孝顺,外婆总夸大妗子对她好,吃个虱也没少过个大腿儿。
二舅是个阴份人,心事颇重,瘦得像根棍儿,走路头勾着地,一年到头也看不着个喜脸儿,似呼全世界都是他的仇人,二妗子更是麻批兼泼妇,仗着娘家人多,茅斯(厕所)石头,又臭又硬,和外婆吵架,连推带打,祖宗八辈都骂上,把外婆气的躺到地上打滚儿,呼天叫地的哭。
小舅舅和外婆一起过,小舅舅心底善良,也勤劳肯干,就是和尚命作怪,媒人介绍的也不少,一辈子也没能找个媳妇,有几个外地的逃荒妇女,都是在这住几天,骗点钱,就溜之大吉了,一辈子挣的钱都孝敬那些女人们了,日子过的捉襟见肘,导致外婆的一碗玉米糊糊都是金贵的。
大姨和二舅一样,是个冷漠的人,刻薄又吝啬,对外婆从不管不问,外婆和小舅的穿衣,鞋脚儿袜子,都是母亲和大妗子做的。平时的生活各方面都有大妗子照顾管。
自从大妗子跟表姐去了新疆以后,外婆和小舅没有了主心骨,生活的无聊使小舅除了干活就是打牌,挣点钱也都让他输了,外婆一个人守着个大院儿,精神无助,和强烈的孤独感,使外婆的精神有些抑郁。母亲常常让父亲套上牛车,把外婆拉到我们家住,住不了几天,就应记她的穷家,囔囔着要回去。
那时我们村儿还算是比较先进的,家家都有个黑黑圆圆的小广播,声音可大了,有条件的做个小四方木盒子,中间挖个圆圆的洞,把小广播装饰一下,看起来好看多了。
外婆一到我们家,每天的乐趣就是听广播里唱戏,广播一开始,就张着大嘴巴眉开眼笑,象看大戏一样,一直仰着脸儿盯着广播。
嘴里还不停的自言自语的念叨:“咦!真妖气,恁大点儿个小方盒儿能盛下一台戏!真有恁小的小人儿?他们在里边能转过来身儿?不显憋得慌?”
逗得大家哄场大笑,谁也给她解释不明白,天天仰着脸儿,立等着那个小妖气儿给她说话唱戏。
母亲一直是外婆五个儿女中最孝顺的,是外婆的贴心棉袄儿和精神支柱,母亲病重的时候,拉着我的手,哭着对我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常常去照顾外婆,每年给外婆和小舅做鞋袜和衣服。
母亲走了以后,遵母遗嘱,替母行孝,每年给小舅和外婆做鞋袜和衣服,隔三差五去帮助外婆洗衣服,做点家务。
每次去外婆家,她都会问:“你妈咋不回来哩?我想她,她是不是不要我了?”
我总是忍着眼泪编着瞎话忽悠她,后来不知道是谁告诉她了实话,外婆听说她的孝顺女儿去世,在剖心挖肝的悲痛中,精神被彻底摧垮,耳朵也失聪了,也不太认识人了。
外婆白天黑夜呼唤死过亲人的名字,还常常胡言乱语做些傻事儿,好几次拄着拐棍,扶着二舅家的墙边,到门前地边,用铲锅刀铲点青草,回家剁碎拌点面粉,在锅里蒸熟,叫小舅吃,小舅把它攉了。
外婆就坐在院里拍地叫天的哭:“俺好不容易蒸点蒸菜,你不吃俺吃,谁让你小三儿把它攉了,你这不是叫俺饿死哩吗?”妈呀娘呀的哭闹半天。
那时物质贫乏,没有什么好东西,每次去看外婆,用那点微薄的工资给她买点儿点心,外婆一看我就问我:“你是哪庄的?拿着干粮上哪儿上学去哩?”
我附在她的耳朵上大声说“我是你的外孙女儿,来看你哩。”
好不容易才似懂非懂的说:“哦!你不是上学的,你是我的外孙女儿,就是那个教学先儿吧。”
急忙捣个拐棍儿步履蹒跚地跑到二妗子家院墙外,大声喊二妗子:“曲姐儿——,你家有馍没有?噷给俺一个,俺家有客了,官庄那个教学先儿来了。”
弄得我哭笑不得。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买了很多点心,骑上自行车,高高兴兴去看她。
外婆一看见我就说:“你又来了,今个你可白阁俺家吃饭,俺没做你的饭,你上前头院(二舅家)去吃饭吧。”
说的我面红耳赤,泪流满面,觉得心里可委屈了。
我又赶忙安慰她说:“你放心吧婆,俺不在恁家吃饭,俺就是来看看您,帮您洗洗衣服就走了。”
外婆这才张着大嘴,露着满嘴的皮牙壳,半天才笑着说:“哦——”
临走的时候,小舅舅送我到大门外,刚好二妗子,表哥,表妹,还有邻居乔外婆们一家儿都在那儿,大家都热情地打招呼,围着我问长问短,外婆也拄着拐棍儿颠颠儿的跟出来了,我赶紧扎好车子,过来扶着她。
外婆笑吟吟的说:“再来了领着娃儿们。”
我一愣。
小舅舅赶紧大声嚷她:“你胡说啥呀?这是官庄小外甥女儿。”
外婆还一个劲儿的白证说:“俺咋不知道是外甥女儿,官庄那个教学先儿?前天外甥女婿自己骑个车子,带着俩娃儿来了,她没来,俺叫她再来了领着孩儿们和女婿一块儿,有啥不对。”
小舅越嚷,她越说,羞得我满面通红,无地自容,真想找个地缝儿钻进去,小舅气得差点打她身上。
从那以后,想起来糊涂的外婆就伤脑筋,泪流满面,两个月没去看她,突然有一天没有任何征兆,外婆就去世了。
外婆走了,我的心里后悔极了,肠子都悔青了,恨自己幼稚,任性。
在外婆灵前泪流满面,长跪不起,深深忏悔,为自己没有完成母亲的遗愿,留下了永久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