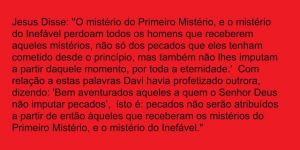回不去的故乡例子
村北头刘昌永口音是上海口音夹杂着我们当地的土话,很是难懂,我们小时候总是喜欢模仿他说话,家里大人总是不太悦意,大约是怕正在学说话的孩子们口音也变成了“外乡客”罢。

刘昌永的头发是剃成那种前半额没有头发的那种发型,据说他家是大清国王室的某个支室。对于这一点,他本人是没有老刘头不是我们村人,饥荒年从上海逃荒过来的,职业是一个铁匠。会用洋铁皮卷各种日常东西,例如铁桶,洒水壶,舀水用的马勺,等等。一块块的洋铁皮在他的手里好像一张纸一样,被他随性地制作成周围村落各家农村人的一些生活用具,相比较于传统的李铁匠家的很很粗制的用品,他做的器具有外观的美还同时兼有一丝丝的灵气。
在此之前,村里平日里大家用是用木头箍的桶,做法大抵就是村子里李铁匠用铁锤敲出来的细铁环,再加上切割成圆形的木做底,条形的木条被铁环箍住做桶圈,这样做的桶,一双桶的重量就超过了一桶水的重量,很是笨重不好用,且过个一年半载总是要拿去花钱补桶。铁皮桶就不一样了,轻巧好用。那时,周围十里八村一时之间都以有一件刘氏出品的洋铁皮桶为傲。
记忆里,我大约是跟着一群好奇的小伙伴去过他家的窑洞,这是一座面南的院落,正面有三孔大窑洞,院子里面种着我们叫不出名字的小花,不像我们当地人,在院子里的空地里,多是种些韭菜,萝卜,豇豆,南瓜之类的菜,总之,一切看起来就是与众不同。偏窑是铁匠的工作室,里面有一张工作台,各种形状各异的搓刀,锤,钳,剪,夹,老虎钳,高级钳工用的工具一应俱全,他先用专用的剪刀将铁皮按图样剪好,敲敲打打间一个漂亮的洋铁皮桶就出来了,然后用不太熟练的当地土话夹杂着上海话的腔调喊叫着,顺手在边上的缸里舀了些水装入桶里,密封效果很是不错,竟也真是滴水不漏,在乡人们的惊叹声里接过报酬,他脸上一脸的淡然,继续做下一个活儿。
刘老头做的桶经用,也好看,桶的大小可以订制,也可以先欠钱,于是,十里八村的传统木桶差不多在两三年内全换完了,旧的木桶劈了当柴烧,桶上的铁环被小伙伴们则拿着满村子跑,男孩子人手一个滚铁环玩儿。
手艺人的日子相比于普通的种地为生的农民家庭自是好的多了,周围村落里很多人都慕名而来找他做一些活什,老刘家的日子在我们当地那是很红火。
那时,乡间物质资源是极缺的,小伙伴们都没什么玩,总是去他家捡一些三角形或是圆形废弃的铁皮边角料当玩具。把铁皮用手折成各种奇怪的形状,相互之间吓唬,彼此之间玩的不亦乐乎,有时铁的废角边将手划破皮流血了,也全然不当一回事,抓一把黄土洒在伤口上止血,接着玩儿去了。
在偏远的大西北黄土沟里,来自上海的刘昌永带着两个儿子一开始独自过活着,就这样在他敲敲打打声里,两个儿子慢慢长大了,长大后的两个儿子只能听懂上海话,已完全不会说上海话了。从他们的衣着,生活习惯已经看不出他们和大上海有任何一点关系了。他们父子在这里扎根生活了下来,偏远,交通落后的村落竟然成了他们逃荒的落脚点。
时局变换,大锅饭年代,老刘家的所有东西全被充公,老刘和所有的人都在黄土坡地上修梯田,吃大锅饭,老刘拿惯了锉刀的手改用了拿铁铣,铁锹,每日里和大伙一起挖土打梗,听着广播里的最高领袖的指示,活的无比地压抑。挣完工分回家的路上,路边是用麦草扎的人偶,上面用毛笔写着“刘少奇”,“邓小平”的名字,村干部和民兵监督着所有农民每天放工后向这两个麦草人吐口水,村人们都听话地给着两个给主席抹过黑的人吐了口水,便回去吃大锅饭。轮到老刘了,老刘没有吐,民兵便轮起铁铣超老刘腿上来了一下,老刘梗着脖子一歪一歪地走了。连着三日,老刘腿上挨了三次铁铣,硬是没有吭一声。
后来,村小队长不忍心了,每次就让老刘在大伙收工后在后面收拾场地里的红旗,喇叭等物件,就不用去唾口水了,小队长私下说,这个上海佬是个“硬怂人”,不了了之了。佩服之余,便看得出他于众人的不同点,在家人一致反对声里,将他自己的子嫁给了这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外乡客。后来,承包到户时,按村里人一样的待遇给他们分了地,报了户口。
时局如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旧时住在黄土塬上的人嫁女子,多将女儿嫁给川道人家,川道人家离水源近,庄稼收成比塬上人家好,日子看起来很是不错,等到八十年代后,塬上交通好,路平整,日子一天天的比川道人家好起来了,川道人家交通诸多不便,外出不易,日子一天天的比塬上人家差了,九十年代后,川道人家嫁女儿则都嫁往了塬上人家。这一切就像一个轮回,所有颠倒了过来。
转瞬,时间到了九七年左右,各个电视台上轮番播放着香港回归的新闻,我那时正在上初一,刘昌永上海的二儿子来村里了,这个消息对于村民来讲是比香港回归更具新闻性,这时候大家才知道,原来这个上海的外乡客,当初在上海老刘是有老婆的,刘昌永原是在一家大型的工厂上班做钳工,一家有三个孩子,后来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被厂子里开除了,家里便揭不开锅了,刘昌永只带着老大,老三外出讨生活,就这样一路到了我们大西北,娶了当地的女子,生了女儿,便在当地定居了,从此再也没有回过上海,直到客死异乡。
刘昌永家的老二和他的姆妈被扔在了上海,没有收入的母子两人便一直在上海的弄堂里乞讨度日,时间改变了很多事物,时过境迁,在上海的刘家老二,因为有上海户口,也有上海的老房子,日子自是越来越好,姆妈去世,没有等到远走他乡的父亲回来,待到成年结婚时,也没等到远走他乡的父亲回来,虽心底里仍然还记是记恨远走他乡的老父亲,但刘家老二还是忍不住找了过来。
历尽各种苦难的刘家老二,走过父亲刘昌永居住过的窑洞,走过父亲走过的乡间小路,一直走到父亲的坟地前,刘家老二嚎啕大哭,在坟前喃喃地说着当地人一句也听不懂的上海话,末了,长跪磕头,将身上所有的钱全掏出来给了还住在村子里的老大,老三,便头也不回的走了。
再见已然变成一捧黄土,父亲走了,所有的恨也走了,刘家老二再也没有回来过。从上海一路飘荡到大西北黄土高坡的老刘,永远也回不去他梦里的大上海了,他在西北的黄土地里慢慢地变成了一颗尘埃。
现在,每次回到老家,在村子里有碰到满头花发的从外地逃荒而定居在我们村的老年人,打招呼时,他们的声音里还是带着他们固有的浓浓的乡音。远有上海口音的,有河南口音的,近有同省但在千里之外的张掖,威武口音的,不一而足。
当然,真相还是让人有些很不舒服,我们村子里除过刘昌永这一家人,其他留下的外乡人则只是女人,也就是说,那时有从河南,甘南藏族,北边张掖武威等地逃荒的人,只有他们的女儿留在了当地,具体的原因自是不言而语,只能是因为了不再饥饿,继续活下去,嫁给了当地的农民就是为了有口饭吃,时间从她们脸上抹去了曾经所经受的苦难,她们在当地生儿育女,在当地倔强的生活着,我也曾问起过她们,有没有想过回去她们的出生地,老人们则是一脸的伤心,多数则是说了一句话,少则无语,马上就转移了话题,这句话就是:找不着路么。带她们一起出来逃荒的长辈们,为了口活命饭,将她们给了当地的农民,而长辈们,兄弟们带着用她们换来的粮食也不知道流落到了那个地方,从此各天涯。恨么?老人摇了摇头,抹了一把有些浑浊的泪,再也悄不做声。
对于她们来说,故乡永远成为回不去了的地方,而落地的外来户自已好像总觉得比当地土著要低一等似的,都极为谦逊,在和同样年龄的人打招呼总会叫别人叔。
至于,当初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大地方的人会来到我们这么偏远的地方呢,大约是交通不好,偏远,所有的战乱,饥荒发生时,这穷乡僻壤没人关注,这里的人大抵还是有口吃的,于是在那个年代,像老家庆阳,还有相邻的陕北便来了众多的逃荒人。
现在,时局就像一场场足球比赛,没有人永远踢主场,以前刘昌永带着两个孩子从上海步行出发到我们大西北讨生活,如今,定居在西北的刘昌永的侄子,孙子和我们这些西北土著大都出来,又去上海,深圳这些地方讨生活,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漂泊,我们都像先辈一样,也是这时间轴上一粒小小尘埃,每日里为生活奔波,不管如何窘迫,但现如今终归是从容了些。但愿,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能回去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