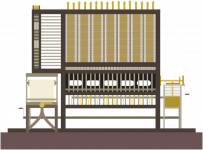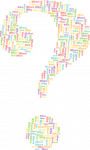遥远山村
小时候曾在一个叫新村的地方居住。记得那是一个位置挺偏、风景挺美的小村落。四周环山,山中为台塬,塬上数间土屋。这是一处才开垦的处女地,所以就有了新村这样的地名。初迁于此,正值秋冬之交,落木萧萧,冷风瑟瑟,檐头墙畔枯草摇曳,呜呜作鸣,似乎在挥手致意,又似乎在倾诉着什么。

这里没有学堂,念书需到很远的一个叫店梁的村庄。每回上学姐领着我和两个小弟。姐弟四人日复一日不停地奔波于山乡的风尘里。没有电灯电话,极为闭塞的乡居生活,一切都简简单单。读书也不用费多少心思,没有夜习、没有作业,也很少考试,学多学少咸有人问津。平淡无奇的日子一如村前时断时续的清冽山溪,悠悠的、汨汨的、无声无息地流淌着。若说学涯清苦,也不过苦在往来的路途。那时给我感觉读书就为赶路,赶路就在读书。
如今想来,于那个时代、那样一个氛围里生息,恬淡、清幽、古朴的格调仿佛让人走进了远古。虽然有些简单,简单得近乎简陋,但这对禾苗般土生土长,尚且未被更多尘嚣濡染过的童年并未觉得有什么不遂心如愿的。习惯于与泥巴打交道的庄户人家最讲实诚,对娃儿们的教育也甚为宽容。能学点啥就学点啥,能做点甚就做点甚,学不来、做不会也不打紧,只要尽了心力并未丢弃做人厚道的本分,这就算是个好娃。不管有无多大出息,到头来不误担水劈柴,种地放羊,娶妻生子,传宗接代就行。不过庄户人也有解不开的愁结。那总是如影随形难以挣脱的温饱问题,怎似横亘于面前的一座难以翻越的大山,令人望而兴叹,愁肠百转。那时我们姐弟几个,正值抽苗拔节、疯吃海喝的年龄时段,却偏偏赶上饥荒岁月。也许地贫,贫瘠得不能出苗;也许人懒,懒惰得不肯播汗!但我想这两样全都不似。那时家家户户都在忙吃忙喝,却家家户户都缺吃缺喝。饥饿真就将姐弟们变成了古书上所描写的那种叫做饕餮的怪物。才吃过上顿便又惦起下顿,有事无事总是绷脸儿往灶间里混,鹫鹜般争食砧板上母亲菜刀切剩下的白菜、萝卜头。一锅米饭还没等煮熟,老早就猫在那里候着抢食锅巴。锅巴蘸酱油或拌菜汤的甜美滋味至今还在心头萦绕。此时母亲就有些沉不住地往外轰:“一边闹腾去,早晚没个饥饱的饿鬼。”缺吃少喝的年代,偏就人人抱了颗可容山纳海的笸箩肚,一天到晚咕咕唧唧地吵闹着要吃要喝。有时忍不住我就撩起衣摆,照着那滚瓜溜圆的肚皮一通拍打“好乖乖别烦人,我也没法子啊。”后来在观看过有关难民的影像资料后,方才晓得那些啼饥号寒的非洲饿殍也都像我们小时候,个个挺着溜圆的肚皮。
与其家中锅罄钵尽难全两餐饱,莫如户外搜山掠地暂缓一时饥。生活是把双刃剑,给了你饥饿,同时也给了你应对饥饿的本领。山溪捞泥鳅,秋场扎耗仓,雪原套山鸡,山林砍柴火。为图生计饥寒的童年向山川原野伸出了祈求恩赐的双手。那时我们能够从野外获取的生活资源——植物类有沙奶、梭牛、山桃、沙枣、马茹、蘑菇、地毛、地皮;动物类有野兔、黄羊、盘羊以及野鸡、野鸽、沙鸡、石鸡等。扎耗仓是极具情趣的营生。每逢秋收季节,姐和我共骑一头驴子,带上耗仓箭、铁锹、拉土筛、口袋等工具前往很远的糜地里。扎耗仓先要查看鼠窝新旧程度,既使新洞也要从显露出的蛛丝马迹进行判断。一般洞口有松土,土中有足印,印上有籽粒的内中很可能藏有粮食。此时用带有倒钩的耗仓箭在洞口周围来回往地底戳,瞬间就会有一小撮禾穗被倒钩带出,随后几锹,少则一升,多则两升的粮食便收入囊中。扎耗仓给家人的餐桌增添了亮色,却苦了失去冬储粮的田鼠。在漫长的冬季饥寒会逐个夺取它们的生命。据说田鼠发现自己粮仓被盗痛不欲生,会自己吊死在树杈上。每当念及于此,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田鼠不是被《诗经》长期讽喻的那种硕鼠,至少还要靠自己的劳作甚至长期积淀的智慧生活。从求生的理念讲,无异于我们人类。
后来村子南头办起一家饲养院。守院人为一光棍老汉,一条腿残缺,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每逢秋季,这里矮矮的几间屋舍便被遮掩在日渐增高的草垛后面。一摞摞草垛,满尖尖、黄灿灿的像是童话里的一座座金山,诱惑着游戏的童年。栽筋斗、捉迷藏、掏草洞、搭草棚,甭提玩得多开心。有一回捉迷藏兴味正酣,无意间我躲到老汉屋里,所幸无人。此时,一股浓香沁入心脾,我径直摸到灶台,掀开锅盖一瞅,满满当当一大锅煮熟的黑豆正腾着热汽。曾听大人说起,黑豆是用来催乳的。听说近日这里一匹姆马下了驹儿,想必这时小马驹正等着吮乳呢。惊喜之余,急忙招呼俩弟,仨人不由分说,以帽代钵,每人连豆带汤满满蒯了一“钵”,端起就走,未待迎面赶来的老汉回过神已颠儿出老远。饱餐后,溪边清洗的当儿,才发现着了色的帽和手灰不灰、红不红面目全非,几经清洗难复如初。我们都给怔住了。那天我们很晚回家,而且着实让脾气暴躁的父亲给皮练了一回。
做了回贼,挨了次揍。连惊带吓我做了一宿梦。睁眼时,天色大亮,家人上学的上学,下地的下地。咋就没人叫我。也许叫了,没能叫醒?不容多想,我胡乱穿起衣裳,拎起书包迷迷瞪瞪往外跑。那时迟到是要罚站的,就站在讲台一侧,傻乎乎地面对着全班同学。以前曾被罚过,很丢人很难堪。途中刚好看见几头驴子路边闲逛,我瞅准其中个头稍矮的,纵身一跃上了驴背,一手薅住鬃毛,两腿使劲一夹,向前狂奔而去。似乎昨个偷吃在肚里的黑豆在喊冤叫屈,一路上腹胀难忍,排气不止。静无一人的校园里,我忐忐忑忑凑到教室门口,几经喊过报告才被允许入内。也许老师正忙着给同学们出题造句,没顾上对我罚站。我侥幸落座,但屁股还没落稳,老师就点名要我造句。“‘······就······就·····’。请答。”很简单。但由于紧张,我一站起来就懵了。蓦然,路上一颠一颠骑驴蹦屁的情形浮现眼前,于是脱口而出“我,我今早在上学路上,就骑驴来就放屁·······”应该讲句子可以这么个造法,但不留神就给这么造了。此句一出无异于掷出一枚重磅炸弹,登时炸了窝,轰然爆笑之后的私语、窃笑、白眼冲击波似地,一浪高过一浪,瞬间将我淹没。
一晃多少年过去。曾经生活过的新村已然成为我生命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因为它承载了我的童年和童年的欢乐与忧伤、幸福与艰辛。想起童年,就情不自禁地想起它-----那遥远的小山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