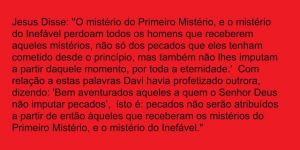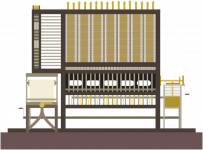童年的记忆满分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难忘的童年,虽然不是每个人都有快乐的童年。但回忆起我童年的时光,可以说是快乐无忧的。

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娃,那时和众多的农村娃一样,村里不像城里的孩子,或是像现在的孩子一样,两三岁就被送进幼儿园。可以跟着老师学唱儿歌、学背唐诗、与小伙伴们做游戏,六岁就可以上小学一年级了。更不会像城里的孩子或是现在的孩子一样,没有多少属于自己的时间,除了上学之外,还要上什么特长班。更不像城里的孩子那样闲暇时可以到学校附近的小人书摊点儿,花个二分钱随便找一本自己喜欢的小人书然后坐在凳子上和许多小朋友一起陶醉在一幅幅画面和那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中。
只是记得母亲告诉我说我四岁时父亲领着我去城里看病,听到羊的咩咩叫声我才会开腔说话。在那之前很多人都说我是个哑巴。我只记得自己八岁那年,很高兴由母亲领着走进村东头的大学校排队报名。随后背起母亲缝制的书包,走进离家只有一二十米远的低矮的教室,开始了漫漫求学路。
因为家中的条件所限,父母不能为我们买更多的可供娱乐的玩具。因而只有自己想法让自己快乐些。
春天的闲暇时光,我会与伙伴一起擓着竹篮、荆篮。到绿油油的麦田挖野菜,累了就干脆躺在麦地望着那蓝天中的白云,做着无数的梦想。临近中午或傍晚,高高兴兴地擓着满篮的野菜,回到家里,再听听父母由衷的夸赞,看看父母喜悦的笑脸,心里总是美滋滋的。除了挖野菜,就是去河堤上挖甜草根。挖出来后,掳去甜草根上的土,放进嘴里就嚼起来。那种甜甜的感觉令我难忘。“九九杨落地”以后,晚饭后又会与伙伴一起点着一根木棍儿、一块儿不知什么时候捡到的手榴弹弹皮、或是一段废弃的车子外胎,或是掂着一个自制的灯笼,到路边的杨树周围去摸“瞎碰”(金龟子,还有地方叫“仓虫”),之后把那些摸到的“瞎碰”让父母给我们炒一下。那种焦香酥脆的美味,每每让我想起来就流口水。风筝满天飞的阳春三月,我和伙伴们也会自己动手找个塑料袋和细线做一个简易的风筝在街上疯狂的跑着、跳着、喊着、笑着;春暖暖花开的时候,也会折一根柳条,抽去柳枝,然后做一支柳笛自由自在地吹起来。
每年夏天,尤其是发了暑假后。那时不是像现在的孩子一样,不是去上补习班,就是去上什么特长培训班。除了每天擓着篮子打猪草(割草或是薅马齿苋之类的野生植物)外,更多的是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那时可以与伙伴光着脚丫踩着软软的土,随意的感受那阳光的温度。(回忆起儿时在土里玩耍的时光不由得想起著名诗人臧克家的一首诗“孩子在土里玩耍,父亲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埋葬”这就是几千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世世代代以土地为生的农民的真实写照。)也可以走进坑塘里打打水仗,洗去夏日的炎热;可以坐在池塘边看看一棵棵树在水中摇曳的倒影,听听那树林里蝉儿的嘶鸣;或者邀几个伙伴,一起去河边或是坑塘边,捡拾些瓦片或是瓷碗的碎片或是石子什么的,打打水漂,看看谁扔下的东西在水面上漂得最远,打的水漂最多;或是比比谁投的更远;可以与伙伴一起去一片小树林里,听到哪颗树上有蝉的叫声,就猫着腰,轻轻地走近那棵小树,再轻轻地将小树扳弯,之后另只手迅速捂向那树上的蝉,那时也有收获的喜悦,也有蝉儿飞跑后的怅惘;打猪草回来的途中,偶尔遇到雨的光临,也会折一片大大地桐叶,放在头顶,挡一挡突如其来的陡雨,或是干脆接受一场淋雨;最喜欢的是一场大雨后,光着脚丫,卷起裤管,躺着过膝深的谁走在村里的大街小巷里,偶然的也会被地上的玻璃片或是别的利器刺伤脚丫或脚趾;也会与伙伴玩摔陪陪窝的游戏,和一堆泥,一分为二。然后各自捏成窝窝头的形状,用力往地上一摔,然后让同伴把他手中的泥拽一点补在摔烂的部分;夏日里,也会捉一只知了捏着知了的肚皮,听听知了的嘶鸣,或是享受一下知了扑棱着翅膀时带来的凉凉的风;路过莲池时,也会猛吸一口气品品那莲花的芳香;小时因为无知也曾戳过马蜂窝而被蛰得满脸是伤。也曾因掏“小虫儿”(麻雀)而掏出一条“长虫”(蛇)吓得从墙上掉下来。好在没什么大碍。闲暇的时候,会收集一些烟盒纸叠成三角,与伙伴玩;(把三角放地上然后用手在地上猛拍,把对方的三角拍翻了那三角就是自己的了);也会和比自己年龄稍大的哥哥姐姐们领着去草地上或一块宽广平地做做“老鹰抓小鸡”或是“杀羊羔”的游戏,先选一人当老鹰,然后是个子高的在前面当母鸡,其余的当小鸡,老鹰追拍排在后面的小鸡,母鸡张开双臂保护着小鸡,小鸡灵巧的躲闪着不让老鹰拍着。或是十来个人围坐成个圈儿,做一做丢手绢的游戏:一个人手里拿只手绢,在圈子外面嘴里唱着丢手绢的儿歌、蹦蹦跳跳围着圈子转着,悄悄地把手绢丢在一个人的后面。随即绕着圈子跑。如果跑了一圈到了有手绢的身后拍着时,这人还没发现,这个人要为大家表演一个节目;说个笑话、唱之歌、或者背首诗。然后由他或她开始丢手绢。如果这人发现了随即拿着手绢追上丢手绢的人,那个丢手绢的就要继续丢,这个人可以回到原位;追不上,而丢者已坐到这人的位上时,这人就要受罚表演节目。也会十几个人一起玩玩“星星过月儿”或是“猫钻十二洞”的游戏。
也记得有一个夏天,得知城里的药材收购部回收知了皮(医学名词叫蝉蜕),每斤两块五。于是天天与哥哥弟弟一起拿着竹竿,掂着塑料袋,来往于村子的树林里找寻着树上的知了皮,一个夏天结束后,我们收获还真不小,整整收获了四斤,买了十元钱。第二年夏天我们又找寻了一个夏天,比头一年找的还要多,没想到高高兴兴带到那儿之后,却被告知不再回收了。辛辛苦苦找来的知了皮,带回来之后在家里挪来挪去的,最后都不知去向。哎!那是怎样的一个徒劳无功的夏天啊!
夏日的雨后,或是晚饭后,最快乐的就是或是拿着手电筒走进树林,或是干脆什么也不拿全凭肉眼去离家不远的树林里,去捉捉拿刚刚从地里爬出的“马吉妞”(知了),每棵树都围着往上瞅一瞅,瞄一瞄,看见树干上有小东西蠕动,确认是蝉后就或是爬上树抓下来,或是找个木棍敲下来,拾起来放在碗里或是茶杯里。捉的差不多了就高高兴兴地回家,让母亲给我们炒一炒,香喷喷的饱饱口福。之后,跟父亲一到麦场里,享受夏夜的微风,或是躺在父亲旁边数着星星,听父亲讲故事;或是看骡子和马拉着石磙,不停地在收获的麦穗上碾来碾去;或是躺在敞篷下听那不远处的荷田里阵阵的蛙声,闻一闻飘来的荷叶的清香;间或的还有谁家盖房子时,十几个人抬着石磙打夯时喊的整齐和洪亮的劳动号子;“大家伙抬起来哟,嗨哟!咱们哪齐用尽哟,嗨哟!”那时的夜,也是那么的寂静。
秋收时节,最高兴的是随父母一起到玉米地一面掰着又大又沉的玉米棒,又瞅准一棵玉米杆折断一节去掉皮,咬一咬品品是否甜,那时称为甜秫杆。有时也会一不小心划破手指,却也毫不在意。玉米收回生产队的麦场里后,每天天不亮就会被父母喊起来去剥玉米裤,好用来晒干后烧凹烙饼。每人不管自己能否剥得完,都是把玉米棒子急急忙忙先往自己身边扒呀扒呀的,快到上学时间时,又各自擓着剥得的玉米裤急忙回家,吃饭上学。当然除了剥玉米裤,就是每天早少擓着篮子去公路边扫树叶。
也曾注目天上南飞的大雁,也曾凝望蓝天的白云;“二八月,看巧云”;也曾对着那中秋的月亮无数次念叨那时的儿歌:“月奶奶黄巴巴,八月十五来俺家,俺家有个大西瓜够你吃够你拿,拿到河北看你大,你大背个蒸馍篓,咔哧咔哧咬两口”;也曾在雨后拿着大扫帚,在路上或麦场扑打飞来飞去的蜻蜓;也曾在生日那天走进家中的那棵大椿树,说几遍奶奶教的:“椿树王椿树王,你长粗我长长。”期盼自己的个子长得更高些;也记得每到阴雨天时奶奶由高粱秆等扎个扫天娘娘,期盼天晴的的时光。
冬天的闲暇时间里,也会与一些小伙伴玩玩挤咕侬,(用肩膀相互扛扛用以取暖),或是玩叨鸡(正名应是斗鸡)单腿立地,然后用双手抱着另一条腿抱过膝盖,相互攻击对方;以此活动筋骨,偶尔的看到对方摔倒在地也会哈哈一笑,然后伸手拉起对方,冬天玩的最多的是游戏是推铁环、打“皮牛”(即鞭陀螺)、摔面包;或是用铁丝和废弃的自行车链条做成手枪,那时也叫砸炮枪;那时看了电影《小兵张嘎》等,也会学着找一块木板用刀或锯条来做一把木制手枪,然后把用来写字的墨汁把那手枪涂染一番,随后当然少不了父母的一顿责骂;也会先划定一个小方块儿,找一个木棍把两头削尖,再拿一块有柄的木板把那木棍敲起,随即用木板猛搧那木棍儿,之后,让伙伴朝着大步把那木棍儿拾过来,比比谁打的远,(我们这儿又称作“打耳”);也会找些石子什么的玩女孩子玩的“欻子”的游戏;或是与女孩子一起踢踢毽子、跳大绳、玩玩蹦房;或是骑兵打仗、抬花轿的游戏;那时最不会玩的就是“开绞”游戏。偶尔的也会找些经了风霜的干燥萝卜缨,揉碎然后放在一张白纸上卷成卷儿,再拿出火柴划着也偷偷过一把抽烟的瘾;冬天里最开心的事要数和朋友一起打雪仗、堆雪人;忘不了穿着厚厚的冬装和棉鞋踩在雪地上发出的吱吱声响;也忘不了父母进城回来时给奶奶和我们带回的,用干枯的荷叶包着的香喷喷的水煎包;还有母亲给奶奶买回来用于祛除胃寒的甜中带辣姜片儿和酸中带甜的利于消化的山楂片儿等;也忘不了生产队里的那片山药蛋以及那烧制砖的土窑前的那棵粗大的靺鞨梨树。
忘不了村东头备战路(现在的文峰路)两旁到的白杨树和低矮的荆条林;往不了生产队里的打麦场和那不远处的土窑,以及窑西面空地上的堆放整齐的一排排土坯;忘不了生产队里的那片竹林和莲池;忘不了那低矮的烟蓬,和高高的烟炕以及烟炕周围那片挺拔的白杨林和那棵长满红红桑葚粗大的桑树;忘不了生产队里的那座挂在树上不知多少年的、每天都要有次序敲几下(用以提醒上工的时间到了)、而紧急情况下(特别是有火灾的情况下)就敲得很乱的钟;忘不了生产队里的那牲口院,以及那勤劳的老黄牛和永不知疲倦的骡马;忘不了村里路旁的墙上贴着的“彻底反击右倾翻案风,深入批林批邓”以及“伟大领袖毛主席永垂不朽”和“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的大字报以及随后的“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子牵牛。”的计划生育宣传标语;忘不了村中间那条不算太短也不太宽的的坑塘,以及翻坑时被人捕去的鱼儿;忘不了村西面的那条小河以及河堤两旁低矮的小杨树,河水曾经是那么清澈,曾是那么的滋润着两岸的土地;忘不了生产队西南角的那口养活村里人多年的水井,和那用来拉水的水箱;忘不了上学时,为迎接纪登奎的视察而站立两旁排成的长长的队伍,和手中摇晃的鲜花和学生发出的整齐的“热烈欢迎!热烈欢迎!”的欢呼声;忘不了村里天天有宣传车的喇叭里传出的声音:“包庇犯XXX。”忘不了那时一元钱能买十三个鸡蛋;忘不了麦收时节与同学为了颗粒归仓,珍惜农民伯伯的劳动果实,而一起提着篮子去麦地顶着烈日、弯腰捡拾一穗穗麦穗;忘不了奶奶为治我的鼻衄(鼻子老是流鼻血),而天天给我用桑寄参叶煮荷包蛋,让我吃喝;也忘不了一次偶尔的与女同学争斗后,父母和奶奶常教育的那句话:“男不跟女斗,鸡不跟狗斗,做什么事都要先让着对方,尤其是女孩。”
每年的大年初一早上,一听见谁家放过鞭炮,我和弟弟等就会急忙跑捡拾地上没有响的爆竹,或是有捻儿或是没捻儿都会拾起来装进口袋,回家后或是把没捻儿的炮掰断,夹着有捻儿的炮点着,或是把有捻儿大雷子点着后再放上一只破碗,看看能把那碗崩多高。也记得自己七八岁时,春节前花两毛钱买了一个大雷子,父亲知道后没有动手打我,只是说了些话让我知道父母为养活我们这个家的不易,让我懂得珍惜父母的每一分血汗钱。每年春节时最高兴的事是和母亲一起去串亲戚,那样可以得到外婆舅妈姨妈等给的一毛、两毛或是五毛的压岁钱。也记得有一年母亲不让无去串亲戚,无法去看那长长的鸣着长笛奔驰的火车,自己气得撕掉了新贴的没几天春联。
如今,随着城市的日新月异的迅猛发展,不知有多少个我们曾世代赖以生存的小村庄,已逐渐淡出我们的视野。人们极不情愿的被挤进一幢幢阳光稀少的高楼。面对逐渐消失的村庄,我对我的生存了几十年的小村庄长生了无限的眷恋。
我眷恋村庄里的那条不算宽但却有几百米长的贯穿我们两个生产队的小坑塘,眷恋坑塘边的石堆,眷恋坑塘里的蛙鸣、夏日树上的蝉声和坑塘里树的倒影;眷恋坑塘岸边谁家的满树的梨花和紫红的桑葚;眷恋坑塘里的那一泓清清的池水;眷恋夏日割草回来走进坑塘舒爽的洗个澡的时光;眷恋坑塘边那一颗颗棵棵垂柳,(那时每年清明那天早上母亲都会早早起来去这一些青青的柳条,在家中的每个门上清扫一番,然后把柳枝插在门头。我们小孩子也会动手折些柳枝编成圈儿套在头上,学着解放军叔叔匍匐前进,或是玩打仗。)眷恋母亲和村里的同龄妇女在坑塘边拿着棒槌洗衣的欢笑声;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坑塘里的水越来越少了,也越来越不流通了,越来越臭了,再后来坑塘里也不再有水了,一天天被生活垃圾填平着,再后来人们也不再忌讳把房子盖在坑里了。到如今陌生人来到村里根本不会知道那里曾经是坑塘,也不会知道多少年前,每个村里都有一条坑塘。
我眷恋村里的或是107国道旁,还有村西边河堤上的那些早已不再的每一棵树,因为那每棵树都有我难忘的回忆。我眷恋夏日树上的知了和蝉蜕;我眷恋村里的那座砖窑和那窑边的那棵古老的漠河梨树;我眷恋村里的那至少有二十多年不存在的打麦场,忘不了麦收时节,长辈手拿扎鞭赶着牲口,赶牲口拉着石磙在麦场碾麦子的情形;无数个夏日里曾与父亲一起去麦场看夜,忘不了父亲讲的那许许多多的故事;眷恋那时无数个叶落的日子,双脚踩在干枯的落叶上发出的沙沙沙的响声;眷恋小时候母亲为我做的猫头鞋,和端午节时母亲用艾叶、蒜杆儿、布头为我缝制的挂在脖子上的香蒲……
童年是焦灼期盼的生日那天父母或奶奶做的的一晚蒜面条;童年是春节时穿在身的新衣服和美味的热腾腾的饺子;童年是躺在架子车上仰望的天空;童年是和伙伴玩过的泥巴;童年是与伙伴一起光着屁股趟过的河水;童年是和伙伴一起围观的一本小人书;童年是耳濡目染的样板戏和家乡戏;童年是麦草垛里与伙伴捉过的迷藏;童年是和伙伴一起捉过的蚂蚱和知了;童年时与伙伴一起嚼过的毛根、桑葚和甜甜的玉米杆;童年是和伙伴们一起摘过的榆钱和槐花;童年是外婆家枣树下的期盼和欢笑声;童年是与伙伴们一起玩过的折纸飞机和;童年是用木木棍敲下的屋檐下的舌尖舔过的冰凌;童年是和伙伴们在手腕上划过的手表和印过的麦籽花;童年是与伙伴一起疯跑着看过的露天电影;童年是时常唱着的《学习雷锋好榜样》和天天听的《东方红》与《国际歌》的歌曲。童年是……
童年的时光虽然简单,却不单调;童年的生活虽然贫瘠,却不乏味;童年的记忆像风中的蒲公英散落在记忆的天空;曾经的天真烂漫的美好童年时光一去不复返;曾经的开心玩耍的日子也渐行渐远;曾经在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已散步天涯;曾经的纯纯的感情也变得复杂。我们怀念童年,我们怀恋童年。但是请不要因为忙碌而淹没了自我;不要因为生活而丢掉了那份童心和纯真;时光带走的只是不再的快乐和忧伤;心中却要永远保存着那童年的美好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