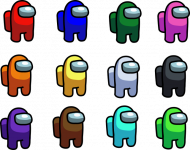距离将爱掩埋下
我回来没找秋明洋,秋明洋也没有找我。这中间好像有某种默契,又好像是在刻意的回避。可我始终忘不了广州的那顿早餐,小妹冷艳的拒绝,她拒绝的不是一瓶酱,是拒绝的秋明洋那份情意。我为秋明洋感到心痛,心痛的同时眼前老是晃动胸前吊着红线的那个鸟语男人。

如果我会画画,我要画一幅画:画得两边远远的各站着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男人和女人中间缓缓走来吊着红线的男人,一边的男人是背对着女人,女人的目光越过红线男人,泪眼婆娑地眺望背对的男人。画得右下角题着一行字,写着“人是会变的,何况口味。”画的背景是那个古色古香的早茶店。
女人的话从来都像做梦,要反着去理解。只是你要甄别,女人的那句话可以入梦。
我还没有家,所以有大把时间瞎琢磨。秋明洋有时调侃我,“找个人嫁了吧,你挑黑的捡白的到时候剩下个没皮的。”秋明洋说这话时说的挺顺嘴,我问他啥意思“黑的白的和没皮的有啥联系?”秋明洋只嘿嘿笑,“我也不知道,你不是好琢磨么!”这时,我想起秋明洋说的这句话,突然有点明白了。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剩下个没皮的是啥?”意思就是那意思么!秋明洋这个阴险的家伙,这么恶毒的咒我,亏我还为你报不平呢。
有人说过,“人无皮则无敌。”
想起“没皮的”,又想起小妹。小妹一定不是那样的人,那么小妹是什么样的人呢?姑且算是“迷失”吧。
后来,我曾经问过小妹,“你当时怎么想的?”
小妹说,“也没怎么想,我去广州了,总要混得像个样子。即使回洛阳,也不能灰头土脸的。”
“那也不能糟贱自己呀,或者说一个好好的家说不要就不要了。”
“我觉得对不起他,就又任性了一次。”
我就是听了小妹下面的话,我至今单身。
小妹说,“人除了爱情,还有需要,需要有时比爱情更实际。在广州时,我有需要。”小妹需要?需要混出样子,需要站稳脚跟把一家接过去,还是仅仅生理的需要。小妹没说,我也没有刨根问底。人的内心都有一块柔软部分,这部分对外紧紧关闭,只对自己打开,而且常常是在独自一人夜深人静的时候。
在我时常瞎琢磨时,我听说秋明洋同小妹离婚了。离婚是小妹提出的。
我听说这个消息后,去了秋明洋的家。秋明洋不在家,秋明洋的母亲带着已经三、四岁的小明洋。
我问,“阿姨,明洋呢?”
秋明洋的母亲说,“这孩子跟我呕气呢,埋怨我当初没有和他一起拦着小妹。他说,‘小妹不去广州就不会走到这一步。’我说,‘留人留不住心呀,小妹坚持栏就能拦住了。’明洋呀,我跟他说不清。”
在小妹去广州后,阳光在秋明洋的脸上越来越少了。冷峻的秋明洋更增添男子汉的气质,小妹把这样的男人抛弃,没有道理可讲。爱情不讲理,只讲感觉。
秋明洋的母亲继续说,“这次离婚,我是让明洋冷静冷静,小妹那孩子任性,脑子热想啥是啥,一时魔怔。说不了小妹嘴上说‘离婚’,明洋劝劝就顺着台阶下来了。明洋不懂女人的心。明洋说,‘这次不听你的了。’事情全拧着,俩孩子都憋着谁也不说句软话。”
我认同秋明洋母亲的话,秋明洋同小妹离婚太轻率,不过他们结婚也像是个冲动。我又想起了方便面,红红绿绿的包装,是挺吸引人的。再说的确方便。在对待秋明洋和小妹事上,我的天平不自觉的向小妹倾斜。男人都有“花心”,尤其是遇到漂亮女人,天平从来都不公平。但这次的天平和小妹的漂亮无关,绝对公平。
这年春节,秋明洋领着个女子来找我,见面第一句话就说,“这是你未来的嫂子。”这是个我敢直视的女人,除了比小妹年轻外,仅从长相看不如小妹。小妹的长相如果打95分,这女子最多打85分。
不过,我听说男人找爱人(找多了应该不叫爱人了,称媳妇或者老婆更合适),第一个选得是漂亮,第二个选得是气质,第三个选得是贤惠,如果有第四个的话,选得是伴侣。像秋明洋这样的帅哥,既然结婚、离婚开了头,我不认为他找一、二个女人就会终结,那样的话,“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既然如此,这个女人我就称之“路人甲”,“嫂子”在我心中只有小妹。
确切的说,“路人甲”气质不错,和小妹有一拼。我真佩服秋明洋,像淘宝一样把一个个出色的女人淘了出来。
秋明洋介绍完“未来嫂子”,也不管我的态度,就理所当然的说,“你嫂子在我那呆不下去了,你把她调到你这接待口,先随便找个位置。”
我这接待口有接待科,下属还有宾馆、招待所和饭店,凭“路人甲”的摸样,如果不挑剔工作,安排个位置我找领导说说应该没问题。我这里正好也缺人。我征求秋明洋的意见,说,“我接待科接待人员还少,让她搞接待如何?”
秋明洋不同意,“接待上,抛头露面不好,我让人惦记上了。”
“那,到招待所当服务员?我争取争取,就是有点委屈她了。”
“路人甲”说,“不委屈,不委屈。”“路人甲”的声音脆脆的如幽谷清泉挺好听。
我对秋明洋说,“我运作运作,你等我消息。”
“路人甲”拿出两条烟放在茶几上,说,“过年,一点意思。”
我把烟抓起来塞给秋明洋,“我又不吸烟,你是知道的,跟我还来这一套。”
秋明洋挡着,嬉皮笑脸说,“你不是运作么?不要嫌少呀。”
秋明洋领着“路人甲”走了,走的很远还能听到“路人甲”的高跟鞋声。听着真有劲道。
秋明洋离婚我是有些生气的,这么大的事连个招呼也不打,现在有事了找上门。我在接待上最不缺的就是烟,“路人甲”从包里拿烟,好像抱着块金砖一样金贵。小家子气了点,冲这点“路人甲”配不上秋明洋。我随手把烟丢到茶几底下。我想我也得打听打听秋明洋和“路人甲”是咋回事,别晕了吧唧办事。
秋明洋那点事还真禁不住打听。“路人甲”是秋明洋所在生产部的计划员,才结婚,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和秋明洋好上了。“路人甲”的“真命天子”听说了,先是到单位闹了一通,臭秋明洋的同时,连带着把“路人甲”也恶心一通。接着,他找到秋明洋家,把秋明洋堵得家里,用棍子抡秋明洋。秋明洋到底理亏,用胳膊护着头一味躲闪,后经人劝开。他出了气,秋明洋左臂被打得骨折。
这件事在秋明洋的单位闹得比较大,秋明洋脸皮厚过得去,“路人甲”脸皮薄过不去,当然在单位没发呆了。
我有点不放心,给秋明洋打电话,“把这女人调过来,那男人不会闹到我这吧?”
秋明洋说,“不会,那男的到单位去闹,就是不想过了。我们说好了,我出了点血。他跟她离婚。”
秋明洋“出点血”,是受伤出点血,还是那个“出点血”。有时文字太暧昧,只能意会。不过通过这件事,我对秋明洋和小妹的离婚有了新的看法。他们的离婚未必像秋明洋说的那么单纯。
我把“路人甲”的事办了,“路人甲”当了招待所的服务员。“路人甲”成了我无意中引进的人才,后来“路人甲”当了招待所所长,干得很出色。也正因为“路人甲”的工作调动了,脸拾起来了,皮也有了。于是,“路人甲”终究没有同那个男人离婚,那个男人还和“路人甲”专门找我感谢,约着出去喝酒,我还真去了。大家都没有提秋明洋,秋明洋像片云轻轻飘走了,为别人留下了蓝天。吃完饭,“路人甲”劲道的高跟鞋声远去,临了“路人甲”对我说,“他太帅。”
“路人甲”最后这句话,让我对她刮目相看,女人常常比男人更拿得起放的下。浪漫用来玩玩如水中杨帆,玩过还要上岸,当不了日子过。
也许是在小妹、“路人甲”的双重打击下,秋明洋心里“出血”了。秋明洋不辞而别,去了常州。随后又把母亲接去,母亲和孩子安排在上海。
这时,小妹回来了,可秋明洋已经走了。小妹回来是兑现对秋明洋母亲的承诺,只是比承诺的时间稍晚。人对生活的设计是很难做到分秒不差的。小妹同秋明洋的母亲联系上了,小妹还是叫“妈”,他们聊着孩子,聊着老人的身体,偶尔也说到秋明洋。
有一次,秋明洋的母亲对小妹说,“你来吧!”这话说的很隐晦,小妹明白,秋明洋的母亲也确信小妹明白。
小妹接话很快,“妈,这话要让他说。”小妹等了很久不再说话,母亲一直在电话那边等着,母亲知道小妹的话没有说完。果然,小妹声音有些沙哑的说,“妈,他欠我一个信任和解释。我回来了,他没有等我。”
小妹在对我叙述这段往事时,明显动了情,而我却不以为然,脸上露出促狭地笑。小妹摇头,“你质疑我的感情?”
“不,你想我讲真话么?”虽然我不想让小妹难堪,可既然有机会还是想戳戳她,她有时太傲慢了,我忘不了广州的早茶还有冷艳的拒绝。
“讲!”小妹那股傲慢又来了。
我说,“好,你不要动气呀。”我立刻严肃起来,口气模仿电视里的法官,“首先,离婚是你提出的,不存在秋明洋没有等你;其次,你在回避同那个男人的关系,我作为局外人都能感到关系不正常,何况秋明洋这个敏感的当事人呢?”
小妹眼神如电,盯的我头皮发麻,半天才缓缓地说,“这就是你们男人的想法,这些问题我想直接对秋明洋说。可惜他听不到了。”小妹又说,“我给你唱首歌吧。这首歌唱出了我的心声,可能让你明白。”
我尴尬地机械点头,房间里荡漾起小妹的歌声:
“你说过你会等着我回来
就让眼泪拭去那些寂寞的尘埃
别让这份爱留下了空白
说好一辈子永不分开
答应我好好等着我回来
我要带你飞过那片流言汇的海
我们都明白距离不能将爱掩埋。”
歌声停了,小妹泪流满面,我在压抑的气氛中感到羞愧。
我不敢再去拨动小妹感情的琴弦,继续着秋明洋的话题——
以后,秋明洋的母亲对小妹再没有提起过秋明洋。母亲自从劝秋明洋同意小妹去了广州后,母子的关系就不再和谐。小明洋经常添置新衣服,母亲收的快递。秋明洋一周才回来一次,有时连一次也保证不了。秋明洋没有注意孩子身上的新衣。
秋明洋刚来常州时,是在开发区与人合作办厂,生产光学镜片,出口日本。订单很稳定,厂子产量的需要,秋明洋赚点钱就添设备,产量越大,设备也越多。后来合作人去了日本,只负责光学镜片在日本的销售,生产这一块他撤了资,全交给了秋明洋。秋明洋在上海买了房子,孩子的户口也转到了上海,就近上了小学。
秋明洋像个成功人士一样,晚上到酒吧喝喝酒,听听音乐,沉郁地把自己融入乱哄哄的酒吧。他会不时地用眼光扫过门口,眼神中流露出莫名的期待。
那年春节,秋明洋去广州见了小妹,着实很生气。秋明洋不过说,“你跟我回去,哪怕我养着你。你看你现在的样子。”小妹就翻脸了。
“我不是你的附属品,我有我的生活,你走吧!”小妹把秋明洋拒之门外。
秋明洋的思绪被浓妆艳抹的搭讪女子打断,秋明洋不耐烦地把人轰走了,连逢场作戏的兴致都没有。秋明洋的为人无趣,人家称他“衰哥”,常州话“帅哥”和“衰哥”也分不太清。秋明洋又想起谷铭,他曾调侃谷铭“找个人嫁了吧”,这句话其实对自己也很适用。秋明洋不自觉地笑了。有闲暇时是要考虑考虑个人问题了,身边没个人是不方便呀。
小妹呀,你的名字叫心痛。秋明洋把杯中酒一饮而尽,似乎下了某个决心。
我接到秋明洋的电话。秋明洋对我从来是命令,而且很不客气。
秋明洋说,“哎,我给你找了个嫂子。”
“你有病呀。”我不等秋明洋把话说完,就打断他。“你咋跟阴阳蛋似得,想起一出是一出。”
秋明洋说,“你别急,听我把话说完。我们碰巧认识的,聊聊还不错。我让她这两天找你,把她人事关系挂你那,然后办停薪离职。”
“你为啥不就近找一个,非要找这里的。”
“还是家里的知根知底,心里踏实。”
“那她咋不在本单位办停薪离职呢?”
“她单位是合资企业办不成,调你那就可以办,我打听好了。”
“我们单位也不是那么随便的呀?”我有些不满意秋明洋的霸道。
秋明洋听出我口气的不善,更加气势地说,“你小子不是提处长了么,少跟我推三阻四,就这讹着你了。”
我话说得不客气,事还是要办的。我倒要看看这个女的,好像应该叫“路人乙”了,我偷着乐。
“路人乙”来找我了,高个圆脸大眼,笑起来两酒窝,漂亮且内敛,一副让人轻松愉快的形象。我原来不知道安分守己是啥样,看了“路人乙”我知道了。我对“路人乙”印象很好,秋明洋身边是应有个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
我对“路人乙”说,“办停薪离职想好了?”
“想好了。”“路人乙”的声音不如“路人甲”,漂亮不输小妹,但缺少小妹的妩媚。
我随口问,“你们咋认识的?”
“他前段时间在这里的附属医院住院认识的。”
“这里住院?”我疑惑。
“诶呀,他不让说。”“路人乙”的脸像晚霞尽然,红云一片,头也低下了。
“你说!”我气恼,秋明洋有事瞒着我。
“路人乙”不得已的交待。秋明洋得的是乙肝,他不想当地知道,偷偷回洛阳治病,住在附属医院的传染病房。“路人乙”的父亲也在住院,同秋明洋住一个病房,这样他们认识了。“路人乙”说,“他一个人住院,也没人照顾,挺可怜的。就这我们??????”
“路人乙”的解释我谅解了。我又问,“你的年龄,没有成家?”
“我都告诉他了。”“路人乙”声音很小,刚抬起的头很快低了下去。
事情办完后,我打电话给秋明洋,说,“你发财给我添堵,最后一次了,以后你的破事我不管了。”
秋明洋心情不错,和我开着玩笑,“该管不管也不对,有困难找领导。”
我们没有提住院的事,秋明洋这种病捂着盖着,我能理解。
我含蓄地说,“以后成家了,注意少胡吃海喝,你也要保重身体了。结婚时打个招呼,我要能去会赶过去。先祝福你。”
“你不要啰嗦了,跟我妈似得。”秋明洋不受教。
“对了,问阿姨好。另外,嫂子在我心里只有一个,就这。”我不等秋明洋回话便收了线。
我到底没有收到秋明洋的结婚请柬和任何结婚的消息。
过了有大半年吧,也许更长。“路人乙”突然微笑着出现在我面前,我问,“回来了?”我的口气像熟人出去转了一圈见面后很自然的一句问话。“回来了!”“不走了?”“不走了。”我们简简单单地寒暄,似乎都明白在简单问候背后的意思。虽然当初我很看好“路人乙”,但总感到秋明洋的事情不会这么简单。一个人的心很大,大到可以装下天下,可往往奇怪是,再大的心它只能装一个人。
这件事我本来想问问,可最后还是没问,我一般不是个多事的人。
关于“路人乙”的事,我在小妹这得到了答案,尽管我对这个答案似信非信。小妹说,“秋明洋的母亲不同意。她说她的一辈子就是这样坚守过来的。她不想孙子有个后妈就如同没给秋明洋找个后爸一样。”
很久没见秋明洋了。这次回来的秋明洋很难用风采依旧来形容了,尽管他仍有着成熟男人的丰韵。秋明洋这次回来是想在这里找个保姆,保姆跟他在常州也行,跟母亲在上海也行。过渡一段时间,哪合适待哪。
秋明洋专程过来,对保姆要求很高,要会做饭、懂会计、能开车,当然待遇也很可观。这种事自然又是我来落实。
我在公司电视台发了条招聘启事,一份份应聘者的情况摆在了我的桌上。秋明洋不甘寂寞的扒拉着。我和秋明洋几乎是不约而同地看中了一位老姑娘。老姑娘小四十,学的是财务,家传一手做菜手艺,曾在饭店干过大厨,要不是怕影响容颜,现在可能还在颠大勺,唯一有点遗憾的是,老姑娘学过车、有驾照,可是操作的很少,开车技术不娴熟。秋明洋亲自面试老姑娘,老姑娘干净、利索一个人,秋明洋更是中意。接着我和秋明洋去了老姑娘家,一餐饭吃完,秋明洋说,“就你了。”秋明洋给老姑娘撇了二万元,说,“你在这租辆车,熟悉两月后,到常州报到。”
这件事以后,秋明洋如同人间蒸发一样,从我的生活中消失。
接下来的事,是小妹告诉我的。
老姑娘去了常州一直待在秋明洋身边,有个四五年光景。后来,秋明洋常州的厂子找了个人打理,他留在上海的时间越来越多。老姑娘不去上海,老姑娘说,“秋哥,你回上海了,我想还是待在厂子里干会计。你偶然来一趟也有个人招呼。”现在,老姑娘还在厂子里。厂子这一块秋明洋临终前托付给了老姑娘。
秋明洋最后是肝癌,在上海去世的。小妹从她孩子那得到的消息,遗体告别仪式按照秋明洋生前的要求,没有通知任何人,老太太也没有去,老姑娘在家陪着她。遗体告别就是小妹和孩子,还有几个女人。小妹说,“几个女人中应该有你说的‘路人甲’、‘路人乙’,还有的我也不清楚了。”
夜色悄悄来临,当我和小妹说完秋明洋的事后,两人很久没有说话,房间里寂静极了,寂静的仿佛能听到两人的心跳。
终于,我打破沉默,“我该走了。”
小妹说,“我也该走了。”
“你?”
“孩子来接我,我去上海。”
“非要孩子来接?”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
“嫂子,再见。”我第一次郑重其事地喊“嫂子”。
小妹家的门在我身后轻轻的关上。我内心虚掩着的门也在轻轻关上,我孤独一人消失在夜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