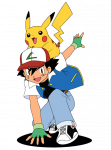中元节焚香祭母
三岁那年,我便痛失了我的周氏生母!

母亲给我以宝贵的生命,她常年拖着病体,咬紧牙关,倾尽心血养育她的亲骨肉。我知道,她给了我许许多多乳汁,许许多多爱。可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她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家里人只称“老周”、“你周家妈”,每逢年节祭祀化炼“信袱”,也是只写“周氏”。最叫人悲哀的是,连她的音容笑貌,我也完全不记得了。
本应该是有过她的照相的,但当年日寇飞机发疯似的狂轰滥炸,重庆周边的县城,也难逃战火的祸殃,北街我家的几间祖屋被毁,片纸也没有留下。
一个小孩子,对母亲的记忆,确乎是不完整不周详的。但说来也真奇怪,偏偏母亲出殡下葬的片段情景,却是清清楚楚地刻在我幼时记忆的深处,一直以来不曾忘怀。 粗壮的麻绳套住未有髹漆的棺木,很重很重的,由好几个人抬着,离开北街的家往城外走。我尤其注意到:棺木上面,那只被绑缚着的公鸡,风里,它飘舞着的红黑翎羽。
出城来到桥坝河,一个岗坡地边,一棵小桐树旁,墓穴已经挖好了。人们拽住粗绳子,轻轻的将棺木缓缓的往下安放入土。 我全身白麻孝服,腰间系着麻绳,大人们让我跪伏在墓穴前的地上,我并没有再哭喊,只是有些不知所以地向我的母亲依依泣别。封土的时侯,我看见那些掀下的砂土,渐渐地倾覆下去,倾覆下去……
哭告无门、无所依托的母亲,她一个人也太艰难了,只有如此失望,如此无可奈何地丢下自己的孩子,撒手离开冷酷的尘寰,独个儿,永远的走了!
表亲罗二,我的姨妈,还有焱云家伯娘,她三位与母亲相处时间久长,见到和听到过的事多一些。她们对我说,“你妈真是命苦,病又多,独自一人支撑着,那样贫病交迫的日子,实在难熬啊,她遭了多少的罪!你可得一辈子记住她呀……” 她们还告诉我,料理母亲后事的是我的舅舅和伯父,那时正是战乱期间,父亲却是远在万县。
“瀛山你那周家外公外婆早已过世,长舅也去世得早。家里只剩下你母亲和二姨、小舅,三人惨怛伶仃,相依为命。” 后来,由十公家的姨婆婆说媒,母亲才嫁进县城北街我家。但是“她的境况未见好转一点,婆家也还是穷困;你父亲是在他的爹妈死后,过继给没有后人的居孀九婶的。”“这位九婶叔娘守住点儿薄产,只顾得了自己,最多,也就是接济过你父亲去重庆,上川东师范的一点费用。她这样的婆子娘对媳妇儿,只会把人当丫头奴仆使唤,绝对不会疼人关照怜悯谁的……”
姨妈还告诉我说,母亲去世之前,去过重庆南岸的罗家坝她家。那时,姨妈和刘家姨叔结婚不久,刚来罗家坝做了点小生意谋生。 母亲或是来投亲、求援、看病的,或是想到万县寻找父亲的?但在那个兵荒马乱、艰难困顿的艰苦年月,这些,显然是没办法实现的心愿罢了。住了两天之后,一切无望,她的病情还在不断加重,姨叔姨妈他们赶紧安排母亲回綦江县城去。
回来她便倒床一病不起,呻吟,挣扎,直到去世。她那时不过二十四五岁,照理应该有着非常强烈的求生愿望。一个正在芳龄的年轻女子,难道就心甘情愿这样匆匆辞世了? 难道就忍心丢下自己尚未成年的孩儿? 她心里不知有多难多难哪!老天一定会知道:她有过多少的失望、多少的哀怨、多少的遗憾!母亲真是孤苦落寞,贫病交加,备受煎熬,她确确实实是穷死的,累死的!
那个冷酷的世道,真该真该诅咒!
我这从小失却母爱的人,自然常常因念母而痛苦啼哭,伤心流泪,我的内心长期郁积着那种挥之不去的伤痛;成年之后,一种深沉的念母情结,仍然一直牵动着我孤寂的心灵和敏感的神经。
有一次梦里,恍惚见到那麦土边儿的岗坡地,那棵小桐树似乎已经长大变高,它参差披拂的树影,隐约掩映着母亲的孤坟。我立刻跪伏下去,冥冥之中,我陪她说话,向她倾诉这些年来,无尽的思念与衷情,告慰她,父亲后来如何的愧疚和懊悔……
直到近些年,我才有了空,曾经几次前往桥坝河,找那块未敢忘怀的岗坡地,我去寻觅伤心童年旧的踪影,我去凭吊母亲长眠的荒凉孤寂凄清的墓地。我要告诉她,这些年来,儿子经历过多少多少人生的磨难与挣扎,才终于走过来的。我要去告慰她,这些年来,也曾经有过多少多少心地特别善良的好人,给苦命儿子以深深的同情,给苦命儿子以母亲一般无微不至的关怀……
可是,这眼前的景象,一切都是那样似而非。在桥坝河场镇后的山坡,上上下下,我踟蹰往返,四处寻找,怎么也找不到那块记忆深刻的伤心墓地,更是找不到那记忆里抹不去的小桐树旁的荒凉孤坟。我独自一人转来转去,几乎找遍了每一个角落,就是找不见它,心里好一阵彷徨苦恼,怅惘得不能自已。
路的东头,有一位白发老者,长须飘拂,他正向我这边蹒跚走来,我连忙迎上前去,打探询问。
“请问老人家,这坡地麦土边,从前有棵桐树,旁边有座土坟,我家母亲,六十多年前的——”
“哎呀,这么久的老坟,世事变迁好大,哪还会在哟? 你想,前一阵,毁林砍树,拆墓平坟,改土造田,修沟筑堰,早就……,先前祖宗老话不是说,慎终追远,入土为安嘛;现而今,人已经死了,还是不得安宁……”他直摇着头,用惋惜而有些怨尤的口气诉说着。
老人很健谈,也有他自己的独到见解,我谛听着他的絮叨。
“也倒是难得,你当小的,一片孝心与苦心! 这,不就快到中元节了,对面的岩坎脚下,那阵掏挖出来的老坟骨头,差不多都堆埋在那旮旯儿了。依我说,你不如办点纸来,去那里给你老母亲化了,也好让你了结这积压多年的苦苦心愿哟!”
“我妈走的时候,也就二十多……”我痛楚地向他解释说。
“哎呀,二十多就去了……为娘的,艰难;孩儿,就更痛更苦了……,那,真够伤惨的——”心慈的老人自言自语地连连摇头,似乎已经有些哽咽了。
还能有什么法子呢,大抵只能如此了!旧历七月十五中元节那天,听从陌生老人的热心指点,按家乡的习俗,我带上香蜡纸烛,去到那岩坎之下,焚香化纸,仰伏天地,哭母祭母。
七月如火,大晴天,正午热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汗水泪水早已模糊了我的双眼;刚点着的两支红烛,那如血的热泪就滚落了一地;猛烈燃烧着的钱纸,化作一道道青烟冉冉升起来,带了我强烈的痛楚思念,飘飘摇摇地,向着那不知名的远处飞去。
儿子在祈愿,祈愿,祈愿我天国的母亲,永远安息!永远安息!
我焚香,我祷告,感恩,祈愿,寄托哀思……,即便如此,这时时刻刻牵动着我的念母情结,思念,对我那苦命母亲铭心刻骨、挥之不去的思念,依然是那样无休无止的。
思念,依然叫我无以释怀,即便我记不起她的音容笑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