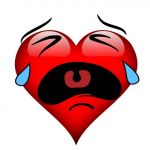浅析《高山下的花环》的新历史主义色彩
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是80年代军旅小说的经典之作,它打破了以往革命战争题材小说的宏大叙事模式,转而从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思想进行探索,表现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情感的丰富性,语言平实,情感真挚,体现了现实主义和人性主义在80年代军旅文学作品中的回归。虽然《高山下的花环》并不属于新历史小说,但是它的叙事手法却具备产生于同时期英美国家的新历史主义的某些特征。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即单线历史的复线化和大写历史的小写化、客观历史的主体化、历史和文学的边缘意识形态化分析《高山下的花环》的新历史主义特征。

《高山下的花环》叙述了企图“曲线调动”的高干子弟赵蒙生下放到九连后的经历。小说虽然取材于对越自卫反击战,但是它并不着重描绘战场的情景,反而用大量的笔墨叙述了赵蒙生的“曲线调动”和梁三喜的“欠账单”,从这些细节中进行纵深开掘,折射出被大历史掩盖的军队内部的黑幕和农民生存的困窘。同时,它摒弃了革命历史小说中的英雄主义,不以“高大全”的英雄形象来服务政治需要。李存葆笔下的赵蒙生、梁三喜、靳开来,既有光辉的一面,也有缺陷:如赵蒙生前期的贪图享乐,梁三喜在现代军事知识方面的短板,靳开来的爱发牢骚。李存葆通过对细节的挖掘和人物性格多样性的刻画,将传统单线的大写的历史,分散成复线的小写的历史,展示了大历史之下的丰富内涵。
其次,小说以第一人称为叙事视角,与以往革命历史小说作者退居幕后展开情节截然不同。小说中有两个“我”,第一个“我”是前往云南采访赵蒙生的李干事,但是这个“我”在小说中仅仅是一个过渡作用,在小说叙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还是第二个“我”,即赵蒙生回忆中的“我”。因为赵蒙生是三年前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所以在叙述这段往事时,“我”的形象总是活跃在过往的场景中,有时“我”还会发表自己的感情和想法,比如赵蒙生谈到自己的母亲因为文革变成一个长袖善舞的“外交家”时曾慨叹“十年动乱,摧残了多少人材。权利的反复争夺,又使多少人茅塞顿开,又学得'猴精”呀!人为万物之灵,极具谋求生存的本领,是适应性最强的动物。在那你死我活的政治漩涡中,心慈的变得狠毒,忠厚的变得狡猾,含蓄的变得外露,温存的变得残暴......”。这样,“我”的形象位于过去与现实之间,小说的情景并不仅仅是对历史的简单再现,而是一种带有主观倾向的历史叙述,打破了文本与历史之间的人为藩篱。
此外,作品中梁三喜一家边缘化的不幸境遇与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了一种线性疏离。梁三喜是出身革命老区的农家子弟,他的父亲和兄长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他为了给父亲治病负债累累。梁三喜是那个时代小人物的一个缩影,虽然小说没有对文革的历史背景做过多的渲染,但梁三喜一家的遭遇却给读者提供了一个窥伺底层人民生存困境的窗口,小说通过疏离意识形态的方式对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进行了无声的控诉,也引导读者对历史和现实进行质疑和反思。
《高山下的花环》虽然是一部军旅小说,但李存葆无意还原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场,他从人性的角度剖析人的心灵和情感,从微观叙事展现宏观历史,打破了旧历史小说经学化、意识形态化的框架,体现了“文学即人学”的主题。虽然它不属于新历史小说,但它初步具备了新历史小说的部分特征,它实现了军旅小说思想上的拨乱反正,为以后的军旅小说创作开辟了一个新视角,在它之后问世的又一部军旅小说《红高粱》,在开辟了军旅小说的第三条战线的同时,也为新历史小说创作注入了新的血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