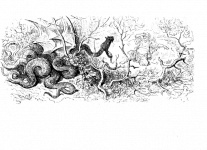婚事(下)
春红的婚事一结束,村里一下子又清静了,像在漂满浮萍的水面上投下的半块红砖头,一圈圈把浮萍荡开,但很快又回拢过来,恢复原来的样子。

一个柴草垛后闪出一条狗,白不白灰不灰的,继而后来又出来一条黑狗。梅有些害怕,小时候被狗咬的伤疤还在腿上呢。因为咬她,小玲爹把狗吊树上勒死了,小玲娘还心疼的跟啥似的,那阵子逢人就说,喂了七八年的狗了,拴上就中了,唉,不听啊,非打死不中。那以后梅见到狗就害怕,就厌烦。那年她哥从谁家要来一只出生没几天的狗崽子,说养着看家,梅就哭闹着不要,还拿根扁担说要打死,后来,哥又拿着狗还给了人家。梅想不明白城里有些人咋就那么喜欢狗,有的都着了迷了,当孩子养了,宝贝儿子女儿的叫着,见人还让狗叫人叔叔阿姨的,比对自己爹妈就好。梅想,那种人心里可能是很空虚的。那两条狗也不叫唤,眼睛盯着她,梅看到了它们的谨慎与多疑,尾巴轻轻的摇着,围着她闻,梅步子放慢了些,狗跟着她身后走,梅心里很紧张,这两条狗随时会攻击她。几步之后,两条狗慢慢停下,望着梅走远,然后转身离开。村里人少了,狗的野性就出来了,马上要变成狼了,梅想。
三大娘拄着她的红漆龙头拐杖,手里握着个小布人,站着自家门口,身子不动,弯成了老树根。凌乱的白发微微的摆动,头慢腾腾的这边扭一下那边扭一下。院里的一棵柿子树有一半的枝干伸出了院外,零星挂着几个泛着白的青柿子。梅看看三大娘,笑笑,她没反应。灰白色的眼睛睁的老大,瞅着梅,有些疑惑。三大娘,出来凉快啦?梅说。啊,啊,是梅啊,唉,你瞧瞧,眼花的啥都看不清喽,三大娘认出了梅。
梅握住三大娘的手,像握着几根枯树枝,三大娘说,小红好闺女啊,也成了家了,可真快啊!梅一愣,忙说,是啊是啊。梅问,三大娘,他们给你打电话没有啊?三大娘知道梅说的他们是谁,缓缓的说,打了,打了,又说,都忙,都忙,妮子说把豆子地里打完药就来。
三大娘五个孩子,两男三女,打工一个比一个跑的远,一般是过年才回来。看样子日子过的都风生水起,家门口停几辆小汽车,走下来的人一个个衣着缤纷,红光满面。车里都带着好多东西,大箱小箱,孩子们喧闹成一片。一旁坐着的三大娘嘴都合不上了,一直笑,仅剩的一颗牙像一个支柱,好像没这个支柱嘴就张不开了。
前年,三大爷死了以后,大儿子就想带母亲去北京,一是在身边好照顾,再是城市啥都方便。开始三大娘是不同意的,说在村里活了一辈子了,那么大岁数了去个生地方不习惯,不去。儿子说,我们常年都不在家,你这么大年纪了,手脚不方便的,一个人咋过?平常还好,要是有病有灾的咋办?我们再快,到家也得好几个小时,到时说啥都晚了。三大娘说,没啥,我能顾住自己,你们谁都不用操心。
后来,拗不过儿子,三大娘还是跟着去了北京,可是去了仨月没到,三大娘就得了一场大病,折腾了大半年算拣回一条命,说啥得回老家。三大娘逢人就说,一回到家啥毛病都没有了,一辈子都离不开这窝。
隔壁村有一个三大娘的外甥女,三大娘叫她妮子,隔三差五来看看,给三大娘洗洗衣服,收拾下东西。三大娘的子女们回来也会给她点钱,还买些东西。村里虽说人少,见天也有人来三大娘家看看,说会话再走。
三大娘有个爱好,村里人都知道,就是做小布人。花花绿绿,大大小小,屋里的床上,椅子上,院里,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好多的小布人,还经常送给别人。她老是和那些布人说话,絮絮叨叨也不知说的啥。不知道的人进了三大娘的家,看着一个个站着坐着躺着的,会以为家里有那么多人呢。外甥女时不时的去镇上的服装厂给她收拾些碎布头回来。
你这是干啥去啊,三大娘看着梅问。我没事,去地里看看。哦,去地里看看,三大娘重复着梅的话。走出老远,梅回身看看,三大娘还站在那里,朝着她看。
村后是一条河,河外边是砖头铺成的东西路,通向庄稼地。顺着这条路往外走就是出去离开村子的路,四面八方能到这世界的每一个地方,村里的人沿着这条路走出去,到处散落,像一颗颗种子在这片大地上撒下,生根开花结果;而往路的这边走就只到一个地方,那就是村子,每年春节,村里在外的人就是沿着这条路回到村里,到各自的家,村子就充实起来,热闹起来。这一刻,路上干净的很,连只鸡都没有,偶尔会有一只蛤蟆从河里爬到路上,再钻入路这边的庄稼地里。河里蛤蟆一阵接一阵的叫唤,热闹,梅听着有些高兴。
一阵风吹来,带着凉意,梅仰起脸,甩了甩头发。眼看着夏天就过去了,真是热的难受。梅现在越来越厌烦夏天,又热又脏,到处都飘荡着灼热的腐烂气息。是不是因为年龄大了才这样感觉?以前可不是这样,小时候一到夏天,赤着脚扑踏着到处疯跑,也没觉得多热。
还是那些年的日子好。
离婚的时候,梅要了女儿和村里的房子。那阵子,连她自己也没想到心里会那么平静。石头晚上回来越来越晚,有时一夜不归,她一打电话过去,就是和工地上管事的或者甲方谈事,喝酒,吃饭,唱歌,洗澡,后来她也就懒得问了。当她怀疑石头在外面有事时,是晚上睡觉时发现他衣服上粘着的几根长头发,和怪怪的香水味。头发是被成的黄颜色,长长的吸附在上衣后背上。一夜没睡好,第二天想问他,嘴动了动却没说出来。过没几天,衣服上又有头发,还是怪怪的香水味,和上次一样。她盯着头发看了一会儿,和上次的一样。第二天一早问他,他一愣,很快说,吃饭是他们那边带几个女的,一个一个来回的敬酒,不定是谁的掉我衣服上了,也可能是唱歌时弄的,人多,一屋子乱糟糟的,身上粘根头发不是很正常。正常吗?梅看着男人,男人眼神有些游移,咋不正常?正常。梅不再问下去,那以后,心里就有了隔膜,俩人之间的那些激情慢慢就淡了。有时,石头身子凑过来,她就厌烦的推开,敷衍说,太困了,我得睡觉,或者说,这几天身子不舒服。有时事后,她会立即起来洗澡,使劲的洗。她对那些事越来越生厌。一次两次,睡一块越来越别扭,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两个人睡不到一张床上了,后来就一个沙发一个床。石头晚上回来,一身的烟酒香水混合的怪味,屋里都填满了,她就心烦,赶紧让他自己脱了,扔阳台上,洗澡去。
只是为了孩子和习惯了的生活才在一起吧,她想。
当她知道石头外面真有了女人时,心里还是震了一下,像是突然被人从背后踹了一脚,不想哭,泪却不停往下落。公公当着梅的面骂了儿子一句,没良心的东西,你对起谁你说?也就不说啥了。梅知道,公公跟着儿子过生活,不能闹太僵,不然他不会好过。梅没闹也没吵,提不起那个劲儿,没那种冲动,像是在心里早已接受这个事实了,只是在等大家撕破脸的那一刻。石头看上去也一副心安理得的样子,看不出一点歉意。梅看着他,咋也和当初认识的那个石头合不到一块。
把远远的转学手续办妥后,回来的前几天,她带着远远在上海一直逛,来福士,新世界,百盛,买了一堆堆的东西,自己的,远远的,装满了两个旅行箱。她想,这辈子再也不会一年一年的来这个地方了,年都过不安生,慌里慌张的来,最后都捞了个这结果。火车上,她翻来覆去睡不着,断断续续压抑着声音哭了一夜。远远也不知听到了没有,在昏暗的车厢里,从对面说,妈妈,睡吧。
梅看见了路边的那幢二层小楼,贴满了白的红的瓷砖,很显眼,那是书记老奎的,村里最阔气的房子。长年在家也不知哪来的钱,都说不是好来的,谁知道呢?满仓正在和书记喝酒吧?就他两个人?不一定,可能是乡里下来人了,或者是老奎家来亲戚了。只要不外出,满仓老是和老奎混一块,老奎要是出个啥事,他也跑不了。爹娘都不在了,女人也走了,孩子也没有,弟兄姐妹都有一家子,谁家没有一摊子事?哪个有闲心能顾得了他?混了多少年还是孤零零一个人,就这还见天乐呵呵的,也不知心咋想的。这两年是年轻,过几年岁数大了呢?动不了了呢?靠谁去?
梅的爹和娘在北京靠着一个老乡关系在一个小区里打扫卫生,过年也不回来,回来干啥呢?儿子孙子也不在家,老俩口在哪不是过年呢?爹娘知道梅的事后就打电话过来,娘说没几句就哭了,说梅啊,你个傻妮子,咋不好好过日子呢?俩口子哪有不闹别扭的?缓缓就过去了,怄那个气干啥?你是没当有这爹娘啊,这么大的事先前也不说一声。梅就有些心烦,说我自己的日子我知道咋过,没事,你们都不用操心,没事就挂了吧,过几天我再给你们打。梅的哥一家在新疆,他岳父在那做门窗生意,他们就投靠去了。哥老实,被嫂子训得像条夹着尾巴的狗,又加上是在岳父家生活,整天连大气都不敢出了。一年也不跟爹娘打个电话,更别说看望了,一年一年待在新疆,过年也不回家。开始爹娘还对着梅和妹妹雪抱怨几句,看来是等我和你爹断气了他才回来,现在成了个倒插门了,没一点良心,当初养活他干啥。后来也习惯了,电话里很少提哥嫂的事。雪嫁到了省城,网上谈的,黑不溜秋的,个子矮,长得歪歪扭扭的,下边还有个弟弟,一家的收入就靠着爹娘养的几头奶牛生活。当时爹娘死活都不同意,娘对雪说,嫁他你都不如嫁南坡的哑巴,他养鸡又养猪,一年也挣好几万呢。娘又张罗着托人给雪找对象,可雪滴水不进,说爱咋找咋找,反正给我没关系,我也不见。娘气得骂她,你个死妮子,哪远滚哪去!后来雪竟偷偷跑人家家去了,说啥都不回来,这边家里也办法了,只能同意,办了婚事。嫁过去没两年,那家赶上了拆迁,于是,又是给钱又是给房子的,一下子就成了暴发户。这边爹娘心里也好受点,娘说,二闺女也算是个有福的上人,这都是命赶的,就是那孩人长的不大可意。雪给梅打过一次电话,把石头骂了一顿,看着挺老实一个人咋会干出这事来?当初穷的时候咋不说离?整天跟个哈巴狗一个熊样。你也是傻,要村里那房子有啥用?值几个钱?他不是有钱吗?不出个十万二十万的谁给他离啊?你可真是,也不知咋想的,越活越不明白了,离婚你给谁也不说,现在谁也管不了你,享福受罪都是你自己选的。雪在电话里说,她上班忙,又要带孩子,刚上学离不了人照顾,暂时顾不上回去看她,就让梅啥时候去省城找她。梅答应着好好,俩人就没了下文。
现在远远在县中学上初一,住校,两周回家一趟。在上海那边上学也不让外地人参加高考,中国制度就这样,没地方说理。学的课程和家里也不一样,还不如早回来上学,基础还学的牢些。去年和石头离婚之前她就想好了,女儿得归她,啥都不要也得要女儿,她可不想让女儿跟着那内蒙女人过日子,后妈有几个不坑害孩子的?石头也没反对,看样子他很乐意,当初生孩子之前他就想要儿子,有儿子了跟人说话才有底气,他说。梅白了他一眼,反正这辈子我就远远一个。
那天,公公把她叫到一边,说,梅,家里的老宅你住着,好好带着小远,我儿媳妇就你一个,别的他娘的屁也不是,还叫我爸,呸,她当我稀罕?我可受不起。看着吧,石头他个兔孙他和那女人长不了。公公还要说,梅就把话拦住了,说,您放心吧,孩子我会带好,家里房子我就先住着,不然孩子没个家了。
从上海回来的前一天,石头给了她一张银行卡,对他说,这里面有点钱,你和远远先用着,不够了再说。他把卡塞到她手里,她没说话,看着手里的卡,她想扔给他,手抬了抬,一犹豫,只是把卡在另一只手上敲了敲,撇嘴轻笑了一下,心里乱糟糟的。
玉米地里呼呼啦啦的一阵响动,忽然窜出几条狗,在路上追逐,狂吠,往远处去了。狗叫声似乎得到了回应,梅身后的村子里也传出了一阵狗叫。
对面有个模糊的黑影在动,是一条狗?梅仔细望了望,是一个人,正向这边走来。空旷的野地,冷清的村路,路的两端,两个人在各自移动,那个未知的黑影正在靠近,在铅灰色的天底下一晃一晃。梅有些心慌,想转回身回家。庄稼有啥看的,看这天雨还是会下,随它去,反正也不指着这二亩地活着。梅停下来,有些犹豫,那就是个人,我怕啥,大白天的,还能吃了我?他走他的,我走我的。
梅抓紧了手里的篮子和伞,继续往前走。
身后的村子在灰色的天空下显得有些模糊,路两边都是庄稼地,玉米一人多高,顶端开着花,中间的玉米棒子吐着一丝丝红的黄的穗。叶子在风里呼啦啦响,一棵棵紧挨着,幽深的安静,整片整片的看不到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