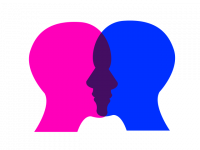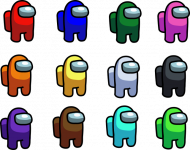西边河
(一)

不知何时起,连槐荫树叶上的闪光都分外刺眼了,才明白蝉已叫得不耐烦了。
木头和胖子一起,赤着膀子坐在塘埂上的槐荫树下盛凉。槐荫树洒下清凉的碎光,偶尔还有从河边吹来的凉爽的清风,这里是这个夏季午后最好的去处了。
看一眼河对面的一大片青黄,那里还有人冒着烈日在田中劳作。木头也是刚从那田里下来的,腿上还沾着黑色的淤泥,这会儿已经干涸成灰白色的了。在这青黄不接的时候,这一场干旱无疑又为所有人增添了太重的负担。木头叹了一声,转过头来,看胖子整个人堆在地上,舌头伸得老长。不由得扑哧一笑:“你真像我们家大黄!(大黄是条狗)”然而胖子只是愤怒地冲着木头送去他的一双白眼,然后继续趴着。木头知道胖子占到了一个极好的去处,以前,那个地方一直是自己的,但今儿胖子来得比自己早,提前占窝了。
不久,随着一阵叽叽喳喳的打闹声,槐荫树树上树下也便满满地是一群亮着膀子的小毛孩儿了。他们来了,在这安静的午后,便也来了些许喧嚣。木头望了一眼胖子,然后一纵身,爬上了槐荫树,和猴子分坐在两撇大枝杈上。从猴子手中接下他刚准备吃的黄瓜,咬了一口:“你又在我家菜地里摘的?你最好别让我奶奶捉住,小心她打断你的狗腿!”猴子便是一脸无辜了:“这是我自家的!上次摘了你家的瓜,那能怪我吗?你家的瓜藤都长到我家园子来了!再说,那瓜最后还是被你吃了……”猴子说完,郁闷地看了木头一眼,木头却是神经大条的一脸事不关己,继续津津有味地啃着黄瓜。然后咬了两口又扔回了猴子:“这瓜不甜,没有我家的好吃!你以后还是摘我家的瓜吧!”猴子嘿嘿笑两声,接过瓜,也不擦一下,直接也如木头一般咬了下去。
槐荫树是在塘埂上的,左方是塘,右方是河。此时的河水因干旱只盛一浅底了,最深处也不过膝盖。除了胖子及树上的两个,其他孩子便尽在水里了,坐着,躺着,趴着,正如河坪上的一头老水牛,在泥淖里刷刷地甩尾巴。
也不知过了多久,大人们也尽些都出来了,去了田里,地里。老人们聚在某家屋檐阴凉的地方,摇着蒲扇,说一些有的没的趣事,年轻一辈是不愿意听的。突然,李奶奶望着前方惊呼一声:“哎哟喂!”众人一惊,回头,却听见塘堤上传来木头的惨叫。
木头捂着自己的脚板,那一道深深的口子,伴着汩汩不停住往外流的红色液体,一下子,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猴子跳下树,满脸通红地在一旁站着。
胖子起来,拖着庞大的躯体扶着木头下河把脚洗干净。可是血仍旧不住地流,晕红了一大片河水。而木头,早已疼得紧咬嘴唇,面无血色,满头大汗。
“快喊毛姑回来!她会止血。”男孩子们见止不住血,有些慌了。三五人一边向前方田里跑去,一边大喊:“毛姑快回来,木头出事了!”
于是,猴子和胖子一起背着木头回到毛姑家。“在纱布上洒上云南白药!”“把小腿系紧!”“把纱布缠好!”……几人一阵手忙脚乱,而木头脚上的血不住地滴在土地上,落成一朵朵凄惨的小花。
后来听说木头的脚落下了残疾,具体是不是从这个夏天开始的就不知道了。
(二)
“哪个叫你去西边河洗冷水澡的?你嫌命长是不?你胆子肥了你!”
“我说了我没去!”登夺门而出,凶神恶煞的,脸上有两个红红的巴掌印:“妈的!哪个瞎说?啊?狗日的!是哪个嚼舌头的,我今天非杀了他不可!”
门外本还在玩耍的孩子一哄而散。顿时,诺大的谷场竟只剩下如一头发了疯的小牛般的登了。
而在不远处的谷场边,拿着蒲扇坐在青石板上的老人,眼中尽是毫无遮掩的厌弃:“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跟他那死去的老子真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登徒子!没教养!”你一句来,我一句去,慢慢的竟是说到了后代如何不孝,说到了谁家媳妇儿是如何不敬公婆,说到了谁家女人偷了谁家男人……
当然,登是没空理会这些老人的闲言闲语的。揉着有些青肿的脸,看着身后怒气冲冲的妇女,他一溜烟地逃了。而后面出来的妇女,紧皱着眉毛,看着撤腿就跑的儿子,本来紧绷的脸“扑”地一声笑喷了。叉着腰,指着登大声喊:“你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吗?你有种一直跑。看今天晚上不打断你的狗腿!”
与此同时,整个塆子里的孩子,都在面对着自己父母黑着的脸,战战惊惊。那阵式,估计连包公审犯人也没这样的压力。
傍晚,天空来了一场火烧云。淡红色的光芒如薄纱般轻罩着整个大地,人们抬头仰望天空变幻着千般形态的云朵,呆呆地竟似醉了。不久,一支浩浩荡荡的牛队从后山路上驰骋而下,那不成调的叶哨声又引得刚停下来的蝉儿一阵欢唱。
登背着鱼网从西边河归来,脸上是一种丰收的喜悦。耗子跟在他身后,提着一桶鱼虾,沉甸甸的。
当天空全黑了下来,在塘堤上,孩子们燃起了一堆篝火。他们围成一堆,用竹签串着小鱼小虾在火上烤,脸上映着火的红光,汗水慢慢地流淌。当伴随着一阵阵妙不可言的肉香从火堆中飘了出来,孩子们的眼睛开始放亮,不自觉地吞了吞口水。但大孩子,比如登和耗子他们,他们都知道还得等一会儿才能尝到真正的美味。而小一点的孩子就按纳不住了,拿起小鱼,狼吞虎咽,但还是满足的一摸嘴,回到桶边看看,然后一脸失望地回头,看着大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
塘水如一面镜子,映照着满天繁星。登与耗子并排坐在塘堤上,望着天空发呆。其他人尽都被自家大人喊回家了。突然间,塘堤上就安静下来了,只剩下篝火明明灭灭,偶尔闪映出两条孤寂的影。
“扑嗵!”“扑嗵!”,两条身影在空中划出两条优美的弧线,在塘里激起两朵晶莹的水花,化作满天星辰飞溅。随后,塘面又恢复平静,清风微抚,塘边芦苇轻轻飘荡,受惊的野鸭也停止了“嗄嗄”的叫声。突然,在塘的对面突兀地出现了两朵浪花,一群刚平静下来的野鸭再次吓得魂不附体地在水面一阵扑腾。在那一群慌乱分飞的野鸭中,传来了两个少年肆无忌惮的哈哈大笑……然后,也不知是水还是泪自脸上流了下来,滴在水里激起一圈圈涟漪。
“你知道吗?在新塆淹死了一个孩子啊。听说是前天下午淹死的,今天早上有人发现河面上漂着一条泡得发白,不成人样的尸体。手里还紧紧地抓着一把草哩!听说是遇到水鬼了……”这个消息是中午在塆子里传开的。
据说,那个淹死的孩子前不久也曾到过西边河洗冷水澡的。
(三)
西边河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候非早晨莫属了。
夏季的白天来得早,太阳是跟着西边河里的梆子浣衣声出来的。
引子和弟弟抬着一桶衣服向西边河里最广阔最清澈的龙颈崖走去。在穿过羊儿湾的田岸上的小路时,弟弟曾经被挤下了泥田里,成了一条活生生的泥鳅。那次母亲将引子狠狠地打了一顿,并再也不许弟弟跟着引子一起去龙颈崖了。但弟弟总是偷偷地跟着引子往龙颈崖跑,这次也不例外。
在路上,引子碰到了细敏。在过小路时,是细敏帮着引子抬衣服的,而弟弟则帮她们拿着梆子。
远远地就听到了龙颈崖水流的声音。不久,就望见一条白练从青灰色的石崖顶上铺下,落入幽绿色的水潭,激起一团团白色的泡沫。潭边能洗衣服的好地方都已被占用得差不多了。引子向二姑,三奶她们问声好,望着自己昨天洗衣服的地方,那里已被花儿占用了。
“引子,我们到对面去吧!”细敏见没位置,便提议道。那潭子对面,也就是瀑布下方,的确有两个极佳的去处,然而怎么过去却是一个大问题。但引子看一看那逐渐升起的太阳,终是点了点头。嘱咐一声弟弟,让他自己玩但别到处瞎跑,便和细敏两人趴在光滑的石壁上,一步步向潭子对面挪去。
在洗衣的妇人们看着一大一小俩孩子艰难地走着,眼中尽是骇然与担忧,想阻止她们却又不敢冒然发出声音,怕吓着她们。所幸,她俩都安全到达了对面。
当太阳从山口冒出红红的脑袋,在崖壁上出现了一道艳丽的彩虹,幽绿的潭水闪烁着金光,洗衣的人如置身云端。然而,她们对这种景象似乎视而不见,抬头望了一眼彩虹,便埋头加快了洗衣的速度。引子眼中也没有任何惊喜的波动,毕竟,再新奇的东西,再美丽的景色,看得多了,便也就平凡了。
洗衣的人陆续回去,就只剩下三三两两的老妇人与引子,细敏她们了。
引子把最后一件衣服扭干,准备回家了。抬头,却发现一直在石头上玩耍的弟弟不见了,喊了一声弟弟。突然,一个黑影从斜上方沿着石壁滑了下来,像一个石头样“扑”地一声落到潭里,溅起一大朵浪花尽数飞到了细敏身上。细敏一惊,不觉往后一退,脚下的石头却是被踩翻了,然后细敏整个人一头栽进水里!
“弟弟!细敏!”引子分明看到那滑下来的黑影便是自己的弟弟,还没回过神来,细敏又落进水里了。这潭子可有三米深呢!“救命啊!来人啊!有人落水里了!”引子扯着嗓子大喊,尖锐的声音穿破清晨的宁静,让人毛骨悚然。
同时,引子来不及多想,一纵身跳下水去,向潭下的细敏游去。而细敏在水下愣了几秒,看到引子,转身,向引子的弟弟游去。
引子背着湿淋淋的弟弟回家,又被母亲打了一顿。她倔强地站在那里,第一次忍着没有流出泪水。
(四)
当冬季的第一缕阳光落在西边河时,河岸晶莹的冰条折射着彩虹般的光芒。河面结了一层薄冰,依稀能够听到冰下低声呜咽的水流,犹自在缓缓地向前挪去。
突然,有一团鲜红的火苗在沿河向下游漂去,透着妖魅般的诡异以及令人心颤的汹涌澎湃的迎面而来的悲伤。
那是穿着嫁衣的明霞。
中午,人们慵懒地靠着向阳的墙边晒太阳,汲取那寒冬里最珍贵的资源。不知是谁谈到了明霞,然后就有人惊呼:“明霞好像又发病了!今早穿着红色衣服沿河走下去,把我家的老牛都吓得发疯了,扯断了绳子!我找了一上午的牛!”“谁说不是啊,太吓人了!她到现在还没回来哩!她家里人都出去找去了。”于是,人们便活跃了,有人摇头叹息,暗自伤感,有人吐舌缩脑,惊恐万分,也有人斜眼厌弃,义愤填膺。
“为什么不把她送到医院去?她们家有钱着哩!何必留这样一个定时炸弹在塆子里!搞得我们提心吊胆,寝食难安的!听说她还打小孩儿啊!”有人满腔愤懑,最后,竟然怂恿众人去明霞家理论:“走!我们去讨个说法!让二麻她们把明霞送走,再也不接回来了。她总是发病,而且越来越狠,要是打伤人时就迟了!”
二麻看着面前这一群熟悉的面孔,看着她们怒气冲冲地赖在家里不走,心冷了下来。明霞的病已经够让人伤心了,她却没想到身后还有这么一群人在捅刀子。平时跟他们也没什么过节啊,不都相处得挺好的吗?你们不帮忙找人就算了,还要无理取闹地耍流氓?
是什么时候起,大家都变成这样的了呢?
二麻说着好话,做了一桌子菜,这些人大大方方地坐在桌子上,还要了酒。而下午,他们仍旧不走,坐在二麻的院子里,剔着牙,眯着眼晒太阳。
明霞最终没有回来,永远也不可能回来了。
当二麻听说明霞的尸体在河的下游找到时,泪呼地涌了出来。而那群吃饱喝足的人,终于是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满意地走了。
二麻看着他们离去时有说有笑的身影,抱着刚刚放学回家的孙子,眼睛在夕阳下闪着一道异样的光芒。
(五)
没有人知道西边河的冰锥是何时落在水里溶化掉了,只是那河岸的柳枝吐出了嫩黄的芽,一群野鸭从开始抽新绿的芦苇里探出了头,金色的阳光便洒在了整个河面。
毛爹是因为打水和桥爷打起来的。塆子里的人都看着,远远地避着,却指指点点,有说有笑。的确,在这并不是很忙的季节,看一出亲兄弟间的生死悲喜剧,也是一种不错的消遣。当毛姑从田里回来,发现了,便拆开了他们。而此时,他们彼此都已头破血流,而毛姑脸上也青肿了几块,是不小心被他俩的拳头打的。
第二天,毛爹去桥爷田里,不小心从田岸上摔了下来,摔了脑子。本来是没事的,毛爹这些年也没少摔过,也没出过什么大事。可是这天晚上,他就那么瘫了。而发现毛爹瘫的人是毛姑,却也是在两天之后了。那时毛爹像一个死人一样躺在满是稻草的木头床上,浑身散发的臭气与茅草屋里的霉气混合在一起,刺得人直掉眼泪。
桥爷帮毛爹稍微清洗了一下。没有人请医生,桥爷请不起。毛姑叫村上的乡医来看了一下,说是中风便走了。人们都知道毛爹要走了,却也没有人伤感了。塆里人依旧各家欢乐各家愁,谁也没在意那塆中间旮旯里的毛爹。
晚上,毛姑正在家做晚饭。桂芬来了,扭扭捏捏地摇晃着她那瘦弱的小小身板。毛姑见了,问怎么了。桂芬说她二叔,也就是毛爹,想要吃咸蛋。说毛爹最喜欢吃咸蛋,说毛爹只在毛姑家吃过咸蛋。于是,毛姑把泥罐里仅剩的六个咸蛋都合着米汤煮了。等蛋熟了,和桂芬一起去了毛爹的茅草屋。
次日清晨,桥爷发现毛爹已没了呼吸。
给毛爹下葬的人都感到很奇怪,毛爹死前脸上是一种令人十分舒服的安祥的,满足的笑容。比那些富贵人家的人走得安心多了。
就像,就像那塆中祠堂里拈花一笑的迦叶。
(六)
后来,西边河干了。
塘堤上的槐荫树都被砍伐殆尽了,剩下光秃秃的桩,在炎炎夏日下泛着灰暗的死黑色。
塘里没有了蛙鸣,也没有了成双成对的野鸭,只是偶尔会突然浮上一只只翻露出白白大肚皮的鲢子,在青黑色的水面上泛着冷光。
有一年,龙颈崖的水也被抽干了。人们看到水底沉着十几具白骨,骨头上长着长长的像头发一样的绿色水草。
然后,当木头们也老去了,就没有人记得这个塆子曾有一条河,叫作“西边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