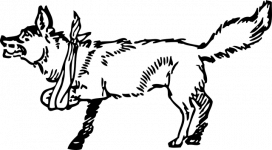铁匠的生日礼物
他用他那只肥厚的手掌揩了揩脖子上的血迹,站在一片衰草的园子里,两片淡紫色的厚唇里肮脏粗俗的辱骂声朝身后的黄砖房里飘去,屋里一个女人哀伤低沉的哭骂着。

对于这样的午后插曲,大家早已见惯不怪,至于他的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早就对这样的生活麻木了,本就有一女是哑巴,就算拳头落在她身上她也是光流泪闪躲,一声哀怨和祈求声都是发不出的;而其他两个早就不会哭了,当男人的铁铲和棍棒落至身上时,就那么直愣愣的挨着,不声不吭,从儿时挨到大。
男人本是一个铁匠,一家生活开支全都仰仗于他,他本生得高大肥厚,到中年来,身体越加发福,两边浑圆的肩膀上顶着一张方头大耳的圆脸,一天到晚都挂着一副对别人献媚嘴脸,笑起来时,一对肥厚的嘴唇朝两边咧着,两只眼眯成一条线,一个浑圆硕大的肚子,跟着他的笑一起一伏的抖着。
今天本是他生日,他想大摆筵席,收点礼金,好把家里几间瓦房全都翻修翻修;他的妻子却死活不同意,说什么前几次不是上梁就是生病为借口的酒宴,请得亲朋好友竟是嘲讽的语气,说什么也不愿再丢脸了。他想起这些话来,心里又狠狠的把那还在屋里哭泣的女人骂了一遍:“整个败家娘们儿,好赚的钱不赚,整天就知道好吃懒做,唯唯诺诺的。”他忘记了他的礼金只收不出,孩子和女人们受尽了邻里亲朋的嘲讽。
他顶着他那硕大的肚子,朝村边的小路上走去,本是好好的日子,如今心里好不火大。已将近是霜降,到处一片冷清,小道边的杂草丛林一片病态,枝头将落未落的枯叶在微风里打颤。他又伸手揩了揩了脖子上的伤,再用手好好摸摸,发现再也揩拭不出丁点血迹来,才把他身上过小的清灰色中山衣领子拉起来,遮住女人在他脖子上留下的抓痕。
橘黄色的太阳洒在清冷的小路上,枯草上的露珠在和煦的微光里,显得更加圆润剔透;他一双解放鞋早已被这圆润剔透浸得半湿,那件半旧的清灰裳也抵挡不住北来的微风,那肥硕的身子即也是如同枝头苍黄的病叶般在微风里发着颤。昨夜,因只顾着如何多捞点钱,兴奋得连晚饭都没吃,今儿早上又干了如此大的“体力活”,他那如灌了半瓢水的肥肠里,随着他的脚步咕噜,咕噜的声响从厚厚的皮下脂肪里传至他的耳膜;他舔了舔紫红色的唇,在一间矮小的茅舍旁停下,屋里传来嬉笑与猪油的香味全都进了他的鼻子。
他兀的推门进去,屋里的大人小孩都惊诧在那儿,即也忘记了嬉笑,屋主妇人正轻轻用力翻转锅里的荞麦饼,一把小锅铲沿着荞麦饼边缘起起落落,见是她来也不说话,刚还微笑的脸颊,因这突兀的到来,笑是笑不出来却又在霎时间收敛不了,竟显得整张脸僵硬在那儿。
他是不会看那张脸的,他的目光全在那锅里的饼上,在那脂肪堆积的喉管下,唾沫在里面迅速的活动着,终也还是进了体面人家,不得不招呼他坐下。在他吞咽第二张荞饼时候,屋主妇人把调匀了的荞面搁下了,招呼孩子们看家,说还有地里活要忙,要和自己男人去山上了,孩子们兀自把嘴撅得老高,摔门而去。别人要忙,他虽还没有吃饱可也不得不离开;拿着那半张饼,出了茅舍,边走边咀嚼着,遇到人,就大声打着招呼,一手不忘了举起手里的饼,大肆宣传自己是如何的待遇;旁人也知他为人,都是一脸揶揄的笑。
他那硕大的肚子一起一伏的跟着他在黄沙的小路与一片白田的田塍小道上不知疲倦的走着。恍惚半响,应是那两张薄饼悉数吸收殆尽了,他开始觉得两腿也跟着劳累了起来,竟觉得时间是如此百无聊赖了,周遭风景变得可狰了起来。又用了同早上的方法,他今天的中午饭有了着落。
村里人家本是大大小小生活铁器都得劳烦他,大到生活用具,小到缝衣针,他虽再不知餍足,也无谁硬挑明了说;这时间一长,他竟再不觉得有任何不妥了,谁家妇人手艺好,谁家菜里油水多,他是一清二楚。东家唠嗑西家久坐,待西山残阳褪去时,他估摸着家里那女人脾气也冷却下来了,就又从早上来的小路,一路哼着小调回家去。
他走到小院时候,天也暗了下来,鹅黄色的灯光在打落在窗下,一屋的死寂;他推开门时候,破天荒发现女人孩子都坐在饭桌旁,桌上一桌子的菜,他本想破开大骂他们不知节省,如此铺张浪费;可忽又想起早上才打了女人孩子,原来都是几个礼拜不理自己,终还是自己家人心疼自己爱自己,知今天是自己生日,才舍得做这一桌子吃的;想到这里,他那狭小的眼眶内溢出了一泓清泪来,笑也不是说也不是,朝女人孩子看着,一张油光水滑的脸上,褶子之间竟也显现出缕缕和蔼可亲了。
他坐下,儿子就忙给他倒酒,一女也忙去给他盛饭,女人坐到对面也不望他,埋头咀嚼饭菜,就那聋哑的女儿,看着他掉泪。他想着平时候的打骂与如今孩子们的乖巧,心里又是一阵难受,忙给那聋哑的女儿夹了一大筷子的肉,一边忙用衣袖揩了揩自己脸。
第二天拂晓时,鸣笛的警报声把一村的男女老少从睡梦中唤醒了起来,全都聚集在铁匠家小院里;红色的警戒线围了一圈,穿着青色警服的警察与白色大褂的法医,在小院里忙成一团。院子里到处都是斑驳的血迹,铁匠呈大字型摆在院子里,苍白的脖子上一条粗粗的勒痕,也呈黑青色了,身上衣服破败不堪,全身上下污血凝结在一起,法医剪去衣裳,清理了污血,发现全身都是伤痕,刀、棍棒、铁钳、拳头各式各样留下的痕迹。
而这些都不是死亡的致命原因,脖子上的勒痕也不是致命原因,在一双双白手套的不停翻转下,一个细心的法医,发现头上,在那根根黑丝中间还在不停的向外渗这血,又是几个人剃发清洗血迹后,在那渗血的地方,又是按压又是抚摸下,他们从里面拔出了一根长至6cm的水泥钉,这下他们知道人是怎么死的了;萧瑟的秋风吹来,他们似在盛夏般个个脸上挂满了豆大的汗珠。
女人和孩子从上警车后,就没有回来过了,丧事终还是要办的;那不满18岁的聋哑女,是这场丧事的主办者也是唯一的戴孝者;看着身边来来往往的脚步与一双双敲击锣鼓的手掌无动于衷,蜷缩在堂屋的一角兀自打着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