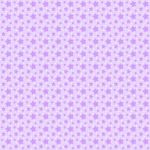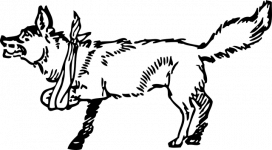熄灭参考
一

布明是我的本家,祖上是一个爷爷。他是长房的老二,人生得实在老实,从小就没怎么当二分钱数,村里人都喊他:亨子。意即喊一下动一下,不喊就不动。
他家住在四进老宅的最前面,由于家庭成份高,从小又学不进去,整天待在家,平时帮家里种田,闲时队里兴修水利,就派他去挖沟挑河,他从不拒绝,不是推,就是挑。好一点事轮不到他,别人不愿干的就派给他。他有一个特点:饭量大,力气大,一吃就是几大碗。
阴天下雨,出不了工,有人喊他:布明,走,趟螺丝去。他就自制一付推网,和别人一起满河沟跑,把螺丝推回来,用螺丝肉和毛豆、茄子、辣椒做成毛豆螺丝酱,那个年代,是一家人的美味。每次我馋得不想回去,被母亲拎起耳朵拽回家。
有一年夏天,突然变天,队里晒场上晒了一地的麦子,大风大雨很快将至,大家把麦子收起,用草帘围盖起来。但风实在太大,刚盖上就被吹走。大家把能压的东西全压在上面,还是不行。这时,不知布明从哪里出现,一手夹了一块破磨盘,从风雨中走过来,一趟两趟,很快将最大的麦堆压好。事后,村里人夸道:真是想不到,亨子还有这本事。
又一年夏季,布明的母亲,我的大妈,正在纺车上纺线,突然邻村来了一堆人,对大妈喊道:“你家布明偷我们生产队里的玉米,要批斗,你要陪斗去”。说着,大妈被来人拉起就走。
我尚小,不知怎么回事,就跟去看。
布明被反捆着,斜躺在邻村养猪场的大灶边。旁边是布明的衣服,口袋里塞着一些刚掰下不久的玉米。邻村的人一边骂,一边用皮带抽。布明满地打滚,脸上身上全是血。
“我看你还敢不敢再偷”,抽打人还不够出气。
“我家赔,我家赔,不要打了”。大妈心疼得呼天抢地。
“你家拿什么赔?”邻村的人问。“我家拿口粮赔”。
随着布明老大、老三一家相继到来,最终写了赔三十斤谷子的纸条,才让家人将布明带回家。
布明躺在堂屋里,浑身疼得喊爹叫娘。大妈一边用热水替他擦洗,一边问他:“你怎么做这个蠢事的呀?”
布明哭着说:“妈,我吃不饱,肚子饿得难受,就想掰几个回来煮一下”。
大妈一边叹气,“就是饿死也不能做这个呆事呀!你不是不知道你家成份高,没打死你,就算你走运了”。
那一夜,睡在后屋的我,一直听布明哼到天明。
从此后,布明更寡言了,除了干活,什么话都不说。
二
有一年,表姑村上来了一个人,对大妈说:“也该给布明做亲了,不小啦。老大、老三都有孩子了,他还没结婚”。
“这个亨子到哪里寻人(家乡话找对象)啊?”大妈一边纺线,一边哀声叹气。
来人说:“我们村上倒是有一个,就是就点痴呆,也不严重。如果不嫌的话,倒是可以给布明做媒的。”
“巴不得啊。我们年纪越来越大,布明不结婚也是个心事”。
这件事就这样定下了。
先是女方家带着姑娘来看,那姑娘一直呆呆地躲在父母身后,低着头不吱声。媒人带着姑娘及父母房前屋后转了一圈,问姑娘:“还行啊?”姑娘愣了半天,说了两个字:“妈定”。
后来,布明一家又去姑娘家访亲,三间草屋,半亩菜地,问布明:“你说怎么样啊?”布明愣了半天,说:“由我妈定”。
亲事就这样定下了。
双方家中都比较穷,婚事也办得极简单,一床被子,两个痰盂,几件衣裳,就算成亲了。
婚后,一直没有动静,大妈很是着急,“不知道亨子知不知道男女之间的事”。大妈几次欲开口,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大妈让长嫂去和布明的媳妇说说。
果然,不久布明媳妇的肚子就开始大了起来。
竟然生了一个大头儿子,全家欢喜得不得了。后来发现,儿子也是亨子,但比布明好一些。村里人看到布明媳妇抱着儿子到处转,就故意逗她,“不是布明的吧?”。布明媳妇咧着嘴笑:“骗我”。
尽管儿子不善言语,人倒也长得不错,布明非常开心。媳妇在家,布明拼命地拼工分,后来又拼命地种田。由于家里没有收入,布明处处节省,蚕豆熟了,他去捡掉落在地上的蚕豆;黄豆熟了,去捡地里长出的豆芽;稻子熟了,去捡落下的稻穗。有时地里没人,他偷偷地拽几株别人家的花生,走人家门口,摘几把菊叶带回家。
时间久了,村上人都知道布明染上占小便宜的习惯。
布明倒是很疼媳妇和儿子。谁要是欺侮他媳妇和儿子,布明扛起铁锹就冲上去。家里难得有好吃的,他总是留给媳妇和儿子,一个人端着粥碗,跑到旁边。有时不知为什么事,布明、媳妇、儿子象中了彩,一家人有说有笑,声音大得全村人都能听见。“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大家都这么说。
三
后来,我离开家乡。其间,本家之间闹矛盾,老大家三兄弟相继搬出祖宅。布明也在老大的帮助下,在一河之隔的新村盖起了三间瓦房。
关于布明的故事就越来越少。只听说他的儿子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去了一家石化企业。
有一年春节,我在村上正好碰到布明,就上去打个招呼:“小哥,现在怎样啊?”
他还是那样,过了半天,才结结巴巴说道:“小哥穷,能做什么呀,种死田。现在老了,身上尽是病”。
夏季的时候,我回去,看他推着独轮车,车上那么多的稻谷,像座山,根本不像七十岁的人。
儿子在外地结婚了,只剩下他和媳妇,守着越来越破旧的三间低平房。
好多年没有他的音讯。
前年时候,弟弟打电话告诉我:“布明出事了”。
我愣了一下。
原来,国家环保政策实施后,农村禁止烧麦秸和稻草,但不少人家为省事,在麦子收割后,剩看护人员不在,偷偷烧。
那天,布明收完麦子后,坐在院子歇息。心里老惦记着媳妇的病。这么长时间好不了,什么活都不能干,儿子也没钱寄回来,如果租用打草机,又要一笔费用。思来想去,又情不自禁地走向麦田。
正是六月天的中午,气温近三十度,又刮起大风。布明鬼使神差,点燃地里的麦杆。大火迅速漫延开来,不断扩散,很快就燃到别人家还没有收割的麦地。布明慌了,急忙脱下衣服扑火。火借风势,风助火威,很快就把布明吞噬于火海之中。等别人发现赶来,布明浑身已烧得一片焦黑。
从镇上医院转到县城,医生扼腕。烧伤面积达95%以上,初步治疗费用100万。布明的儿子只能拿出2万。看着不能动弹,在疼痛中挣扎的布明,所有人都束手无策。
布明儿子在别人指点下,上滴水众筹,亲朋好友纷纷捐助,也只筹到5万元。
消耗了所有的现金,布明从医院转回家,只剩下一条路:等死。
村里人来看他,怪他迂腐,布明睁着眼睛,呆呆地看着房顶,什么话也不说。浑身上下失去皮,全是红通通的肉和发白的关节。布明在疼痛中失去了时间概念,从早到晚,由黑到明,他一遍遍地高喊:火,火,火。要不就是:妈妈呀,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四邻的人拎着东西来看望,对他贪图小利,因小失大的做法埋怨又同情。
布明的媳妇坐在房门口,对进进出出的人不停地点头。
布明的病情越来越恶化,人也渐渐开始昏迷,偶尔嘴里断断续续地喊:妈,我饿,我饿……
二十多天后,布明终于归西。
一盏蜡烛,在黑暗中摇来晃去。
布明死后,被安葬村中的墓园,对面,就是他自己点火烧死自己的地方。空
阔的田野,四周出奇的安静,偶尔,一两只鸟从天空飞过。风,将尚未烧尽的纸灰,一点点吹向天空。
布明的儿子返回单位,他媳妇坐在门口剥蚕豆,村里人又开始各自忙各自的事情。
布明只是先走一步,陪他的父母和老一辈去了。
像村里所有死去的老人一样,布明也渐渐开始被人们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