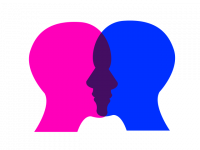霁红梅瓶
“再回首流年空空,待回首碎梦重重!”

他无力地滑坐在地上,表情极其凝重,并怔怔地望着那一地妖冶的红瓷,失神的双眼滚落着两行热泪,砸在那张泛黄的老照片上,砸的心好疼,嘴里不住地呼唤着祖父的名字,一声一声,字字铿锵。
初见这只霁红梅瓶,他仅仅是一个8岁的孩子。高大的祖父从床下费力地翻出一只樟木箱子,这箱子藏得特别隐秘,祖父用颤抖的双手轻轻地摩挲着,古朴的箱子承载着岁月的沧桑,好像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吸引着他。他看着祖父缓缓地打开箱子,拿出了那只看起来很普通却又非常干净的梅瓶,眼中噙着泪花,时不时我好像听到抽泣的声音,但又不敢近距离的却细听。那是怎样的一只梅瓶?殷殷如血,莹莹如玉,在祖父的手上,仿佛有了生命一般。妖冶的红流动着,令他向往却又不敢直视。他偷偷的看了一眼箱子,箱子里面除了梅瓶,还有一些信件和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子柔情绰态,温婉端庄,虽无珠翠点缀,亦无损一身贵气,是何等的佳人,祖父沉思着,他轻轻地拉着祖父的衣角,指了指照片上的女子,满脸疑惑的问了祖父:“这……”祖父好像没有在意我的疑问,顾自地讲述了一个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正是祖父和照片上的女子。
那时的祖父潇洒帅气,刚刚由东洋留学而归,满腹经纶,在昆明这般纸醉金迷的城市,永平纱厂的名号也是响当当的。但祖父并非整日胡混,夜夜笙歌的纨绔子弟,而是潜心于生意。在他的努力下,纱场的生意蒸蒸日上,自此,黄家大少爷在螳螂镇这个地方迅速传播开来。年关将至,社会各界名流齐聚号称“滇南第一乐府”的百乐门,身为新晋名流的祖父亦应邀而去,然而就是在这里,遇到了令他梦萦终生的女子。
“她光着洁白的颈,一颗颗滚圆的珠藏在墨玉色的旗袍下,时隐时现,那秀气的眼神,如花似玉的脸庞,玲珑剔透的嘴唇,而当中那块极具特色艳丽的琉璃,则与绣在身上的彩蝶相得益彰。如玉的肩上,披着一块狐裘。葱葱十指,则以凤仙红点缀。明眸皓齿,眼波流转,巧笑倩兮。一举一动,都牵动着我的心,让我惊叹不已。”
祖父陷入了那惊艳的邂逅,居然忘记了他就站在祖父的身边。他用力地拉了一下祖父的衣角,祖父自觉失言,便牵起他的手,严厉地看着他,不许他把这件事讲出来。他用力地点着头,但心中的疑惑,就一直蔓延着他十多年,直到他26岁那年,谜团才抽丝拨茧,谜底一点一点,浮出水面。
十八年后的祖父已经年迈,高大的身影早已经佝偻,头发花白,双眼失去了当年的神采,甚至有时开始胡言乱语,满脸皱纹相伴,手脚极其不方便,但祖父经历一辈子的沧海桑田。看着祖父日渐消瘦下去,他明白祖父一辈子放不下的就是对那箱子里的秘密,早已黄昏,他思索着,这或许是他唯一牵挂的吧,可能就是他从小就看到祖父床下那只古朴的樟木箱子的缘故吧,箱子里的霁红梅瓶,还有那梅瓶旁的女子,让他不能自解,更使他难以入眠。他不知那女子姓甚,名谁,甚至不知她是否还活着,更不知道梅瓶和那女子曾在祖父的年华里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日复一日,看着祖父每况愈下的身体,他决定将这件事弄清楚,让祖父能够离去不留任何遗憾,但与祖父年纪相仿的老人都早已不在,因为父母早就离他而去,因此记忆中也未曾有父母的影子。他推断,那唯一的线索,就一定在那樟木箱子中。
于是,在祖父熟睡中,他偷偷地潜进房中,蹑手蹑脚地来到床下,童年中巨大的木箱现在不过尔尔,只是抱起来,仍如记忆中那般沉甸甸,坠在心里。他胆战心惊的看了一眼熟睡中的祖父,怯怯的打开箱子上的梅花锁,霁红梅瓶安详地躺在那里,依然那么静谧,只是那妖冶的红变得有些苍白,如同祖父的生命逐渐枯萎。旁边有几封陈旧而又疯狂的信,他迫不及待地拆开了第一封信,信中对祖父没有只言词组,只有一首《上邪》一点儿都看不懂,他满头雾水,接着他又拆开了后面的信封。一首首唯美的诗词看的他眼花缭乱,但没有失去耐心,拆开了最后一封信“念笙…”他感到非常的惊讶,这是他第一次,在信中看到祖父的名字:
“因为清王朝的腐败无能,军阀肆略纵横,东洋人来势汹汹,东三省,大上海已然失守,商贾富豪都被洗劫一空,死伤惨烈。同时,日本天皇下令山本村树誓要铲除中国的全部民族工业血洗大西南,而大西南的民族工业又集中于螳螂镇地区,你黄家乃是民族工业有头有脸的大家,他定要拿你家开刀,其余几家也难逃此劫
。我父亲与其他几大家族商定,举家南下,远渡台湾避难,莫不知你意下如何?我知道要你舍弃这里的一切很难,这毕竟是你一辈子的心血,可你若不走,到时候不仅仅是家业不保,甚至有可能惨遭灭门之灾,望你敬请三思。明晚三更,我于家中的后院十字巷的大槐树旁等你,你我约定,切莫失约。”
难道?他正思索着,难道祖父…… 他仔细再一看,发现信封里还有一张字条:
“君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
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
短短几行字,墨迹竟有晕染的痕迹,想必是早已被泪珠打湿。后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的心中不禁焦急难耐。看来,只有鼓起勇气去问祖父,才有可能拨开迷雾,水落石出。
想到这里,他马上想把祖父弄醒,但看着熟睡着的祖父,是如此睡得那么安详,他始终没有做出反应,看着年迈的祖父,他蹒跚步履的走了出去,关上祖父的卧室门 ,那黄昏的夕阳是多么的漂亮。过了不久,他始终坐立不安,同时祖父病情突然加重,看着祖父是那么的苍白,但还是要求他帮祖父打开箱子,他抱着梅瓶,很凝重的看着那张照片,我仿佛又听见祖父嘴里发出声音,但我就是没有听清楚。这让我更加确定,这里面一定有故事,他一定要询问清楚。他心惊胆战的问道祖父:“这女人是谁?和梅瓶有何关系?和你又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您老一辈子不能释怀。祖父那仿佛一潭死水的脸上突然有了表情,失神的双眼因激动而瞪得好大死死地盯住照片上的女子,两行浑浊的老泪滚滚而流:“眼波流转,巧笑倩兮!好一个翠城黎家!好一个黎家大小姐!好一个黎琬琳!好!好!好!”一连串的好字,仿佛耗尽了祖父的全身力气,声音因情绪的高亢而变得尖利,可怖。祖父瘫坐在藤椅上,身体不住地颤抖,为他专门制作的老藤椅咯吱、咯吱地惨叫着,为空闲中的寂静平添了几许凄凉。祖父指着照片,对那女子好似没有了一丝情感,满满的,只剩下无尽的怨恨。悠悠的,祖父沙哑的声音在空中纷飞弥漫着,静静地讲述着十八年前那未完成的故事。
“那时的我第一次见到她,心就被她偷走了。面对她,我一身的沉着和冷静都抛诸于九霄云外,取而代之的,则是对她无尽的相思之情。琳儿仅仅一个回眸,我便魂牵梦萦了一生。那时的我,是黄家的大公子,而她,则是富商黎家的大小姐。那场年会,我们的偶遇,至此,我满脑子都是她。得知了她的身份,我激动得不能自已。每一天,黎府的门房都会收到一束鲜花,署名黄念笙。她怎能置若罔闻?不出一周,便与我有了回应。不过她性格精灵的很,颇有读书人的气质,在信中从不提一句有关我们之间的事情,仅仅是一些古词、情诗。但落花有意,流水怎会无情?从她的诗中,我感受到她的心意,我们渐渐地把对方当做了唯一的彼此,并有意向其父亲提亲。
可好景不长,仅过了半载,由于东洋,沙俄,还有欧美等列强纷争不断,渐有蚕食我中华之意,尤其小日本直奔云南若到云南,必先夺取螳螂镇。他因联合那些爱国的有识之士,共同保家卫国,共同维护我中华的仅奄奄一息的名族工业。也就在这时,日本鬼子就要打过来了。早听闻北方关东失守,华北沦落,华中大上海岌岌可危,更可恨的是小鬼子征服了东南亚;一支军队将直插螳螂镇,第一任务就是摧毁民族工业。他们都劝我走,可他知道,自己好不容易才小有成就,怎敢做亡国奴?怎能做日本人的走狗!”说到这里,祖父剧烈地咳嗽了起来。他忙过去扶住祖父,轻打着祖父的背,轻柔着祖父的肩,祖父慢慢缓和了情绪,接着慢慢道来:“当时大西南八大名门,除了我黄家,竟都是见利忘义,吃里扒外的鼠辈,没有一家敢站出来和日本人火并,逃的逃,降的降。
婉琳的父亲也联合其他几大家,仓皇而逃,远渡台湾。就在日本军队进驻的前一晚,黎琬琳约我夜半三更相见,我如约而至,没想到,我们的匆匆见面,竟是一辈子的长诀。她见到我,就要我带她走,无论去哪儿,她都会为了我,她甘愿隐姓埋名,粗衣淡茶,远走他乡,只要换得太平日子。而我不能,在当时的局面下,我无法选择儿女情长,我不仅仅是我,我肩负着自己家族上百口人的责任,我不能决然抛下他们不顾,我不能欺骗我的初心。我告诉她,让她先走,等我处理完厂里这边的事,便去寻她,无论天涯海角,我都愿意和她在一起。可她那天竟是如此任性,完全失了平日的端庄、矜持,那样苦苦地哀求我带她走。但我没有,我们僵持到天蒙蒙亮,她眼见无果,便将脚下的包裹塞到我的怀里,幽怨地看了我一眼,顿时,早已藏在眼角的泪还是摔下来,那啜泣的声音,砸的我心好痛。渐渐地,她转身就走,头也不回的慢慢的消失在黎明中,她每一步都那么哀愁,彳亍在那狭长的巷,竟没有在看我一眼。残存的夜色吞没了她的身影,我半分都寻不得!只有紧紧抱着那包裹,失魂般地踱回自己家中。打开包裹,也正是这梅瓶和她的照片。看着它们,心里有种莫名的伤痛。我找来母亲陪嫁的樟木箱子,连同她给我的信封在一起,埋入隔壁向阳街槐树旁边的老宅中。
她走了,竟是如此干脆!
走后的一个月,这里果然沦陷。我仓促地带着家人向西边逃亡,一路上数次遇到追兵,差点就失了性命。当我和剩下的人躲在山中月余后,听闻局势渐有太平之意,才敢逃出山林。稍作整顿,我便欲去寻她,不料听闻,我听闻她原来竟成了日本大佐山本的妻 … … 可我怎会去相信,她不是走了吗?国仇家恨,叫我怎能忘了她!黎家大小姐真真待我不薄啊!自此杳无音讯。”祖父说到这,几欲昏厥。原来事情竟是这样!怪不得祖父从未提起,即便是几十年后,颠沛流离一生的祖父,心中的痛意未减半分。看着风烛残年的老人,他的心,渐渐地沉寂下去。
或许是年迈的祖父过于激动,或许是祖父真的老了。在他听完这个故事后,没有几周,祖父便去了。深秋时节,残阳如血,斑驳的日光洒在老藤椅上,洒在祖父熟睡的脸上,竟是那样安详,饱经沧桑的脸犹如一片秋叶,脉络分明却又失去生命的光泽,没有任何征兆,祖父就在很普通的一个下午,与世长辞。他忍住心中的痛,整理着祖父的遗物。除了那几件简单的衣物,就是那伴随祖父一生的樟木箱子。他知道,祖父最后,也没能放下那女子,还在嘴里喊着黎婉琳的名字。于是,他操办好祖父的后事,带着梅瓶,带着那仅有的线索,乘着轮船,朝着台湾,朝着黎家而去。
漂洋过海半月有余,他终于来到了台湾。
简单地收拾一番,找了一家看起来还算干净的旅店住下。第二日一大清早,他便找到老板,询问黎家的下落。可从老板口中,他得知黎家早就不复存在了,不知为何,黎家得罪了日本人,除了少数在外的黎家人没有回来,其余的,全在那场大火中失去了性命。他不禁愣住了:黎家没了,线索断了,祖父的遗志,恐怕真的是遗憾了。他怔怔地问老板:“黎家剩余的人呢?他们在哪?”老板说过去这么多年了,好像因为黎婉琳假借嫁山本,暗中杀了日本人,所以遭到了日本人的通缉令,死的死,伤的伤。要不是他提起,谁还记得黎家啊?就算有幸存下来的,也早已下落不明,隐姓埋名。
无奈之下,他道谢了老板,带着梅瓶,回到了螳螂镇,回到那和祖父相依为命的老宅。而那妖冶的梅瓶,被他安放在樟木箱子内,扣紧了梅花锁,依然尘封于祖父的床下,未曾再动一次。但心中的疑问,并未随时光的蹉跎而淡然,反而成为他心中的一个结,一个令他铭记一生的结。
多年后,他也有了自己的家庭,成了祖父。在一个充满阳光的下午,品着茶,依然伴着老藤椅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渐渐入眠。在这熟悉的声音里,他仿佛看到祖父在寻找着什么,又什么都没看到。冥冥中,仿佛有一股力量在牵引着他,来到那布满灰尘的樟木箱子前。他费力地拖出它,打开锈迹斑驳的梅花锁,那抹妖冶的红跳动着。看着那淡黄淡黄的梅瓶,他一瞬间愤怒了!他不知这一生为何守着它,祖父的一生为何要守着她!
终于,愤怒战胜了一切,他举起梅瓶,朝着地上砸去。哐当一声,散落一地的红瓷中,一个小小的布包洒落了出来,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慢慢弯下那枯瘦的身躯,拆开来看,竟是一封早已青黄的信。他抖抖飕飕的展开书信,令他纠结一生的谜团终于揭开:
“念笙,若你执意不肯走,我也无法,只是这一役,恐你凶多吉少,父亲已答应山本的求亲,但我宁死不从。你走后,我定去寻你,待我杀了山本,为你,为我们的幸福,为了更多的人,我要报此深仇!想我一生,竟是爱别离,求不得啊!只愿你我来生,莫再有缘无份,镜花水月般无果!琬琳绝笔。”
看过此信,他无力地滑坐在地上,怔怔地望着那一地妖冶的红瓷,失神的双眼滚落着两行热泪,砸在那张泛黄的老照片上,砸在那巧笑倩兮的芳容上,砸的心好疼。嘴里不住地呼唤着祖父的名字,一声一声,字字铿锵。原来你这一生,终究是错了啊!
自此,令他疑惑一生的谜团解开,这个困惑让祖父含恨而终,让自己自记事以来就一直想知道真相,原来自己解开了谜底,他却不知所措,他感觉祖父似乎就在他身旁,露出了微笑。此后几日,他每天黄昏时分,他依然靠在曾经祖父发出咯吱咯吱的老藤椅子,仿佛在诉说着什么?又仿佛在挣扎着什么?就这样,夜深了,皎洁的月光照在他满脸的皱纹和花白的头发上,是那么的安详,他微微的闭上了双眼,渐渐地露出了一丝笑容,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拿着钥匙,来到祖宅起初的老地方,老槐树旁的老屋里。打开门,青苔满布,砖墙斑驳,一切竟不复当年。唯有那扇天窗洒下融融的日光,洒在满地的红瓷上,熠熠生辉。清风掠过,古老的藤椅吱呀吱呀,仿佛静静地讲述着一切。同样的深秋,漫天落叶纷零,火红火红的,分不清是残阳,是落叶,还是那妖冶的霁红梅瓶。
嘘,别问谁是谁的谁。
遇见,别问是劫是缘。
相知,恨别泪两行。
再回首流年空空,待回首碎梦重重;
终老亦犹未悔,怎赐霁红梅瓶满目疮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