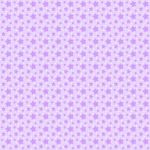筑波君
爷爷说,他年轻的时候,家乡东北正被日本人占领,在朝鲜族推行“皇民化”。接着,讲述了埋藏近一生的思念。

一天早上,我们到药店不久,做营业前的准备。突然接到消息,日本人要来这选几批人,进行“皇民化”训练。大家立刻呆住了,心里慌慌的,谁也不知道训练内容,是否涉及生命安全;谁也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选中。沉寂的气氛,没有了往日的问候或笑声。一个年长的店员也许为了缓解大家的情绪,开起了玩笑,让大家猜猜谁能被选中。他也许是也受了惊吓,这哪是玩笑,分明加重了大家的紧张。
我心慌到极点,双腿发软,仿佛一阵风就能吹倒;手里的笔已经握不住了,心里一直在祷念,“别选我,别选我。”
但这个玩笑引起了反应,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到我身上。那时大家都已换了店服,,只有我还没来得及换,西装革履的,非常扎眼。
突然,门外匆匆跑来一个人,是店里的小张,他边跑边说,“来了,来了”。接着,走进一老一少两个穿着军服的日本军人,环视着四周的人们。我微低着头,瞄着他们,心里还在不停地祷念着,“别选我,别选我。”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那个年轻军人几乎没有犹豫,就走到我跟前。他个子比我略矮一点,看清了他的脸,和我一样,一脸书卷气,眉目清秀,面部却紧绷着,但没有那种凶神恶煞的神情。
“你,去吧。”他说着流利的汉语,尽管声音不大,还有几分轻柔,但却犹如炸弹,爆破了我的大脑,没了思维。
接着,一道寒光闪过,一把带有木纹的刺刀横在我的喉头,但那刀刃却不见光泽,暗黄的,好像还有几处卷刃。
“别怕。”他大概是看到了我惨白的脸色和额头的汗珠,也好像知道我看到了那道光。“能见到刀刃的光芒,那是一种荣幸,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的;死在那刀下,也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的,那是一种神圣和荣誉。”
他在我耳边轻缓地说,我身躯却正坠入深渊,周围模模糊糊的,只隐约看到传信的小张在分发纸片。接下来的记忆断层了,一丝印象也没有。
醒来时,我正俯身走在木制的阶梯上。
阶梯两旁是木制的扶栏,再两边是葱绿的灌木丛,听到茂密的枝叶下流动的水声。我清醒了,自己正走在山间的道路上,一把戒尺或长剑一样的东西,从后背延伸过头顶,连同我的双臂一起被倒绑,这样上山,只能是弯着身子。
“他们在前面很远了,只有你,不,我们俩落后了。”一个声音传来,陌生又熟悉,看着眼前的军靴,我想起来了,一定是他,那个年轻的日本军人。
“我们去见佐木少将。”我无心听这些,只是在默声地咒骂。
“你头抬不起来,一定觉得很耻辱。我也有过这个感受,能有今天,就是从这耻辱中过来的。”
我默不做声,仍在心里咒骂。
“你有今天的耻辱,就会有明天的荣耀。” 我不想回应他,一步一阶艰难地俯行。
“你可以说点什么?”
突然,我感觉背后被什么压住了,挪不动步子,接着被一双手扶起。我的头“嗡”的一下,血液往上涌,渐渐缓过神来,眼前一片明亮,后背直挺挺地靠在扶栏上。
“你累了,可以歇一下。”
然后,我们俩对视着。
他看着我,我看着他。我怎么也想不到,一个面貌稚嫩的同龄人,竟是一个野蛮的日本兵。
他清秀的脸庞变得松软,没有初见时的僵硬;嘴角有一丝抽动,仿佛要说什么又说不出来;眼睛流露的目光,像一双温柔的手,在抚摸着我的全身。这是什么感觉,我自己都诧异了。他猛地转过身,从衣兜里掏出手帕,擦了擦脸。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转回身。
“我叫筑波。你像我的弟弟。”他顿了顿,“哦,这些——,没办法。”我不完全理解他的“没办法”的意思,一声不吭。
“我故意选中你。如果我不选,你也会被别人选中,因为第一批受训的有要求很严,你哪方面都合适。”他仍轻缓地说。“我能做的,就是单独押你。你就是身体太差了。也好,正如我意,落在别人后面,我们可以……”他好像感觉到冒失或失言,便戛然而止。
“他们大概已经到了,也许在等我俩,你不想说点什么么?”
我不知说什么才好,只好说,“你想让我说什么?”
说完,便转身前行,他跟在后面。
“你的经历,家庭,学校。”
“我国高毕业,本应继续读书,你们来了,就开始了工作,今天在药店上班正好一百天。”
“你懂中医?!”
“懂一点,姥爷教的。”
“那太好了。”他似乎忘记了他的身份,激动地说。“我到你们药店时,就想问,有几副药一般药店没有,可能是不愿卖给我。”
“我弟弟的病一直没好,听说这个药方不错。”说着,他从衣裳兜里掏出纸片,放在我眼前。
“我不是一个强盗,你能帮助我的话……”
见我停下步伐,他扶我站住。也许我的善意出卖了我,他说,“谢谢了。”说完,鞠个躬,把药方单放到我上衣口袋里。
突然,我口袋里的什么东西引起了他的注意,脸色立刻大变,恼怒起来,大叫道,“混蛋,你把圣谕弄脏了。”
我看清了,这是小张发给受训人的表格,每人两张。每张都是“目”字表格,中间两条横线是手工画上的。顶格印好了字,就是筑波所说的“圣谕”,下面是空白的格子。有张纸被汗水浸湿了一角,恰巧是所谓的“圣谕”部分。
“别的地方还好,这地方脏了怎么办啊?”他仍在愤怒。
我转身上路,他在大声地喘气,一路沉默。
不久,到了一个山坡,走进一个宽敞的、四周玻璃的木屋。果然,大家已经到了,正在等候受训。
筑波不知去了哪儿了,一会气喘吁吁地来到屋子,拿出什么东西,处理我那张纸上的污渍,一会放下,一会拿起,表情渐渐轻松起来。这时,从大厅里面的过道门匆匆走出一个面色苍白的中年女人。我认识,她是我姐姐的同学,姓董,日语好,早听说被请人走了。
“表格都画线了么?” 她对筑波说。
“不用画。”
“要画的。”
“不用画。”
“要求画啊。”
“没关系,有我呢。”
这时,有人从过道门里出来,开门的瞬间内面传来有人议论画线的声音。
董大姐的汗水已经下来了,筑波也明白了,说,“别急,我来。”于是,他把我那两张表格对齐,画直线、对角线,以连成一个表格。由于两个“目”字中间手画的横线间隔不一,他画的直线有的成了斜线,对角线有的成了弧线。董大姐在一旁惊呀,我们受训人则不知道这么做的目的和用途,只是漠然地看着。最后,他涂涂抹抹地把我们这批受训人的表格连完了。
轮到我们受训了。筑波和董大姐走进了过道小门。
我们忐忑地等等待着。突然,里面传出一阵暴怒声,接着是什么物体碰撞跌倒的声音。不一会儿,看见筑波被人从里面搀扶出来,用毛巾捂着的额头不停地渗血。
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们没有受训,回到了药店,回到了家。
事后,听说董大姐说,筑波被佐木训斥了,还挨了打,具体原因她也不知道,也无法打听,可能与表格有关。
中药买好了。我想起了筑波,甚至说有点思念。董大姐捎来的口信说药是捎不进去的,只能筑波来取,可是他一直没出现。
不知怎地,我见筑波心情迫切起来,哪怕见不到他也想去一趟那个山坡。于是,去求助董大姐。她说她也不知道筑波哪天回来,甚至能不能回来,去那儿不仅白费心思,风险也大。在不断的央求下,我们终于成行了。那天,经过几道路卡的盘查搜身,我来到了那个木屋。
一个接待我的矮个子年轻女子告诉我,筑波先生还没来,至于什么时候来,她也不清楚,并谢绝了我在这儿等候一会儿的想法。我失望之极,仿佛又跌入深谷之中。
就在我失望地转身退出的时候,和一个刚进门的人撞个满怀。啊,是筑波,头上还缠着绷带。我们呆立着对望一下,便情不自禁地拥抱一起。接着,他把我带进一个狭小的会客室。原来,这是他第一天上班。我想,真是天助我也。
我告诉他,药买了,带不来。他用异样的目光盯着我,说,“我代表弟弟,谢谢你”。说完鞠个躬,抬起头来,望着我,迟疑了一下,说,“其实他不全是我弟弟,也是我恋人。”
说着,他把我推倒在榻榻米上,压在我身上,用双手捧着我的头,我们吻在一起。那是我的初吻。
回到家,我一直等筑波来取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还没来取。
爷爷混浊的眼睛湿润了,闪着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