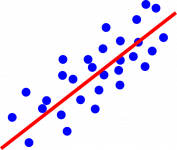日暮西头
编辑荐:无边无际的草,蔓延至天边,与残存的一丝晚霞融合在一起,给人一种神圣有诡谲的感觉,我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兴奋与悲伤的交加。

日暮西头,太阳的余晖照射在进入生命晚期的墨绿叶子上。不一会儿,所有的光芒都散去,黑夜如期而至。
连续几周,我废寝忘食,不断的增添删改,终于将几年前搁置的小说修补完毕。是有关于社会冷漠与温暖的,相信此书一发表,定能给这个冷漠的社会一丝暖意,然后掀起轩然大波,到那时我就不愁不出名了,各种签约与金钱都会自己找上门来。想到以后的辉煌日子,嘴角忍不住上扬。
得意的端起桌上的茶杯,茶已凉了好一会,茶叶被泡过久,茶已成了浓茶。慢慢踱步到窗前,才惊觉夜幕已降临,身后昏暗的光线竟是没能打扰到奋笔疾书的我。讶异了许久,才想到许是自己太专注了,连开灯都忘了。
端着茶杯走下楼,老妈正拿着遥控器换频道,老爸不在,许是到外边乘凉了。我的突然出现,显然吓了老妈一跳,好像我从没有在这个家出现过一样。看了我半晌,扭头看电视时才说了一句“饭在锅里。”我点点头表示知道了,眼睛下意识地往厨房与卫生间搜寻,总觉得缺少了什么。这种感觉真不好受,像是不断给我输送新鲜血液的心脏控制着我,而不是大脑皮层。
端坐在沙发上,就像刚进行了一场大脑极限训练的我终于意识到,老弟去外婆家大概两个月了吧,一直没见回家,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明天二外婆生日庆宴,你去不去?”老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但似乎对她来说这个问题也没必要问,因为她觉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嗯,去吧。”想想也没什么事,便答应了。只见老妈不可置信的看了我一眼,我回了她一个坚定的眼神。
说来奇怪,世界对我来说有种扭曲感,但又说不出是什么感觉,觉得老妈的眼神不对,周围的光线不对,就连墙角的蜘蛛网也不对。弟弟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有回家了,但大家却感觉很正常,一切都很正常。看来明天我得亲自去看看。
如往年,宴会很热闹,大家平时没机会聚在一起,便趁这个机会好好聚聚。但我盼望了好久的身影却是没有出现。
“嘭”,喧闹声从那边传来,我随着大家跑过去,原来是七叔摔倒了,他的轮椅本就破旧不堪了,又因为他喝了几杯酒,上身重心乱晃,轮椅招架不住,朝一边倒去。
他不应该喝那么多酒,我这么想着。
人群中也有相同的看法,议论纷纷。
他的轮椅太烂了。
他应该注意自己的身体。他应该用右手支撑着站起来,左手被压住了。
我不能扶他起来了,该打电话叫他儿子来。
虽然我们是亲戚,但社会上总是有太多的善心被辜负,自己还是提防些吧。
大家听到这话纷纷点了头,就连刚刚与七叔饮得正欢的二舅听到大家的话也默默走到围观的人群中。我们很自觉的有秩序的围成了一个圆,看着侧坐在地上的七叔,用右手颤抖着扶起倒在他旁边的轮椅,但因为轮子总是在快成功的时候又滑向另一边,他显然变得急躁,周围的人也为他焦急,说:“加油啊,要成功了。”七叔便对着周围的人却笑笑,又开始努力的尝试。
我有点无语,大家一起去帮他不就行了吗,干嘛让他一个人那么辛苦,社会真是太冷漠了。
过了许久我看到场上出现了一个陌生人,一身笔直的黑西装,脸在帽檐下,看不真切。但我的预感告诉我,他定与弟弟的失踪有关。果然!他的身后跟着的就是弟弟!
弟弟外貌没什么变化,只是脸上没有了往时天真的神情,他拨开人群,走到七叔脚边,见他作势要帮七叔抬起轮椅,我大喊:“别啊,小心有诈。”只见大家把奇怪与责备的神情看着我,好像我说的是非常不对的话语。
弟弟把轮椅抬起后,又扶起了七叔,七叔激动地拉着他的手不断地说谢谢,人群又议论纷纷:果然是个好孩子,一点都不像他姐姐。社会就应该多需要这样的人,这样才能让世界更美好。现在的人啊,一点点善良被辜负了,就不该再付出了,这是问题根源啊。
我可不管这么多,与他们评论社会问题就像大鹏与学鸠为伍,一把拉过弟弟,“这两个月你都去哪了,我都担心死了,你没出什么事吧?”
“姐,我没事,你不用担心我,我只是去了我该去的地方。”他很平静的说。
一听这话我就来气,责备着他:“什么叫你该去的地方,家不是你该去的地方吗?你这样会让家里人很担心的。对了,你这几个月呆在哪啊,是不是什么医院之类的?”突然想到之前新闻报导孩子失踪被找回后到医院检查发现肾不见了之类的事件,心中有些害怕。
“没有,姐,我真的没什么事,你看,这是我的身份证。”
“身份证,你是在逗我吗,你一个小孩子哪有什么身份证!”我拿过来一看,粉红色的!而且上面还是爸爸的名字!我总觉得这世界就要疯了,乱套了。
“姐,如果你是为我好,就不要担心我,我不会有什么危险的,只是爸爸说我不在这,去那里才是最好的选择,看到那个黑衣人吗?等下我要跟他一起走。”
我没想到小学三年级的他居然会说出那么多不符合他年龄的话,看他作势要转身,震惊之余,我紧紧抓住了他的手。拼命喊着“老爸,快拦着弟弟,他又要离开家了。”而弟弟拼命的想挣脱我的手,旁边的黑衣人显然不知所措。
赶来的爸爸分开了我们的手,看着不依不挠的我,对黑衣人摇了摇头,叹了一口气,说:“唉,我去吧。”便带着我和弟弟离开了。爸爸跟我说我跟妈妈坐小电动车,他和弟弟一车。直觉告诉我他想甩掉我,所以无论他怎么说我都不答应,况且他的车明明就很大,可以容得下好几人,不必再坐妈妈的电动车。劝不动我,爸爸只能带上我。
到了村口,有一妇女在等车,看着她两腿叉开的站,应该是怀孕了。我见她老远就开始招呼着我们。车开到她跟前停下了,她说要去镇上,请求搭一下我们的顺风车。爸爸停下,我扶着她上车,可是还没坐定。爸爸就开始踩油门加大速度,惹得我和那妇人都一声惊呼。
深觉老爸做得过分,便对他吼道“老爸,我们都没坐稳呢!你就不能别那么急吗!而且车上有孕妇,你能不能开慢点!”他却默不作声,好像没有听到我的话一样,专心致志的开着自己的车,也没有因此把车开得慢些。
我的心中有些恐慌,觉得眼前这个冷冷的,毫无生气如木头般的男人根本不是我的父亲。
到了镇上,天已经黑了,大多数的商店都已经关门,只有王福饭馆还开着灯。我们四人走进饭馆,点了几个菜,爸爸说他去外面等着上菜,要我先付钱。我点头说:好的。便站在柜台边等着服务员算账。可帐都没算完,便听到外面发动机开火的声音,心中暗叫,完了。不管身后服务员的喊叫,飞快的跑出了餐馆。
是的,千钧一发之际我还是跳上了车,只是可怜了那妇女,没到达目的地,看来她要步行好一段路了,坐在车上的我看着她的身影与饭馆消失在黑夜之中。爸爸突然发动发动机分明要甩掉我,他回头看着我,我对上他那无奈的眼神,耸了耸肩,把弟弟抱在怀中。
车子又原路返回了,只是在过山洞时拐了一个方向,开往山脚。疾驶在崎岖的小路上,因为路的坑坑洼洼,车子不断地尖声呻吟,我也觉得自己要散架了。
看着周围不断变化的景象,似曾相识,参天大树枝繁叶茂,密密麻麻的遮住了月光。车子与地上石块的碰撞声惊起树上鸽子,咕咕咕的乱叫。进入这个地方,才知道它比从公路上看进来要幽深的多。即使车子很吵,我觉得我还是听到了周围的蛇吐着红信子的声音。回头看来时的路,那些路好像消失了,这里只是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
“你看,那是什么,把你看到的告诉我。”老爸突然说话,把我吓了一跳。看向他手指指的方向,只有黑黑的一大片树,但我知道老爸问我这个问题一定会有他的用意。他不可能把弟弟带到这么一个了无人烟的地方,难道这其中有什么秘密吗。我集中精神看着那个地方,希望能看出个所以然,可是依然没什么变化。
当我准备放弃时,奇异的事就发生了!在远处,一幅画面,无数根电线杆竖立在田野上,在夕阳的照耀下闪着淡黄色的光,而它们周围的草,鲜嫩又肥美,一看就知道很久没人打理过了。我定定的看着它们,记忆匣子像被打开了一样,一幅幅画面拂过脑海,我看到也是这个地方,不过是日落时分,画面中农民们挥动着镰刀割小麦,一些人堆起,一些人扎好,一些人一捆捆的放上牛车,他们开心地笑着,拉着牛归去,迎着夕阳唱着歌。看得我的心里暖暖的。
伴着那歌声,我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我出现在半山腰上,山下的军队在嘶吼着,战斗非常的激烈,山下的士兵看见了我,便招呼着大家跑上山,还放开手中的一匹匹黑狼,看着疾驶在后的黑狼,我慌不择路,只管往丛林深处跑去,之后就什么事都不记得了,应该是落下了山崖,因为在记忆中有人拿着火把在寻我。不知为何,被温暖的心心一下子充满了寒冷,我觉得世界不应该还是这个样子。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记忆,而他们好像已经被封锁在我的脑子里的某个角落。感受到老爸在我背上拍了几下,我回过神来,仔细想那些农民所唱的歌,不由自主的唱了起来“蒙德拉斯的草原真辽阔,连绵的雪山在我心,心中常想那不归路呀,来世能否寻得见。”爸爸诧异的看着我,完全没有想到我会唱出这个歌,难道这个歌是是什么密码吗。
周围突然变得很湿,像是升起了大雾,打湿了车身,打湿了衣服和头发,我的意识回来了,我们处在了闹市区,周围的人来来往往,很是热闹。经过几个学校,一大波学生从里面涌出,应该是放学期间,而教学楼的墙上,镶嵌着“物校”两个大字,大脑自动翻译着,物校就是专门教物理的学校,也不知道大脑何时有种种功能。看着周围纷繁复杂的事物,脑子乱乱的,很想知道到发生了什么,这里是什么地方。为何我们可以从黑夜的树林中穿过就可以到达白昼的城市里呢,我在树林中看到的那些到底是什么。我问老爸,他却默不作声,依然不回答我的问题。
经过一个小阁楼的时候,老爸却自顾自的在那里说“上伯被刺杀的事我还是不能忘记,到底是何人竟如此心狠手辣。”上伯是这里的一个高级官员,大脑又自动翻译,盯着小阁楼敞开的窗口,上伯被刺眼睛的血腥场面重现在我的脑海里。
车子开到了郊外,在一条小河旁,爸爸在终于停下了开得飞快的车,他转过身,看着我和弟弟,幽幽的说:“一个是温暖与残酷并存的世界,一个是安全但冷漠的世界,你们会选哪一个?”对于爸爸的这个问题,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但又很想跟他说他那样对待那个妇女,他就是冷漠的的人,冷漠不是别人体现出来的,还有我们本身!我咬咬嘴唇,终究没有说出口。看着弟弟,他说得对,我应该让弟弟留在这个地方。
车又开始发动,朝着离城市更远的地方行进,爸爸说那里更容易成为好人。一直开到四周长满草的地方,草高到盖过了车身,在很远的地方,连绵的雪山在阳光下闪着尖尖的头,我从车上站起,茫然的看着这一切。
无边无际的草,蔓延至天边,与残存的一丝晚霞融合在一起,给人一种神圣有诡谲的感觉,我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兴奋与悲伤的交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