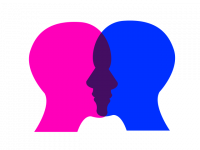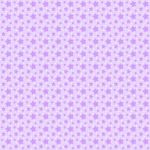爸爸,你去哪了
——谨以此文纪念几年前在工地上意外死亡的河南工友。并向所有的农民工以及留守儿童、留守老人致敬!

天很好,没有一丝云彩,就像人的心里没了烦恼一样,显得格外高远、空阔;冬天的阳光并不热烈,但在雪后初晴的早上,却能给人以可贵的温暖;山脚下唯一一条简易公路宛如坚硬地巨蟒,顺着窄溜溜地山溪曲折蜿蜒至山外。
海燕坐在半山腰自家的屋檐下,捧着一本书,边翻边晒太阳。一只黑色翻毛老母鸡“咯咯咯”地伸缩着脖子,在不远处觅食,将草垛边一坨尚未化尽的积雪扒拉的四处飞溅。十几只小鸡仔抖抖缩缩的围着它打转,像一只只滚动的小绒球。海燕合上书,眯眼呆望着这群小精灵,想像着自己也变成了小鸡仔中的一员,正幸福的跟在鸡妈妈的身旁,一股暖流就慢慢地在体内蔓延开来。
“咳咳咳……咳咳咳……”
爷爷在床上咳得地动山摇。他气喘加咳嗽的老毛病又犯了,嗓子眼里像安了簧片,听来刺耳且让人揪心。海燕已经有了经验,早早的就在爷爷床边放了一只破火钵,里面盛了半钵草灰,给爷爷当痰盂。爷爷痰多,一口一口像脓一样,需要她隔不几天就得换一次草灰。
爷爷死犟死犟,任她怎样劝,都不肯动用爸爸寄回来的那些钱,去山外的医院看病;却不知从哪里讨来了偏方,自己照着方子上山寻了些草药,未入冬就喝。几年下来,病不但不见任何起色,反而有了加重的迹象。爷爷以他七十三年的人生经验对自己的顽固作了解释,爷爷说:“你爸难呢。我已然是黄土埋了大半截的人了,怎么能不知轻重,乱花子孙钱呢?你又不是不清楚,小丽她奶奶花了那么多冤枉钱,最后还不是人财两空。哎,谁叫咱是农民呢?熬吧……”
海燕听了就很难过,不知爷爷的话在不在理。不过有一点她很清楚,正如爷爷说的那样,爸爸在外挣钱的确不易。也是的,从农村走出去的人,有几个是能够轻轻松松就能挣到钱的呢?为了省下路费,已经四年了,爸爸都没回过一次家。俗话说:金窝银窝,抵不上自家的草窝。家对一个人而言,意义是多么重大啊!特别是过年的时候,如果不是因为什么特殊原因,谁愿意忍受思念亲人的煎熬,忍受身在异乡的孤独,而不在这重要时刻与家人团聚呢?海燕理解爸爸的难处,从没有埋怨过爸爸。家乡还有句俗话:猫生儿猫疼,狗生儿狗疼,叫花子生儿边走边疼。这是对父爱母爱多么形象的诠释啊!爸爸难道不懂吗?
爸爸肯定懂的。可有什么法子想呢?家里的房子还是爷爷年轻时盖的,泥坯草顶,一下雨,屋檐就往下滴“酱油”,连冬天结的冰溜子也是酱色的。朝阳的墙壁上,被野蜂打出了密密麻麻的大窟小眼。整座房子看上去,简直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民居的活化石。如果不是几根碗口粗的柱子斜撑着,估计早就散架了。为了盖一座像样的新房子,爸爸必须外出打工,至于几亩薄产的责任田,也只能丢给爷爷“责任”了。
海燕以与她年龄不大相称的成熟面对着生活,对爸爸与爷爷的艰难深有感触,就懂事的挤出学习空余时间帮衬爷爷一把。除了生火做饭、浆洗衣物之类的家务活,在农忙季节,她会跟爷爷一道下田,像个大人一样弯腰直背的插秧,割稻。春去秋来,太阳晒黑了她的小脸蛋,镰刀、锄头之类的农具将她的小手磨出了老茧。她已经把自己锻炼成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小农民了。这似乎很残忍,又似乎好呢合理。可她毕竟只是个才十三岁的小女孩啊!这样的年纪,若在城里,可正是在父母跟前撒娇,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无忧无虑的小公主啊。海燕没有撒娇的对象,只能在夜深人静时,缩在被窝里紧紧搂着一只枕头,默默流泪……
“海燕,药煨好了没?我好像闻着前气味了”
爷爷咳了几声,喊她。
“诶,我来看看。”
海燕将书放在小竹椅上,辫子一甩,闪身进了灶屋。一股难闻的药味在空气中弥漫。她用一块湿抹布裹住陶罐,将它从灶膛里拖了出来。又拽把稻草掸去沾在罐身的草灰,小心翼翼地捧到爷爷床前。爷爷披着一件破棉袄,斜靠在床头。爷爷脸色蜡黄,白头发蓬乱如荒草,两只手软软地搭在被子上,目光浑浊,像一只刚刚挨了主人毒打的。可怜巴巴的老狗。海燕拿快布揩去了爷爷胡子上的涎痰,滗了碗药喂他。爷爷摆了摆手,意思是不用她喂,自己喝。
爷爷喝了口药,问:“你爸爸,你爸爸今年过年肯定回来?”
“嗯……”提到爸爸,海燕脸上闪过一丝喜悦的神色,说:“信上是这么讲的。再过两天,大概就能回了”
“回来好,回来好……过了年,你也跟你爸爸走,到他那里去念书……”爷爷边说边抬头,朝房顶望了望,“跟我一样,撑不了几天喽!连江大嘴家茅房都不如,哎……”
“人家是干部,儿子又在城里开店,日子哪能不好……我爸爸信上讲了,这次回来,把房子修一修。”
“修一修?”爷爷有些警觉,耷拉的眼皮向上抬了抬,问:“你爸爸没讲重盖?”
“没。”
“哎!在外苦了几年了,也还……”爷爷有些无奈的摇了摇头。
海燕的情绪也突然低落下来。是啊,爸爸当年下决心外出打工,最大的心愿不就是回家盖三间敞亮的打瓦房吗?可现在,从爸爸的信里只提到把房子修一修可以看出来,这几年,爸爸在外并没有当初预想的那样顺利,大概也没存上多少钱,至少是没存够盖三间大瓦房的钱。
海燕记得很清楚,爸爸临走的那年年三十,买了张红纸请村子里的退休会计金跛子帮忙写对联,金跛子并没有在他那本研究卷起边角的历书上选现成的,而是结合她家的实际情况,给现编了一幅。那副古怪的对联贴上大门后,引得村子里的一帮顽童站在她家门外齐刷刷的喊:
“行客请注意,留下墙要倒。行客请注意,留心墙要倒……”
那时的海燕虽小,自尊心却一点也不小。她拿眼恶狠狠地剜比她大的那帮顽童,甚至摸出灶台上的菜刀相向,吓得那帮小子一哄而散。大年初四的晚上,她偷偷把那副对联抠了下来,扔了。
她还记得那年三十晚上吃年饭时,平时很少喝酒的爸爸将一大杯白酒猛地倒进嘴里,好像担心有人跟他抢似的,然后将杯子往桌子上重重一蹾,目光异常坚定,自言自语地说:“田是不能再做了。不管怎样,到外面苦干几年,就算把命搭上,也要把房子盖起来,我就不信了……”
那年正月十五一过,爸爸就扛起一蛇皮袋行李,跟村子里的单身汉小猴子走了。
四年过去了,小猴子回过一次家,还带回来爸爸给她买的新衣服。爸爸不知道她已经长高了,买的衣服不合身。她一点也不怪爸爸粗心。穿上那套新衣,原地转了一圈又一圈,脸上绽开了笑容,幸福的有些晕头转向。
爸爸人虽然没回来,却时常寄些钱回家。既当她学费,也当她和爷爷的生活开支。当然,每次寄的数额都不大,为此,海燕没少受委屈。
邮递员一般都是吧信件、报纸之类的的东西送到村部便算完事。江大嘴家就在海燕她们队,就顺便把汇款单捎给她。江大嘴经常在给她汇款单时不屑地埋怨几句:
“这个树根也真是,每回都三百两百的,还不够一顿饭的钱。就不能一次性多寄点?小气吧啦的,烦死人了。天生就不是干大事的料……”
海燕听了就好很难过,却无话可说,只在心里想:不愧是干部,讲话都那么有气势。
海燕命苦。像村子里瘪嘴豁腮的无奶奶说的那样,比山的黄连还苦。
三岁时,妈妈抛下她,走了。妈妈没留下任何影像资料。在她心里,妈妈只是个抽象的符号而已。她只能凭借自己的想象,凭借自己对“妈妈”————这个世界上最温馨的字眼的理解,在夜深人静时,伴着咸涩的泪水,在心里拼凑一幅妈妈的形象。
妈妈得了尿毒症。这对于一个生活上早已经捉襟见肘的农村家庭而言,意味着已经收到了死刑判决书,根本没有转圜的余地。如果生命的延续非得靠金钱来维系、来决定的话,那么,在将所有的积蓄以及借来的钱花光,但于巨额的医疗费而言只不过是杯水车薪的情形下,除了把病人拉回家等待奇迹发生外,还有别的办法吗?
奇迹很难发生。妈妈丢下尚未记事的海燕,一个人走了,长眠于对面山坡的半山腰,化为一座野草丛生的孤坟,与这个风雨飘摇的家隔着一条小山沟相互守望。海燕那时小,整天哭着闹着要妈妈。爸爸想尽办法哄她,哄不歇。这个对生活也几乎完全失了信心的男人,索性蹲在地上,双手抱着头,像一头老黄牛似的哞嚎起来。海燕惊恐地望着爸爸,听不出爸爸的哭声里有着怎样的意味。
时光不会因为某个人的悲伤与不幸而停止前行。磕磕绊绊中,海燕一天天大了起来。她已经不再整天哭着闹着要妈妈了,而是将妈妈深深地珍藏在心底,不去触碰。时间似乎治愈了她心灵的伤口,看上去,她好像已经习惯了没有妈妈的生活。只是心中对母爱的那种与生俱来的渴望,仿佛一只毒蝎子,会利用某个契机偷偷溜出来,狠狠地蜇她一口。
那次,她跟隔壁的小丽玩,跌了一跤,很疼,但她爬了起来,若无其事的继续游戏。小丽也跌了一跤,就赖在地上不动,哭着喊妈妈。小丽的妈妈应声而出,慌忙之间连粘在手上的白面也来不及清洗,一把将小丽搂在怀里,心肝宝贝的哄她。海燕呆站在一旁,怔怔的看着小丽在她妈妈怀里尽情撒娇,既羡慕,有妒忌。突然地,她感觉刚刚摔的地方也疼了起来,就悻悻地回了家。爷爷跟爸爸都下地干活去了,孤零零的她倍感无助。她的小嘴瘪瘪歪歪,瘪出了心里珍藏已久的两个字:妈————妈!就一头扑倒在床上,拿被子蒙住头,低声抽泣起来。
“燕,你怎么又发呆?快,把那只小布袋拿过来。”爷爷又咳喘了几下,指了指墙角的一只木箱。
海燕停止了发呆,走到箱子前,揭开盖子,在箱子拐角底部摸出一只红布袋子。
“你数数。我记得总共是九百二十六块钱。你再数数……”
海燕按一的吩咐,将布袋里一卷面额大小不等,成筒状的纸币倒在被面上,一五一十的数起来。
“不对,爷爷。一共只有九百二十四。你看。”数过一遍,她抬头向爷爷说。
爷爷把这笔钱看的比命还重,隔三差五的拿出来核对核对,生怕有一天这些钱会长出翅膀飞走了似的。爷爷对这笔钱的支出也是精打细算,除了她的学费,以及确实省不了的生活费用,平时几乎是分文不动。听说无故少了两块钱,顿时紧张起来,咳喘的更厉害了,忙不迭的让她在数一遍。
海燕比第一次更加仔细,把钱一张一张平摊在被子上,爷爷也看的真切,可还是那些钱。
爷爷有些坐不住了。身子往上撑了撑,急的抓耳挠腮,愣是想不出那两块钱是用在哪里了。看着爷爷的窘相,海燕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其实在数完第一遍后,她就记起来那不翼而飞的两块钱是怎么一回事了。她只是有些调皮的想试探一下爷爷,看爷爷是否真像村子里的人说的那样,一分钱如命。现在,从爷爷紧张的表情可以判断,爷爷当年因为丢了五块钱而懊悔的两顿没吃饭的是确实有过。如命的传言应该是真的。爷爷曾经把人与钱的关系作出了一个着名的比喻,一直在村子里广为流传————钱就是命,命就是狗屎。
验证了人们的传言,海燕有些心疼起来,后悔拿一开了玩笑。她也明白,爷爷之所以把钱看得重,不是没有原因的。他老人家一辈子在田地里刨食,所有开支都指望那么点粮食(包括皇粮以及各种硬性摊派),风里来雨里去,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几十年,手里几乎没剩下一毛钱。就这么点积蓄,也还是从爸爸寄回来的家用中省下来的。当然,也可以说是从祖孙俩牙缝里抠出来的。别说两块钱,就算是两毛钱,爷爷也舍不得乱花的,更别说不知道钱花在哪里了。
“爷爷……”海燕决定向爷爷坦白,但还是卖了个关子,“前天我从学校讨成绩单回来……你忘啦?”
“哦……”经她提醒,爷爷顿时轻松了不少,猛地拍了一下脑袋,“对了对了。瞧我这脑筋……你语文考了一百分,数学考了九十八。我奖励你两块钱买零嘴吃……你个小讨债的,怎不早说,害我急的要死……”
爷爷大概是看出了这是孙女在逗他,或者是想到可怜的孙女那骄人的成绩,整天愁容满面的他居然咧开嘴,笑了。
海燕也笑了,心里却难过起来。
今天已经是腊月二十五了,尽管爸爸在信上说的肯定,但海燕还是有些担心。去年春节前,爸爸也来信说回家过年。她就天天坐在门前的小竹椅上,边看书,边朝山脚下那条简易公路张望。那种过程是令人幸福的,也是令人焦虑的。她盼望着在某一次不经意间抬起头时,能够看到爸爸那高而瘦的身影出现在山脚下。她甚至在心里谋算好了与爸爸见面时的场景。一旦爸爸出现,她会像真的海燕那样,一下子飞到山脚下,去迎接爸爸。她会扑到爸爸怀里,但她还没谋算好自己该苦还是该笑。不管哭还是笑,她想她都应该是幸福的。
可直到年三十下午;直到山野中此起彼伏的响起人们请祭祖宗时的鞭炮声;直到人们都围坐在自家的桌子旁,高高兴兴的合家享用团员饭时,爸爸还是不见踪影。她急切地目光都要把挡住视线的群山穿透了,却依然什么也没看到。
有了这样的经验,她的担心就不显得多余了。她有时想:钱真是个神奇的东西,就那么一张薄纸,却有着那么大的能量。它能使拥有它的人活得有尊严,活得有滋有味,活得随心所欲;也能使得不到它的人活得低三下四,活得颠沛流离,活得如蝼蚁般卑贱。连最起码的天伦之乐都难享。这样的感悟本不该是她这个年龄段的人而有的,但她却又了这样的感悟。这或许就是生活的神奇之处吧?
又落雪了。大雪飘飘洒洒,宛如漫天飞舞的柳絮。半天时间不到,地上便积了厚厚一层,像是要急于掩盖什么似的。
海燕急了。爸爸还没回来,然而,已经是腊月二十九了。明天就是年三十了。看来正如她担心的那样,爸爸打算回家的计划将会又一次落空。这对于她而言,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啊!要知道,由于年的脚步越来越近,已使这个平素不大热闹的小山村逐渐有了节日喜庆的气氛了。大人们邀三请四,互相帮忙杀猪宰羊,忙得团团转,为过年准备着吃食;孩子们则偷出家里为过年准备的鞭炮,这儿扔一枚“嘭叭”,那儿扔一枚“叭嘭”,伴着孩子们的嬉闹声,热闹了整个小山村。
海燕感到无比烦躁,说不出什么原因。家里只有她与爷爷,一老一小,枯坐着。与外面热闹的气氛相比,更显得冷冷清清。她原本就清瘦的小脸庞愈加清瘦了。她表情木木的,双眼充盈着泪水,欲滴未滴的样子。着或许就是哭的最高境界了。没有大声嚎啕,没有涕泗滂沱,不张扬,不歇斯底里。那种隐忍的、含蓄的姿态,叫人看了更加心疼。
海燕已经不打算再走出门向山下张望了,那种过程是痛苦的,期望越高,失望越大。她已经接受了爸爸不能回家这一现实了。再说,不接受又能怎样呢?这几年,不都是这么过下来的么?
“咯吱咯吱……咯吱咯吱……”
门外有脚踩雪地发出的声音。海燕心里一惊,像是突然得到了某种启示,迅速从堂屋的小竹椅子上弹了起来,用手背揩去蒙住双眼的泪水,扑向门外。
果然有一个高高瘦瘦的人,肩上扛着一只大包,歪着脑袋,走上了她家门前的场地。
“爸爸回来了。爷爷,爸爸回来了……爸爸,爸爸……”
海燕兴奋地往那人跟前跑去,边跑边回头喊,要将这一天大的喜讯报告给爷爷。毕竟四年了,老人家也没见过儿子一面。
那人站住了,从他的身上和包上的污泥可以看出来,着一段难走的山路使他摔了不少次跤。他腾出一只手,摘掉遮住大半截脸的口罩,顺手将头发上的雪花打落,咧了咧嘴,一脸苦笑,声音低沉的说:“海燕,我是你猴叔。你爸爸他……走,进屋再说。”
海燕的心一下子冷了,手足无措的呆站在雪地里。大概是刚才的满腔热情无处释放的缘故,她有些气急败坏的轮流抬起左右脚,胡乱踢踏着地上的积雪,像跟谁赌气似的,不愿进门。但家里发生的一幕,又迫使她着急忙慌地跑进堂屋。
“老李叔啊,我小猴子对不住您老人家哟……哦呵呵哦呵呵……”
小猴子刚跨进家门,把包往墙角一放,就跪在爷爷面前,放开喉咙哭了起来。
海燕与爷爷同时蒙住了,不知小猴子是什么意思。海燕靠在门框上,呆望着小猴子的背影。爷爷做了个搀扶的动作,说:“大侄子你这是咋啦?快起来说话。莫不是把树根托你捎回来的东西弄丢了?丢了就丢了。不要紧,你李叔不是他们说的那号人……快起来说话……”
“不是……”小猴子跪在那里不动,“是我没用,没照顾好树根。树根他……树根他……”
小猴子泣不成声,只是抖了抖手,指了指墙角的那只包。
海燕与爷爷几乎同时将目光射向那只包,仿佛包里藏着某种天大的秘密。
爷爷咳喘了几下,颤声问:“树根……树根咋啦?”
“老李叔啊,树根他,他回不来了。他最后一个班,从三十三层人货电梯口摔……”
“嘭……”
海燕的大脑一声巨响,恍惚中看见爸爸正惊恐地瞪着双眼,手脚乱蹬鲁昂划,从三十三楼飞也似的坠向地面。她眼前一黑,顺着门框软软地瘫在了地上。
醒来时,她发现自己已经躺在床上了。床边站着村子里的几位婶婶辈的妇女,个个神情凝重,默然无语。堂屋里有男人们交谈的声。小猴子带着哭腔叙述着:“……摔得太惨了。就不该趴在人货电梯口朝下喊呀!你们不知道,每一层都有按铃,你在哪层按,电梯会有专人开到哪层接你……他非要朝下喊,脚下一滑,就……”
海燕一激灵,翻身起床,连鞋子都没穿,冲到堂屋分开众人又冲到八仙桌前。爷爷木然地坐在桌子旁,眼神浑浊而干涸,样子更像一只挨了主人毒打的老狗了。爸爸的骨灰已经被人们从包里移到桌子上了。海燕踉跄着扑了上去,紧紧搂住爸爸的骨灰盒,脸上的肌肉使劲往眼眶处挤,嘴唇颤抖着,泪水顺着双颊往下流,但愣是没哭出声来。众人见此情景,都悄悄的抹眼泪。小丽的妈妈没忍住,放声大哭起来,边哭边轻轻抚摸海燕的头,带着哭腔安慰:“小乖乖呀……要哭,你就哭出来吧!不能……憋着啊……”
海燕终究还是没哭出声来,就那样紧紧搂着骨灰盒,就像紧紧搂着爸爸一样。任人怎样劝,都不肯松手,生怕一松手,爸爸就会永远离开她似的……
雪落的更大了。大年三十那天,整个世界已是洁白一片了。除了西山顶上偶尔传来的几声寒鸦哀啼,整个小山村没有任何声响,安安静静的。仿佛这个世界原本就洁白无瑕、安安静静的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