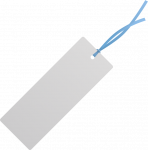日落田边炊烟上
一

镶嵌在白墙中的木门只露出一条缝。“吱呀”,门缓缓地推开,“当——”,挂锁恶意地扇了门一掌。低头弯腰走进院子,进入眼中的,是另一侧的白墙,墙边残存着一些枯萎的灌木。还有那口酸菜缸,上面压着愣头愣脑的青石,却不能阻止,酸菜的味道,传到院子里每一个地方,有一分熟悉,夹杂着九分的陌生。
房门前的帘子突然被掀开,“回来啦,”姥姥端着掉漆的铁盆走了出来,看见我,急忙把盆用左手拎着,右手来抢我的行李。我并没有松手,姥姥把门帘掀开,带我走进去。“姥姥晚上做酸菜白肉。”说着,姥姥又掀开门帘走出去了。
我放下行李,把那只精心挑选的北京烤鸭放在厨房门口,转身走出门,姥姥在水缸前慢慢地搬起缸里的青石,我跑上去,帮着姥姥抬起青石,青石趁机把所有的力量压在我的手臂上。渐渐撑不住,我把青石搭在水缸边上,一声碰撞。姥姥抓着一颗酸菜,“小心,别把石头磕坏了。这可是老物件,你妈妈小时候就在用了。”酸菜以为姥姥在训斥它,流下酸臭的汗水。
放下青石,抬起头,太阳落到了西边人家的屋檐上,烟囱高举着太阳。可能烟囱也要力量不支了,太阳一点一点降低下去,隐去了一部分身影。
二
“昨晚下雪了。”姥爷拉开窗帘。我裹着棉被,爬到窗前望了一眼,又不是一眼。近处的土地是一片洁白,只有零星的蓄水池睁着眼睛凝望着天空;远处的山上,一些精神异常的树脱掉了白色的羽绒服,挥舞着手臂裸奔,却没有留下一个脚印。
钻进被子,我快速地穿上衣服,又套上羽绒服,跑向了大门。学中医的姥姥叫住我,“身上有汗,等一会再出去,一吹了凉风,汗毛孔一张开就感冒了……”大铁锅里小米粥升起轻浅的烟雾,飘进了烟道。
身上的汗干了一些,还幸存着一些。我转动把手,一丝调皮的风自觉地挤进门内,好像也没有那么寒冷。把门打开,那一丝风的亲戚都拥在门口,突然间就开始抚摸我身上各个地方,羽绒服也有些支撑不住。坚强地迈出一步,门框上潜伏许久的雪跳下来,钻进我的衣服里,瞬间的寒冷渗入皮肤里,那一片衣服哭了,把泪水都留在我的后背上,潮湿地粘在一起,我并不感到舒服。
可能是冷风的压迫过于残酷,连“香”飘满院的酸菜都不敢发声,只是低声嘀咕着自己的不满。木柴堆上点缀着一撮一撮的雪,斩成一节一节的树枝焕发了成为灰烬前最后的生机,开出了不属于它们的白花,映着天与地的颜色。
跑出比我略高的院门,远处的白房子融进了天地的颜色,有些看不清楚了,只有屋檐的黑瓦还在固守最后一条警戒线,但也将自身难保。昨天消失在田边的太阳并没有在山头挂起,只是在浓重的云层之上,迎着寒风把天空照亮。炊烟还没走出烟囱,便已经失去了形状,只有时断时续的一阵白雾,诉说着每一家清晨的味道。
三
姥姥拿起刀,“咔咔咔”的声音传来。我骑着滑板车钻进厨房,水池里的水盆中,躺着半死不活,泛着昏黄的绿色的泥鳅。
肥瘦相间的肉一片一片脱离开来,躺在纹理均匀的案板上,我停下滑板,碰了一下一片肉,一点凉意走上指尖,滑腻的感觉停留在手指前面。姥姥抓起我的手,“不要碰,有细菌。”
走到窗前,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只有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将一片天空染成蓝色。在余晖的照射下,远处的人家起了炊烟。转眼,夕阳彻底消失在田野的尽头,那一抹炊烟也看不见了……
“来,洗手吃饭了。”姥爷垫着抹布把盆子端到桌上。没用香皂,打开水龙头让手湿润一些,便甩着水来到了桌前。坐到椅子上,双腿悬空地踢来踢去。
宽大得肉片平铺在最表层,在灯光下泛着光泽,死气沉沉的血肠挤在白肉形成的平面上,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圆,翠绿的香菜被恭敬地供奉在最中央,翘起碎花的裙摆。拿起筷子,伸向血肠,然而一下就捅到了它的身体里,瞬间就失去了形状。姥爷架起一片肉抱住了我夹的那个血肠,放进我的碗里。肉片展开,血肠已经破碎,一块块血纷纷扬扬落在米饭的周围。夹起肉片,咬住,肥肉的一条被我撕了下来,吸溜进嘴里。瘦肉也放入了嘴里,嚼一嚼便吞了下去。嘴还在咀嚼,筷子已经迫不及待伸向另一块白肉……
“来,粉条,”姥姥的筷子上搭着下垂的粉条,我自然地端过碗,粉条都盘旋着落进我的碗里。“细嚼慢咽,对胃好。”姥姥腾出筷子,夹了一些酸菜丝。
四
姥爷在后厅的一群麻袋里翻找,终于揪出一大把粉条,放进铁盆里。把麻袋口翻折,他站起身,平视我的眼睛,“你喜欢吃粉条,今天多加一点。”
“这个烤鸭也吃了吧。”我拿起烤鸭的盒子,让它更清晰地展现在姥爷眼前。他们都在东北,没吃过正宗的烤鸭。也要,让他们尝尝,我所生活的地方,最著名的味道。
“这个是凉的,要不在锅上蒸一蒸吧。”我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我也不知道,凉了的烤鸭要怎么热,才能展现原本的味道。
酸菜在锅里已经煮起来了,上上下下翻滚着。揭开锅盖,水雾迅猛地闪出一团,扑腾在我的脸上,瞬间便温暖了,然后就变得湿润,又很快凉下来。屋顶上,如果没风的话,大概就是孤烟直了吧。但也不是孤烟,家家户户,应该都在烟火气中,等待平静的晚餐了。
姥姥姥爷在下肉片。我走过去想帮一把手。“不用你了,歇一会,一会儿吃饭了。”
掀起帘子走出屋子,天空已经慢慢地刷上蓝黑色。太阳蹒跚的背影靠在西边的田野上,近处除了正对着窗户的木柴堆还能看清楚模样,其他的都只是一团黑影了。远处的田野里有几户农家,明亮的窗户上方,烟囱升起笔直的炊烟,在夕阳前铺陈一丝朦胧。下一秒,一阵风吹过,炊烟就柔弱地改变了身姿。
五
和其他人家的孩子打雪仗,我的身上已经没有一处是干的了。手套几乎成为一块泥巴糊在手上,我干脆把手套摘下,让手直接碰触冰冷的雪。手冻得通红,冰冷的感觉让我对雪已经有些厌恶了。惭愧,虽然故乡在此,可是多年在京城的学习生活或许让我对于打雪仗这种本应该最熟悉的东西都不擅长了。
玩了多久呢?直到姥爷和其他家长来叫我们回家吃饭时,太阳只是站在目光所及的田野上,发出温和慈祥的光。西边除了一片橙色的光影,深蓝色像东方渐变,却走不了几步,便被黑色吞噬,再也没有生机了。
向西,朝着家走去,近处的院子和远处的人家不约而同升起炊烟,希望为我们点亮回家的路途,却远不及手电筒和各家窗中的灯光好用。经过许多院子,感觉他们散发的气息也是不约而同地,相似地,在一些油烟气息中带着腌酸菜的味道。
进了院门,炊烟在灯光的渲染下,略微看得见身影,在钻出烟囱的一刹那还很清晰,远了,散了,便看不见了窗户里投出的光照到柴火堆上,换回了一片死寂。不知谁家的狗催着太阳离开,夕阳隐去了所有的光亮,远方成为了一片漆黑,只留下那几户人家掩埋在窗帘后面的朦胧灯光,和整条街上每个院子里飘荡的菜香,越过街道,翻过墙壁,传到别人家里。他们偶然细嗅,心中一惊——竟然是相似的味道。
六
姥爷把最后的箱子拎出院门,关上院门,上了锁。来接我们的叔叔早把车停在了路上,我们放好行李,坐上车,一溜烟便开走了。我回头望着玩乐的院子,慢慢地与别人家的院子混合在一起,再也看不出了。
“开往北京站的……”姥姥姥爷让我走在前面,和一群背着大包小囊,拖拽着行李的人一起走上了火车,经过了一夜,在平日里炊烟升起的时候,我看到的是火车头冒起的黑烟。许久不见的父母开心地见到我,把我们用车接回了家里。桌上的早餐也是小米粥,只是那种香气,只有进到了屋子里才能闻到。
家住高层,每每在夕阳西下时走到窗边,太阳在目光所及的最远处慢慢地隐去了身姿。没有炊烟,倒是满地的灯火点亮了整个黑夜。不论天空怎样的黑,向下看,街道上的灯火以及往来的车流永远照亮着街道。楼房起伏,不再是一望无际的平原,也不再有一座大山的依靠。偶尔几座高楼遮挡了太阳下山的轨迹,完整的太阳隐藏在高楼的后面,只露出一部分,作为我的念想。
过了几周,我又和姥姥姥爷坐上了车,只是这回,是姥姥姥爷要回去了。在检票口,我吃力地提着一个兜子。姥爷拉着我一只手,说,“快上小学了,要好好学习,努力读书啊。”
火车头不断地冒出黑烟,“嘀——”一声鸣笛,我全身一抖。火车开了,姥姥姥爷隔着窗户挥着手,随着火车走远。一会儿,只剩下光秃秃的铁道,铁道下面,在石子当中躺着的,我认为是多余的木柴没有烧,幸存在石子中间,只是它们的样子过于整齐,我又觉得应该不是。
七
姥爷把密封包装剪开,把烤鸭倒入盘子里。烤鸭的酥皮在灯光的照耀下,泛着高贵的光。放进蒸锅中,“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啊。”姥爷嘀咕着。
姥姥姥爷上一次吃烤鸭应该是十几年之前了吧。我在记忆里苦苦思索,应该是把我送回北京上小学时,在北京住了几天,有亲戚请他们吃过烤鸭。应该,只有那一次吧,毕竟东北菜丰富,并不会多次接触北京的特产,就好像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并不能发现日落之时,素淡的炊烟升起在一望无际的,沉默的田野。
我猛然想起,回老家之前的最后一次吃酸菜,还是在过春节之前。将近半年过去,那一顿酸菜白肉的印象却让我苦苦思索,可能是太过平常,所以我早已忘了吧。我只是记得,那一次,我在掀开锅盖时,水汽缓慢地推出来,我把脸伸过去,希望感受到水汽的湿润与温暖,但许久,只有零星的温润感觉,大部分的水雾在吸油烟机的鞭策下,早早地离开,哪怕绕路经过脸庞,走向了烟道里。屋顶上会有炊烟吗?我哑然。大概,大部分的烟气,可能已经在烟道里不知所往了吧。就算它飘到楼顶,又有谁,会在日落时观赏楼顶微不足道,又转瞬即逝的一丝炊烟呢?
屋里的灯光明亮,漆黑的窗外闪着屋内的影子,远处人家的灯火已不甚清晰,田野则完全陷入了沉睡。我走到窗前,把脸贴到窗户上,却也看不见别人家屋顶的炊烟。
八
脱下全身湿透的衣服,直接去洗澡。关上门,打开水龙头,温柔的水小心翼翼地洒在我的身上,泡在雪水里的身体突然很温暖。渐渐地,镜子里的我模糊了,洗手间也越来越热,一大团水汽汇集在浴缸周围,又挪动到屋顶。
洗完澡,走到饭桌前,桌上的大瓦罐盖着盖子。姥爷拿着抹布缓缓掀起盖子,盖子周围先出现了一层水汽,如一层纱裙,朦胧地遮掩着蕴含的秀美。里面果然是酸菜白肉,酸菜和肉缠斗在一起,在汤中时隐时现,而血肠则十分规则地排成了八边形。
“好几年没回来了,冬天回东北吃酸菜啊。”姥爷笑着端起白酒杯,喝了一小口。
夹起一些酸菜放入口中,隐隐约约,好像有小时候的感觉,但并不真切。“来,吃肉,吃血肠,你和你姥爷一人三个,我吃两个。”她把血肠夹进我的碗里,用大勺子盛了一勺汤。一些酸菜也好奇地跟了上来,在酸菜中间,露出了五花肉肥肉的一角。姥姥把勺子换到左手,右手拿起筷子,夹出那块白肉,递到我的碗里。
九
“写一篇作文,讲述我的家乡。”卷子上的字映入眼帘。我在脑海中回想老家的场景。
在半山腰的空地上,向远处看时,全是绿色,田野里和半山腰是青翠,山坡上的树和远处茂密的林子是浓厚的绿色,进出远处都是一家一户的院子。平房刷着白墙,青瓦歪斜在屋檐之上。乍一看时,似乎是江南小镇的马头墙和江南的园林穿越时空,来到小兴安岭的山村之中,远处的树木隐蔽了几家院落。时至中午,家家户户的屋檐上升起长长的炊烟,携带着家家户户的烟火气,飘散,飞舞。它们向上飞呀,飞呀,或许来到了蓝天中,就成为了白云,在风中缓缓漂荡到田野的尽头,倏忽不见。或许,它们充盈在天地,让一分极其微弱,又十分鲜明的味道徜徉,或许,远离家乡之后,我也不会孤单。因为家乡的气息,永远陪伴。
脑海中的景象落到小学生的笔下,却读不出家乡的优雅,只是一些景物,孤单地站立在一副画板之中。看完自己当年的作文,我会心一笑。
太阳西沉在繁华的城市,打开窗户,我假装自己,看到了一抹抹平静的炊烟;闻到了,故乡的田野上,家家户户传来的永恒味道。
十
“老头子,来吃饭呐。”
我坐在桌前,并没有动筷子。姥爷放上沾着水珠的酒杯,满满倒了一杯白酒。“这烤鸭油可真大,”姥姥夹起烤鸭,看见盘子里流出的油,又把烤鸭放下。
“这烤鸭怎么吃?”金碧辉煌的饭店里,姥爷指着烤鸭问。妈妈熟练地卷了一张烤鸭饼,递给姥爷。又卷了一张,夹到姥姥的盘子里。
圆桌上筷子你来我往,但很少有一双筷子迈开双腿,走进烤鸭的盘子里。
“爸再吃一张鸭饼啊,烤鸭剩了不好热了。”爸爸看着剩下许多的烤鸭,“妈你也来一张。”
“不了不了,我吃饱了。这烤鸭油可真大。”姥姥拿一张餐巾纸,撕成两半,一半放到姥爷手边,另一半拿起擦擦嘴。
“来,吃吧吃吧。外孙带回来的,可得尝尝。”姥姥看见没有人动筷,便发动起来,同时以身作则豁开烤鸭的酥皮,连皮带肉夹起来一大块。我们便也把筷子伸到桌上……
把血肠和一片白肉夹在一起,蘸满了蒜泥,一张口便吞了下去。带着些血腥味和油腻的气息,再用勺盛一些酸菜汤,酸的味道瞬间拂过,在嘴中不断地充盈,绽开。我又夹了一块肉。
“慢点吃,细嚼慢咽。”姥姥看着我,夹了一筷子酸菜和粉条。
“来,烤鸭,你也吃啊。”姥爷在姥姥豁开鸭皮的地方,也撕下一大块肉。我把筷子伸到烤鸭上,轻轻地点了一下。
蒸过的烤鸭水灵灵的,油光光的,摆在正中间,看上去完完整整的,却在极显眼的地方,被剥去了一块皮,露出一条条白白的,毫无血色的肉,让人不寒而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