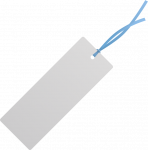祖母的哈达
1

自从父亲去世后,我们家就把祖母彻底地丢了。
父亲在的时候,曾带我去给祖母上过坟。祖母的坟茔在一片黄花菜田的尽头,是一个比田地略高一点的土包子。
为什么会埋在这里?因为这块田当时是属于我们家的。可是,后来村里重新分田,这块田分给别人家了。
一个没有石碑,没有树木做标记的土包子,好多年,连培土上香的人都没有,它隆起的那一抹小小的弧度,早被风雨夷平。
每年清明,我回家看望父亲,总会经过那一片黄花菜地,我却一次都没有走进去。我不能确定祖母到底住在哪里,也怕侵扰了田地现在的主人。我只能多给父亲捎钱,请他分一些给祖母。
2
祖母是1982年去世的。那年我十一岁,清晰地记得大人们说她活了七十八岁。按照虚岁推算,祖母应该是出生于1905年。到底出生于哪一月哪一天,我就无从得知了。
我甚至不晓得祖母的名字,只晓得她姓张,别人都叫她张婆。祖母的娘家在岳口健康村。小时候,每到春节,祖母总会带我去那里玩几天。佐城伯和府城伯,这两个留在我记忆深处的人,应该是祖母的两个外甥儿子。
祖母有几个兄弟姊妹,我就不记得了。只记得祖母有个妹妹,我喊她姨婆。这个姨婆是常来我们家走动的。姨婆和祖母长得很像,都是高瘦身材,大团圆脸。
祖母去世后,佐城伯和府城伯就不再跟我们家往来了。姨婆来过一次,那天我正在灶门口放柴禾,猛一抬头看见姨婆,以为是祖母的魂魄回来了,吓得差点钻进灶火里。
祖母在人世间挣扎了七十八年,流了多少汗,吃了多少苦,却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一抔黄土,甚至一个名字。生如草芥,死化尘埃。从孙子这一代起,就磨灭了记忆。只要想想,我就为生命的卑微而潸然泪下。
3
祖母一共生了七个儿女,只留下了长子和幺儿。就是我的伯父和父亲。伯父比父亲整整大了二十岁。这二十年之间的岁月,对于我的祖母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黑洞。
我的二伯父是在读天门师范的第二年在县河里溺亡的。还有两个伯父和一个姑妈,都是十一二岁夭折的。
最小的姑妈是不足月生下的,祖母担心养不活,将她送给了健康村一户不能生养的人家。这个叫桃枝的姑妈,在祖母七十岁那年,给她送来了一套青花瓷缎面的夹袄夹裤。祖母就是穿着这身衣服走的。
听人说,我的二伯父是长得最俊了,方面大耳,白白净净,而且有过目不忘的好记性,深得祖母宠爱。
二伯父特别擅长游泳。据说在水下拱背可达一个多小时。出事那天,二伯父就是在给同学表演拱背。结果,两个多小时没出水,大家才开始着慌。也是命运捉弄,能水的二伯父竟然就栽在浅水坡上,半边身子青紫。
白净净的一个儿子上学去,黑漆漆的一口棺材抬回家,我的祖母当时就晕过去了。六月的雪飞进祖母干枯的发际,再也没被融化。祖母从此耳闭,腰身也不再挺拔。
4
哭过长夜的祖母,将仅剩的两个儿子紧紧地搂在怀里,不敢再有半点闪失。
我父亲自小聪明,长于记忆,精于算术。他曾以岳口区第二名的成绩考入天门中学。可是祖母说什么也不让他去天门读书,父亲就此辍学。
辍学后的父亲,一定是与祖母生了隔阂。因为多年后,父亲偶尔对我提起这事,还对祖母多有怨怼。他说,要是去天门读几年书,文革后恢复高考,就绝对可以脱离农村了。
父亲是祖母四十四岁生的幺儿子,是典型的秋葫芦。一向瘦弱多病,要是能脱离农村不干繁重的体力活,可能就不会刚到知命之年就去世了。
七个儿女,损失过半。最疼的老幺,也在心里与自己隔膜。祖母的心,一定比黄连还苦。但她无法述说,也无处述说。记忆中的祖母,总是在跟一辆纺车絮谈。
纺车的声音,混合着风声雨声,鸡鸣狗吠,嘤嘤嗡嗡,像一支老掉牙的歌。祖母面无表情,动作舒缓。她摇着纺车,摇着时间的经纬,摇着人生的起落,摇着命运的悲喜。
一根根棉芯被纺成线,织成布,缝成衣服和被褥。祖母的生活,就这样周而复始地旋转着,粗糙而单调。
5
我出生就没有见到祖父。只记得家里还有个二祖父,腿脚不灵便,长期依靠板凳挪步。听说,二祖父是在年少的时候被旋窝风旋倒后瘫痪的。他终身未娶。年老后跟着伯父过,祖母跟着我父亲过。
祖母与母亲的关系一向不好。我大弟出生时才两斤多,成年后也只有一米五几。母亲总是记祖母的仇,说她怀大弟的时候,每天上工回家,最害怕吃红薯,偏偏祖母就只焖了半锅红薯。母亲经常饿肚子,就造成了大弟的先天性营养不良。
都说姆妈最疼幺儿,祖母心疼我父亲,不可能故意刻薄我母亲,一定是当时的物质条件实在不好。母亲也一定是爱子心切,才迁怒于祖母的。加上父亲身体不好,粗活重活都压在母亲肩头。她脾气本就暴躁,自然对祖母没有好声气。
总之,我年少的记忆里,充斥着她们的争吵。
儿子怨,媳妇恨,我难以想象祖母的生活有何幸福。她就像那路边的苦艾草一样,被马蹄踏过,被牛车碾过,却仍能晃晃悠悠地站起来,维持残破的尊严。
6
祖母年迈,不能下地干活,就操持着家里的细活杂活。
她总是是天麻麻亮就起床,先打开鸡笼,再洒扫庭院,然后就是做饭、洗衣、喂猪……禾场里的鸡粪和牛粪,她会小心地拾掇起来,撒到菜田里。
我小时候虽然粮食还够吃,但下饭菜都是季节性的,难免单调。祖母总是变着花样做菜。红苕梗子和芽尖都可以摘来清炒,埋在窖里的红苕,过年吃比梨子还甜。马齿苋、南瓜藤,这些别人家不吃的东西,祖母也能做出美味。
祖母是制作腌菜的行家里手。她做的乳豆腐,色泽鲜红,硬中带软,口齿留香。她做的豆豉,咸淡适中,回甜化渣,鲜美可口。她做的酱油瓜、扎辣巴子,都是下饭的佳肴。
“容儿,回来吃饭呃——”每当祖母的声音伴随着夕阳的余辉,回荡在田间村口,无论我是在踢毽子,还是在跳房子,我都会立即停止游戏,撒着欢儿跑回家去。
对于我来说,家的味道,就是祖母的味道,就是祖母做的那些美食的味道。
7
我是祖母一手带大的。吮吸过她干瘪的乳房,攀爬过她弯曲的脊背。我最初的温暖与光亮,都是祖母给的。年幼不懂事的我,却很少体恤她的难处。
家里添了小弟后,我被安排跟祖母煨脚。这是我很不情愿的。
祖母裹得一双小脚。每晚睡觉前,祖母总是用热水泡,用纱布缠,可被子里总有一股异味。在寒冷的冬夜,当我嫌恶地躲避着她的脚时,我的脚却被搂在她暖和的胸前。
祖母耳闭。我跟她说话,总是踮起脚,将嘴巴贴近她的耳朵。就是这样,她还是经常听不见。有时候,重复多次后,我会躁得蹦起来。
祖母从不跟我计较。每天清晨,祖母都会给我炒一碗油盐饭,让我吃了上学。偶尔,还会是蛋炒饭。有一次,祖母不知怎么攒下了一钢碗猪油,每天在我的饭里埋下一小勺。猪油饭香喷喷的,我连续吃了个把月,觉得生活都是香喷喷的。
我每个学期得的奖状,都是祖母亲自做了浆糊贴在墙上的。有一次,我听见她跟我父亲说:“这个女娃聪明,你让她把书读大一点,你将来要享她的福的。”
村里与我同龄的,大多小学毕业就去学手艺了,只有我读了中学,又考了师范。可是祖母还没等我考上初中就去世了,父亲在我成家没几年也走了。他们都没能享我的福。只有母亲,这些年一直由我养着,也算是没让祖母的话落空。
8
1982年夏天的那个清晨,我醒来,发现自己睡在堂屋的竹床上。家里轻悄悄的,没有祖母活动的迹象。我意识到不好,慌忙喊起父亲。然后,我就听到了父亲的哭声。
祖母是被一条白绫带走了。我从不相信吊死一说。因为祖母的身子根本没有悬空。她双腿跪在床上,双手拽着白绫,好像在向谁敬献哈达一样。
床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七套新衣,最上面的一套,就是我的桃枝姑妈送给她的那身青花瓷的缎面夹衣。祖母平时都是粗衣烂裳,这些衣服是她多年积攒下来的,每年六月六都会拿出来晒一回。
祖母穿着这七层新衣,静静地躺在木板上,这可能是她此生最体面的一次。我的桃枝姑妈、姨婆和两个恩婆,在她的身边哀哀地哭。她第一次这么倔强地理都不理。好像这个世界,本就与她没有任何关系一样。
在火化当晚的招魂仪式上,我们将祖母平日穿的衣服焚烧。明亮的火焰中,我仿佛看到了车马仪仗的影子。父亲说,这是天神驾着马车来接祖母了。我愿意相信这是真的。在人世间受尽磨难的祖母,也该到天上享享清福了。
9
祖母走了。她的三寸金莲小之又小,留在这个世上的脚印本不清晰,上面又叠加着猪呀鸡呀牛的脚印。她的生命轻得就像一朵蒲公英,风一吹就散了,再也无从寻觅。
属于她的七十八年,只是一场噩梦。
小时候,每次听别人说我长得像祖母时,我总是以祖母那么高我这么矮相反驳。如今,对着镜子里这张初现皱纹的大团圆脸,我默认了。
生命的密码是无法篡改的。在我的身上,流着祖母的血。我生命的黯淡与精彩,都是拜祖母所赐。我是祖母留在人间的脚印之一。
每次想起祖母离开人世的姿势,我总是觉得庄严而圣洁。
我生平接受过别人敬献的一条哈达,也是白色。那是一个西藏姑娘双手奉送的,她说,扎西德勒!扎西德勒,是祝你吉祥如意的意思。
我又了解到,哈达也有多种颜色。蓝色的代表蓝天,白色的代表白云,绿色的代表河流……
我的祖母,她是坐着白云走的。她留给我们的遗言是:扎西德勒!
(原创作者:熊荟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