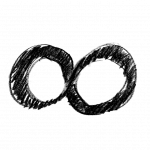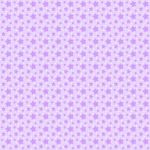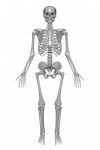我的启蒙老师(上)
一

1978年夏末的一天晚上,父亲领着我来到小五爷家,极其恭敬地说:“五叔,小子上学的事就交给您了,他要是不听话您打也打的,骂也骂的!”
小五爷慌忙起身,“凤岐(我父亲的名字),看你说的,孩子交给我你就放心吧,唉,这没娘的孩子,谁舍得打骂?”
那一年我8岁,秋天一开学便成了小五爷的门生。
小五爷其实那时年纪不过30出头,论辈分,确实是我本家已出了“五服”的爷爷,他也是我们张家家族这一辈人里年岁最小的一个,那时我父亲的年纪也比他这个五叔长了近20岁。不过“萝卜不大长在辈儿上”,因为小五爷兄弟五个,他行五,所以我们这些小辈人都尊称他为“小五爷”。小五爷年轻时当过六年兵,听说是被他母亲强拉硬拽回的老家,随后在村里的学校当了一名老师。
也许70年前后是人口出生的高峰期,造成我们这批新入学的同学格外得多,我们的一年级只能被分为甲、乙两个班,这也是村里学校史无前例的,小五爷是甲班的班主任。那时村里的小学校只有有限可用的十几间教室,既包括初中,又包括小学。我们这个班没办法只能借用在一间离学校挺远的三间闲置民房里上课,而且没有课桌和椅子,于是架起20来张1米长短的石条代替课桌,学生们从家里搬来小板凳、小马扎就是座位。虽然硬件艰苦,可是几十个孩子心情却相当不错,这么多小伙伴真是难得聚在一起,这下可有人一起玩啦。整个班级就小五爷一个老师,语文、数学、美术、体育都是他一个人兼职,教室与办公室同样集于一身,师生们朝夕相处,俨然就是一个大家庭。说起那时小学的课程与现在相比确是有天壤之别,知识点都是基础的基础,语文的拼音生字、造句默写,数学的加减乘除、“小九九”口诀,等等,对于大部分孩子们来说不算是艰难的课程。当然这里也有例外,班里有一个小名儿叫小营的留级生,年纪要大过我们好几岁,应该是多次留级,被大家戏称为“一年级万岁”,当然这只是在背后,当面我们尊称他为“营哥”,他的个头、他的拳头对我们都很有威慑力。营哥虽然学业不佳,但在课堂上会常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快乐。有一次上识字课,学习青蛙的“蛙”字,大家高声跟读若干遍,当小五爷轮流提问同学们,问到小营时,得到的回答是,忘了!小五爷多方启发未果,最后在黑板上画了一只鼓眼蹬腿的青蛙,惟妙惟肖。小五爷黑着脸问,这是什么?但见小营低头沉思良久,脸憋得通红,吭哧瘪肚地吐出俩字,蛤、蛤、蛤蟆!顿时,整个教室一片欢腾,桌椅山响,小五爷只有无奈摇头苦笑。
因为学业不紧张,大家玩的时间充裕,加上小五爷寓教于乐的教学方式,所以同学们逐渐忘却了学生对老师与生俱来的那份怕,代之更多的是长幼间的亲近感。由于当过兵的缘故,小五爷上的体育课也渗透着部队的味道,从基本的稍息、立正到起步跑步,他的要求一丝不苟,谁也不许偷懒,不然,得到的处罚也是挺严厉的,有时要反顶着帽子站上半小时,这谁受得了(新兵连时我才知道,其实这是部队训练军姿的方法)!上体育课时,我最喜欢的是“跑步拔旗”的游戏——左右两列同学,相对的两人一组,小五爷一声令下,俩孩子如同脱缰野马,不要命地狂奔向50米开外的折返点,折返点上左右各立一块小黑板,黑板的顶部插着一面小红旗,黑板上早有小五爷出好的算术题,必须做对题目后才能拔旗跑回,先完成的为胜利者。说来惭愧,我自小跑得就慢,站队时和我固定对齐的是一个班里跑得最快的女生小青,拼绝对速度我每次必败,但这个游戏的胜利者还是属于我,因为答题环节是我的优势,每次当我迅速答题完毕拔旗往回跑时,“短跑女子健将”——小青同学那时还在小黑板前冥思苦想,写了擦,擦了又写!
也许是受父亲之托的缘故,小五爷对于我的关照有加,当然我犯浑耍皮的时候他也从没有姑息迁就,虽没有打骂,但是那严厉的眼神,也足以让我想找个地缝钻下去;不过,小五爷从不会把我的“劣迹”向我父亲“告黑状”,相反的,倒是经常在我父亲面前给我美言几句,诸如“富森(我的小名)又作对了一道难题”、“富森的字写得有进步”、“富森第一批加入少先队,还当上了中队长”、“富森评上三好学生了”,等等,听得整日操劳、疲惫不堪的父亲脸上立时绽放出如花般灿烂的笑容。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凭借自己的努力取得一点点成绩,即便仅能给大人们带去那么一丝的快乐和欣慰,也绝对是让孩子们感到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小五爷整整教了我们两年,他象疼爱亲生儿女般疼爱着他的学生们。记得冬天到了,那时的冬天真冷,风雪也真大,我们那“民房教室”四壁漏风,冻得我们的小手哆嗦得握不住铅笔,小五爷自己用小推车从老远的学校一趟一趟拉来大堆黑亮的煤块,又用砖头泥巴盘上炉子生火取暖;再不行,就为每个孩子准备一个破搪瓷茶缸,把烧得通红的煤块放进去,给我们焐焐手焐焐脚。暑假来了,小五爷领着我们来到田野里,打芦草割野菜,草交到生产队喂养牲口,得了收入,新学期为我们添置铅笔、橡皮、作业本,野菜则拿回家喂鸡喂鸭喂兔子,分担一点大人们的工作压力。
两年间,我们得到了人生最初的启蒙教育,尽管那时物质生活不是多么丰富,但是我们也同样享受着童年那无忧无虑的欢乐。等到三年级开学,由于学校扩建了教室,这个年级的这甲乙两班最终合并,我们这30来个学生也随即搬离“民房教室”,回归本校区,随后班级间也更换了一批任课老师。小五爷因为工作需要,被调到镇中学任专职体育老师,不过家一直住在村上,他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由于我们两家住的不远,因此爷儿俩经常在路上碰面,每次看到小五爷从远处骑车过来,我都会毕恭毕敬地叫一句:五爷爷!那应该是我对他发自内心的敬重;而彼时小五爷总会面带笑容又不失严厉地教训道:别忘好好学习,得对得起你爸爸!
我们这一届同学在村里的学校一直读到初中毕业,那一年,40几个应届毕业生中有8人考入县一中的高中部,这可是我们村学校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好成绩,而这其中当年小五爷任教的甲班占了6席,无怪乎人们都评价说,当年小五爷打得基础好!
二
古语云:人有旦夕祸福,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我上高二的下学期,父亲突然中风导致偏瘫,我的家庭在母亲去世后再次遭到重创。那时,父亲失去了劳动能力,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全家老老少少的吃喝穿用全部压在哥哥一个人肩上,经济的困窘,生活的艰难,让一家人都狼狈不堪。我早已斗志全无,哪有心思学习,草草混到第二年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准备帮助哥哥一起挑起家庭的重担。想的容易,做起来难。一个刚从学校出来,不满二十岁的青年人会干什么、能干什么也是让人头疼的事情。就在此时,小五爷及时来到我家里,他是来和父亲、哥哥商量让我当代课老师的事情。
小五爷那时在镇中学已经不具体任教,专职后勤总务工作。就在几天前,他去县教育局办事得知邻乡的一个村小学正缺少一名任课老师,刹那间想起毕业赋闲在家的我。
父亲和哥哥当时正愁我的工作问题,对小五爷的建议求之不得,半倚半靠在床上的父亲更是翕动着嘴唇,磕磕巴巴地说,全、全凭五叔,您、您安排!
第二天上午,我和小五爷分别骑上一辆自行车,我的车上驮着被褥和简单的生活用品,向邻乡的那个村子进发。“春风得意马蹄疾”,一上路我禁不住有些小得意,毕竟人民教师的职业还是令许多人羡慕的;小五爷可没有丝毫的兴奋,一路上紧皱着眉头,开始一句话也不说,到后来这话匣子一打开便收不住。
“森啊,你家走背运,你爸爸走背运,这么多年愣是没走完,让你和你哥也赶上啦!我这还一直希望你能考个大学,我对你们这一批学生一直都看好哩!”
闻此言,我那一点得意的劲头儿一扫而光。
“这代课老师终是临时的,能不能转正,谁也不知道!有的代课老师一代十几年还是个代课老师,要待遇没待遇,说收入养不起家,你别高兴太早,你的情况,还不如人家!”
我顿时蔫了,犹如霜打的茄子。
“不过,咱干什么就是干一天也得干好,不能让人家说三道四,背后指指划划,这点你爸爸做得好,这些年你家里的日子不容易,你爸干着地里顾着家里,又不忘为村里操办红白喜事,而且做人谦逊实诚,做事不惜余力,咱老张家认,咱全村人也认,如今你爸这一撂倒,喃们心里都急,都想帮一把呀!”
不自觉中,我已是泪流满面。
“甭哭天抹泪的,谁这一辈子还没个沟沟坎坎,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你才多大,有的是机会!”
那一天,时值初秋的季节,“秋老虎”依然凶猛,干热的风很大,而且是顶风,风中扬起的尘土扑面而来,将近40华里的坑洼土路,我竟然没觉得累,没觉得热,没觉得路远。
到达目的地已近午时,小学的董校长显然和小五爷相熟很久,两人拍拍打打,相互开着半荤半素的玩笑。午饭就是在董校长家吃的,我生平第一次喝白酒——五十几度的陕西西凤酒。小五爷不但没有阻拦董校长给我斟酒,反倒命令我多敬校长几杯,还说,成年啦,上班了,男人不喝酒怎么行?
结果,我是不胜酒力,未至半酣我已倒在董校长家的炕上呼呼大睡,隐隐约约听见小五爷跟董校长的谈话。
“这孩子命苦,老伙计给你添麻烦喽!”
“老张,看你这话说的,咱们谁跟谁,放心吧,干,干!”
......
等我一觉睡醒已是日落西山,董校长两口子正笑眯眯地看着我,我一骨碌爬起身,觉得很不好意思,满屋子寻找时,哪里还有小五爷的身影。
董校长摆摆手,让老伴儿给我做碗面条,然后对我说:“你五爷已经回去啦,你今晚就住我家,明天开始去学校上课。”随后,又不无感慨地补充了一句,“这个老张对他的得意门生,真是好啊!”
我在那个小学代课的时间将近一个学期,代的是六年级的课,作为我也想学着小五爷当年的样子,和孩子们打成一片,既能教授知识,又能给他们带去快乐。想法是丰满的,实际是骨感的,古人云:书到用时方恨少,一点不错,可怜我这知识储备不够,想往外倒时肚中没货,也只能成为一纸空谈。不由感慨:当好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谈何容易!
正当我暗下决心、踌躇满志时,另一个机会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