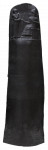赵鼎新:什么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

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展开本文的观点:(1)东亚经济成功的关键;(2)中国古代国家建构及其对于现代经济发展的意义;(3)作为东亚文明的核心地区的中国,为什么其经济起飞滞后于东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
一,后发国家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障碍
二战前,在西方率先兴起的帝国主义与工业资本主义的挤压下,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先后出现了“独立”和“图强”意识。所谓“图强”,核心就是学习西方世界的生产方式,争取在生产能力、经济和军事技术上超越西方。对于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和地区来说,要成功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首当其冲的任务当然是要获取政治独立。二战后,非西方国家先后都取得了独立,但它们中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在很长时间却没能发展起来。
后发展国家在发展经济时都面临着许多方面的强力制约。复杂多变的大国间政治往往是一些中小国家经济长期不能发展的重要原因。
即使避开大国政治不谈,一旦西方国家取得了经济强势,这个强势就会对后发展国家的经济在多方面产生抑制作用。发达国家在技术上的领先会导致国际劳动分工的不平等,使得后发展国家的企业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只能依靠生产低附加值产品生存,从而加剧了后发展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和环境问题,并在国际上形成了不利于后发展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等交换”(wallerstein,1984)。
发达国家的公司能通过政治影响建立一些不利于后发展国家经济发展的市场规则,能通过政治控制和强大的财力(包括行贿)对后发展国家的政治进行操控,迫使这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屈从于西方的公司和国家利益。发达国家的公司在后发展国家的投资,既可能会挤垮地方工业,也可能会因为投资方向的偏颇使得被投资国家发展成为专门生产少数几个商品的“香蕉共和国”(bananarepub-lic),并造成这些后发展国家对投资方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严重依赖。
最后,如果发达国家产生了经济危机,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这些危机对于后发展国家经济将产生更大的影响。比如阿根廷,它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前是西方世界牛肉和小麦的一个重要产地,也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世界经济危机后,西方国家很长时间不再进口阿根廷的牛肉和小麦,把阿根廷一下子打回贫困国家状态。
后发展国家的内部条件也会对经济发展有很大阻碍。现代的市场经济会对传统的经济、权力结构,文化产生很大的破坏。传统的农业和手工业会被现代农业和工业摧毁,传统精英的财力在新的经济条件下会大大减弱,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会随着新型精英的兴起和民众对他们依附程度的降低而大大衰弱。这些都是传统精英所不愿意看到的,也因此会受到传统精英自觉和不自觉的抵制。发展现代的市场经济还需要有大量的廉价优质劳动力。这些劳动力需要受过一定的教育,与传统精英之间不存在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且行为方式不受到反市场的传统文化习俗的严重束缚。但是,在一个传统国家被迫走上现代化道路之时,它的民众往往依附于统精英,并且往往在行为方式上受到反市场的传统文化习俗的严重束缚。
市场本身的性质也会是经济发展的阻碍。现代的市场经济只有在健全的法律体系、一定的教育水准和基础设施的国家中才能很好地运行。市场经济还会带来诸如经济危机、贫富差距、工人失业和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加强社会福利和环境保护才能缓解,一旦得不到妥善处理就会引起政治动荡,从而破坏市场得以良性运行的环境。但是,许多传统国家却往往没有能力大力发展教育和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二、面对于此,为何东亚国家能率先成功?国家的性质!
由于发展的障碍来自多个方面,并且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面对的主要障碍也不尽相同,带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学者和政治家因此就会提出不同的经济发展“理论”和相应的解决方案。具体情况很复杂,一般来说,左倾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往往会把外部条件看作是本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并把违反市场原则的“进口替代”(或“自力更生”)作为政策选项(cardosoandFaletto,1979;Frank,1967)。偏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往往会把一个国家的内部条件看作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进而推崇“现代化理论”和市场经济政策(Black,1986;Rostow,1971;DeSoto,2002)
如果一个理论在某一国家取得优势地位甚至成为国策,其背后肯定或多或少有现实原因。比如,“进口替代”思潮往往会在一个刚独立或者长期受到西方列强控制欺凌的国家中盛行,而“现代化理论”则是西方主流学者的看法,也往往会在一个独立了很久却没把经济搞上去的国家中盛行。
鉴此,我不想对这些“理论”的对错作出简单评判。笔者要指出的是,二战后西方殖民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消退,各国纷纷独立,经济发展正式成为后发展国家的一个共同议题。此后有的国家采取了“进口替代”的发展政策,有的国家采取了市场导向的发展政策,但无论采取哪一种政策,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成功,而经济率先得到突破性发展的国家和地区都在东亚(比如韩国和台湾地区)。
东亚经济成功的关键不在经济政策,而在于国家的性质(Deyo,1987),因为像“进口替代”或者“出口导向”这样的政策本来就各有利弊,并且经济政策的利弊会随时间而变(YangandZhao,2015)。
二战后大多数后发展国家采取了进口替代政策。这对于一个试图摆脱西方列强控制、建立本国独立经济体系的新兴国家来说是有好处的。况且,在进口替代政策施行的初期,许多国家的工业也有很大的发展。但是在没有市场引导的条件下,进口替代生产出来的是高成本低质量的产品,并且这一问题将随着进口替代规模加大和进口替代政策施行时间的延长而变得越加严重。长此以往,进口替代不但不能解决贫困落后的经济状态,反而会造就大量需要“进口替代”政策保护才能生存的利益团体(Bardhan,1984)。在许多国家,这些团体的利益加上意识形态的误区妨碍了国家经济政策的改变,进口替代于是就成了路径依赖。但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却能在上世纪60年代进口替代问题凸显时不受利益团体的束缚,把进口替代经济转向面对市场的出口导向经济,使经济获得持续的发展。
上世纪60年代,除了东亚国家和地区外,其他一些国家(比如南斯拉夫和匈牙利)也搞出口导向经济,并且也给本国经济带来了繁荣,这繁荣一直持续到70年代的石油危机。石油危机给所有搞出口导向经济的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危害,但后果却截然不同。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石油危机断送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经济从此低迷,直到东欧共产党政权垮台。但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石油危机后低端产业难以维持的局面反而促使政府采取新的政策,把经济往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方向引导,造就了所谓的“东亚奇迹”。危机反成了契机。
东亚国家和地区能得益于完全不同的经济政策,其他地区国家的经济却有可能被任何经济政策伤害。东亚的国家和地区的成功表明了:一个国家采取的经济政策与这一国家的经济成功之间的关系其实没有这么紧密。关键在于当旧有经济政策的问题凸显时,一个国家是否有能力摆脱利益群体和意识形态的约束,推行新的经济政策,把挑战转化成机会。为什么东亚国家和地区能做到这一点而其他国家做不到呢?
埃文斯(evans,1995)认为这是因为东亚有着其他地区没有的一种既能把国家权力嵌入社会之中同时又有很强自主性的政府。埃文斯把这一现象称之为“嵌入式自主性”(embeddedautonomy)。嵌入式自主性是埃文斯在总结了许多前人工作后提出的概念(e.g.,Deyo,1987;Amsden,1989;Haggard,1990;wade,1990)。笔者要指出的是,这一概念直接指向了被埃文斯和其他西方学者所忽视的经济成功背后的历史原因,即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西方帝国主义和工业资本主义浪潮到来之前的国家建构历程。
三、中国古代国家建构的现代意义:历史建构的“强国家”传统是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
当殖民主义的尘埃落定后,在西方率先形成的“现代化”浪潮呈现出了两个清晰的面向:民族国家建构和工业资本主义发展(tilly,1992)。作为理想状态,民族国家中每一个成员效忠的对象应该是具有共同认同感的同胞及其共同认可的国家。民族国家建构包括许多方面,但是最为基础的就是建立一个不受传统精英和利益集团严重束缚的、能有效管理国家的文官官僚体制,和一个能被广泛接受的民族神话和认同感。许多后发展国家在独立后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家没有文官传统,以及人民缺乏一个共同的认同基础。在这样的国家中,中央政权不能插入地方社会,民众受到各种地方势力和分裂主义势力的操控,种族冲突
和种族清洗频发,连政治稳定都是奢望,谈何发展?许多后发展国家在独立后经济没有取得突破性发展,关键就是受民族国家建构滞后所累。但这对中国来说不是问题。
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国家建构历程中,以下三个发展不但具有里程碑性质,而且其后果对当今的经济发展和其他方方面面都仍具有重要影响:(1)西周以来形成的天命观和强烈的历史感;(2)战国到汉代逐渐形成的强国家传统、统一的象形文字以及以择优录取为理想的科层制;(3)宋朝后形成的儒教社会。
君主干得不好,天命就会转换,而旱灾、水灾、虫灾都是上天不满的信号。在当今中国,很少有人还相信天命,但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买红薯”已经成为政治文化。再加上中国人强烈的历史感,这就使得到了一定级别的官员不得不经常考虑“身后名”这一问题。因此,绩效始终是民众对官员的一个要求,是一方“父母官”需要面对的核心问题,也是国家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来源。
强国家传统和科层制削弱了国家之外其他政治团体的合法性和权力,促成了一套削藩、打击大族和控制兵权的历史经验和方法,使中国更容易避免在其他后发展国家常见的军人强权、部落、家族势力和利益集团坐大、政令不能下达、政局长期不稳的局面。象形文字给了不同的方言或地方语言一个统一的书写方法,便利了持有不同语言的人之间的交流,促进了中国文化在没有现代教育与通讯条件下的融合。
北宋伊始,科举规模扩大,不同口音、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都开始做起读书做官的美梦。同时,宗族和私学兴起,儒学化的通俗文本和文学作品大量涌现,儒家伦理逐渐深入民间社会和融入其他宗教。这些变化使得中国产生了一个儒学化的官僚士绅阶层,促进了国家力量向社会层面的渗透,加速了不同群体在文化和认同感上的大面积融合,形成了所谓的儒教社会。
宋朝后特别是明清以降,中国虽然没有发展成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但是已经接近蒂利(tilly,1992)所说的“民族的国家”(nationalstate),即一个由官僚集团统治的,并且精英具有同一核心文化认同感的国家。19世纪末,当中国在西方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出现了民族主义思潮后,传统精英的文化认同很容易就被改造成大众的民族认同。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严重困扰着其他国家的大规模的分裂运动、族群战争、族群清洗等问题在中国的核心人口地区从来就没有发生过。
简言之,悠久的国家建构(statebuilding)历程给中国带来了一个同质性较高的文化,一个自主性较强的讲绩效的官僚传统和一个地广人多的有力量抵御国际政治压力的国家。也就是说,中国在国家能力和文化认同建构方面要大大“领先”于其他后发展国家。因此,在西方帝国主义所带来的现代化浪潮的压力下,大多数后发展国家同时需要解决民族国家建构和发展资本主义两大问题,而中国却只需解决一个问题,即发展资本主义。中国所面临的现代化任务本来就比其他国家和地区要简单得多,因此经济成功不是奇迹,而是顺理成章。
读者千万不要从以上的分析中得出笔者是一个传统文化鼓吹者这样的结论。笔者虽不看好“五四”以来形成的一个鞭挞中国文化的传统,但也绝不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笔者在分析问题的时候秉持的是严格的中性立场。笔者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古代中国发达的国家建构历程并没有何“现代化”意义上的意义。中国发达的国家建构历程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与西方发生的“现代化”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当非西方国家在西方率先兴起的国家军事主义(statemilitarism)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压力下不得不被动地走上“现代化”道路时,中国的强国家传统作为一个历史的非期然后果(unintendedconsequence)就构成了当代经济成功的一个关键。传统中国从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落后国家”,但也不是什么“先进国家”。
笔者同时想强调,强国家传统并不是决定一个国家经济成功发展成功与否的唯一因素。如果强国家传统是决定经济成功发展唯一的因素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能解释如下现象:在中国影响下的整个东亚地区(乃至越南和新加坡)都有着悠久的国家建构历程,或者说这一地区在国家能力建构方面大大“领先”于其他后发展国家,且相对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中国是整个东亚文明的核心,有着更为深刻的国家建构历程,然而中国的经济飞跃却发生在邓小平时代,大大晚于日本,也晚于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要解释中国经济起飞滞后于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这一现象,我们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强国家传统的“暗面”。
四、中国经济起飞滞后于东亚其他地区的原因
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历史可以大致分成四个阶段:晚清、民国、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虽然中国经济在前三个阶段都有所发展,但与东亚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是个失败的案例。在前三次的失败中,民国时期失败的原因比较复杂。毕竟,民国有一个沿海地区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改革开放前,中国绝大多数民用“名牌产品”,比如三五牌台钟、永久牌自行车、牛头牌门锁、培罗蒙西服、五洲肥皂、金星金笔、三枪牌内衣、414毛巾,都是那个时期民族工业的产物。假以机会,难说民国时期中国经济不会出现重大突破。但中国在1937年后经历了几乎是整整12年的战争,丧失了经济全面发展的可能。
在晚清和毛泽东时代,中国都获得过一段较为稳定的时期,都有经济大发展的可能,但都错失了机会。失败的原因很复杂,其中,强大的国家力量是主要因素。
今天讲中国近代史一般会从1840年满清在鸦片战争中被战败算起。事实上,在当时的统治者眼里,鸦片战争只不过是大清经历过的大大小小的边境挫折中无足轻重的一次失利而已,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历史意义。即便是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和火烧圆明园这样的事件也没有完全挫败满清统治精英强大的文化优越感,激发他们作出根本性的反思。
从1864年太平天国灭亡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满清有过整整30年的相对平稳期。在此期间,满清对内陆边疆和西部边疆的控制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满清在这一阶段却只进行了被称为“洋务运动”的极其有限的改革。反倒是国力弱小的、处于旁观者位置的日本因为大清被西方战败产生了危机感,并在佩里率领美国军舰开进日本后危机感进一步加深。日本在1868年开始了明治维新,走上了君主立宪和资本主义的道路。显然,文化中心意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蒙住了满清统治者的双眼,延缓了改革的进程。在中国,与日本明治维新相似的改革直到甲午战败和义和团运动后才开始进行。改革使得满清的军事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满汉精英之间的矛盾却在改革的进程中变的越来越大,改革因此促进了满清政权的垮台。
中国在毛泽东时代也获得了一段本来应该是较为稳定的时期。国民党政权败走台湾后,中国政治迅速走向稳定,而且国家政权在“土改”和“镇反”后深入到了农村和城市的基层社会,国家力量变得空前强大。朝鲜战争花去了中国相当的财力,但这毕竟是在国门外的局部战争,而且时间经历比较短暂。在国内,战争的需求刺激了经济的复苏,而战争的胜利(至少是在当时国人的眼里)则大大提高了新政权的凝聚力。在一片大好形势下,中国的经济却走入了误区。
也许有人会说在冷战的国际形势下中国不可能搞邓小平时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在当时,苏联和东欧是中国的盟友,西方世界也并非铁板一块。再加上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如果中国在当时搞了市场经济,或者市场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国经济也许就会出现很快的发展,西方的有些国家也很有可能会在中国市场的吸引下向中国开放自己的市场。
然而事实是,中国的经济政策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后逐渐走向极端。先是公私合营,后是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把中国引向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些都是意识形态指导下的产物。在极左意识形态的指引下,中国不但对各种给予市场一定作用的经济理论进行批判,甚至把农民的“自留地”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把苏联式的讲有序平衡发展的计划经济看作是“保守”,把工业建设当作政治运动来搞。这些都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最后当然是文革。整个十年,全中国卷入了在意识形态引导下的派性争斗狂热,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简而言之,满清强大的“自主性”反而给了统治精英长期坚持保守意识形态的力量,从而延误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导致甲午战败和革命。同样,毛泽东时代国家强大的“自主性”也反而给了中国领导长期坚持极左意识形态的力量,使得中国在极左道路上越走越远。国家的强大反而给意识形态长期误导中国提供了土壤。
十年“文革”后,传统中国的意识形态已经被革命洪流摧毁,极左意识形态也因为已经把国民搞得民不聊生而失去了市场。中国是在几乎失去了任何意识形态资源的情况下才开始回归现实,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放弃了“顶层设计”的幻想,采取“摸着石头过河”的态度,以实用的精神来对待经济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飞跃发生在邓小平时代,晚于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原因。
总之,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出现了突破性发展是理所应当,而不是奇迹。但是,如果这一地区某一国家的经济未能发生突破性的发展(比如像今天的朝鲜),那就需要做出特别解释了。
五、中国绝不能被任何一种“理论”忽悠
从历史经验和教训来看,中国必须避免意识形态陷阱,防止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来绑架现实政治。一个正常的社会必须有学术和思想自由。“顶层设计”、“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大国崛起”、“普世价值”、“儒学复兴”、“后三十年是前三十年的继续”、“中国模型”、“北京共识”等等提法作为学术观点都没有问题。不同观点反复争论才能使国人走向成熟,并且争论各方所揭示不同的社会问题和反映的社会力量也可以成为国家在某些方面政策的基础。
但是在重大国策层面上,中国绝不能被任何一种“理论”忽悠。比如,笔者很赞同国内严肃左派学者的有些观点和分析,却强调中国必须长期防左。这是因为笔者深知如下政治学原理的重要性:一个政党更容易被与该政党原有意识形态倾向一致的政治正确话语所绑架。政治正确背后垃圾必多;当政治正确与个人利益能相结合时,背后隐藏的垃圾就更多。因此,左派政党要防左,右派政党要防右,自由主义政党要防范自由主义,宗教政党要防范原教旨主义,有很强民族主义倾向的政党要防范民族主义。这就是邓小平“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思想背后的政治智慧。
邓小平的“防左”思想和“摸石子过河”思想是中国的财富。只有坚持这两点,中国才能避免意识形态的陷阱,才能在经济上取得进一步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