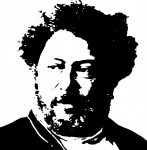崔健(中)
2.3崔健歌词的后现代主义诗艺特征

崔健的歌词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较多。就诗艺特征而言,应该归于先锋派诗歌一类。“先锋派”诗歌也被人称为“后现代主义”诗歌,是继“朦胧诗”与“寻根诗”之后出现的一种诗歌现象。以韩东、于坚等为代表人物。“朦胧诗”以象征、意象等手法表达主观情绪与伸张人性;“寻根诗”把诗歌推向民族的文化历史,试图在“天人合一、“人神合一的古文化境界中找回人们的“生命冲动”与“英雄精神”:而“先锋派”诗作则一反常调,把诗歌拉回到当代人的生活现象与实际存在中来。他们主张诗歌与“生命”联系,认为“诗到语言为止”,从而显示出“反文化”、“反意象”、“反英雄”的诗歌倾向。而韩东的诗,带有一种哲理味,严密、细致、反复说明,语言则平淡无味。
“《山民》是韩东转型时期的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一首冷色调抒情诗。诗人借“山民”这一形象,表达了对民族命运和人生命运的深切咏叹和思考……由此便引出了第三代诗歌的基本母题:生命意识。生命的原色和本真的存在状态,是韩东也是第三代诗人执意还原和呈现的本体”。在崔健的歌词文本中,《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象一把刀子》、《混子》等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韩东的另一部诗作《有关大雁塔》表面上看似乎仅仅是除去和消解大雁塔的历史、文化属性而返回事物,然而本质上依然返回到了生命”。让我们再看看《让我睡个好觉》这一文本:“别管我为什么名叫卢沟桥,别怪我对你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卢沟桥作为中华民族反抗史的重要标志,其历史影响和历史意义是众所周知的,但卢沟桥本身认为自己并没有那么复杂,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接着“听够了人们哭,听够了人们笑,受够了马车花轿汽车和炮,让我听见水声听见鸟叫,让我舒舒服服睡个好觉”文本中作为主体的卢沟桥,战争和经济都不需要,它需要的是山清水秀的环境和“舒舒服服的睡觉”,它要回到桥的本身最初的生活状态,返回生命的本真。这里作者把卢沟桥的历史、政治、以及文化属性一一消解掉了。而这种“主张诗歌与?生命’联系”以及“反文化”、“反意象”、“反英雄”的风格,也正是“先锋派诗歌”的主要特征。
诗歌语言的口语化色彩是崔健歌词与“先锋派诗歌”另一共同之处。《假行僧》“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假如你看我有点累,就请你给我倒碗水,假如你已经爱上我,就请你吻我的嘴里”。这些口语化的歌词以及后来的Rap(说唱)风格的歌词无不“自然亲切,透视出去掉伪饰之后的生命的本色”。
由此,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处于西方同一时代起源的摇滚乐和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某些文化主张上是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的。崔健的歌词具有后现代诗歌的诗艺特征也就不足为奇了。
3崔健歌词的社会文化内蕴
3.1时代的产物
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和国门的洞开,人们一下子意识到了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所存在在的巨大差异。落后就要挨打的前车之鉴,十年内乱之后的痛定思痛,使人们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的怀疑;现代化的诱惑、富国强民的梦想又使人们不得不对西方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于是,新一轮的文化概念、科学技术的引进开始运作,激进主义的情绪开始浅滋暗长,种种社会问题也淤积起来并吁请着解决。1986年,邓小平把改革的目标从经济体制推进到了政治体制,文化热也在这一年掀起了高潮以致被学术界命名为“文化年”。在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中,人们发现自己除了被刺激和唤醒了渴望、焦灼、愤怒、无奈等等情绪外,却原来一无所有。这种物质与精神上的次贫感与彷徨、苦闷、失落的时代情绪给人们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抑,人们嘴需获得一种合理合法的渠道,把这种情绪释放出来。当听惯了革命歌曲、主旋律音乐和传统民歌的中国听众,看到摇滚乐放浪不羁的演出形象,声嘶力竭的演唱风格,震撼人心的旋律和节奏时,无一不产生一种视听感官上的冲击力和震惊效果。崔健带着他那首苍凉激越的《一无所有》和国人一起喊出了压抑已久的心声,喊出了对生命本真严肃的思考。
前文我们说过,摇滚乐的出现,始终伴随着主流思想和主流文化的压制。这种情况在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就是在这样的压制之下,崔健的作品风格日趋鲜明、思想内蕴愈发深刻。崔健作品的反叛形象也由此建立。现在看来,他的反叛形象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一方面应该归因于他那种“不停地走”的执着与顽强,一方面也归因于80年代那种特殊的社会氛围和文化氛围。80年代是个理想主义情怀流行的时代、启蒙主义姿态风靡的时代,同时也是文化反抗情绪极易被催生的时代。由于人们普遍有一种参与社会改造社会的热情,介入现实、批评现实的冲动。由于主流意思形态又总是把这种热情和冲动阐释和误读为洪水猛兽,所以文化精英产生出来的精英文化,便老是与主流文化处于一种或暗中较量或公开对峙的状态,文化反抗情绪也极易产生和蔓延。在崔健的后期作品中,尽管反叛性有所减弱,但作为一个时代极其影响力的人物,他的作品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3.2介入现实、批评现实
摇滚乐自诞生之际起就与时代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的,如果说早期的摇滚乐还只是青春期骚动的结果,那么60年代的摇滚乐就俨然充当起了社会责任承担者的角色。特别是中国的摇滚乐出现在一个政治、思想、文化的转型时期,一方面要反思那个人性压抑,思想专制的时期,另一方面还要面对各种思潮的影响和各种利益的诱惑。在这个转型时期的文化大潮里,所有的艺术家都在思考、都在行动。“我不相信一个艺术家是为了下一代人活着,实际上艺术永远不可能与平行于自己的时代脱离,也没有这种愿望。摇滚乐恰恰更直接一些,直接得已经不能算是艺术,它以第一速度,脑筋里不转弯了,尽可能最快地形成表达”。崔健在这里毫不掩饰他的作品对时代的关注和思考。因此,当一代因体制变革、因传统的断裂而产生无所依凭之感的人正在迷茫的时候,崔健用他敏锐的洞察力捕捉到了“失去传统之后的荒凉,荒凉中的自由,以及自由中的追求”,于是才有《一无所有》里的呐喊“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这时,崔健的音乐不再是生活的饰品,歌唱也不再是纯粹的表达,而是力图成为现实和生活最本真的揭示,成为真实的现实和生活的本身。
对传统和过去的反思,是崔健的作品对现实的切入点之一。对于生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对十年的“黑暗”一定有着切身的经历和体验,因此对这一时期的反思也就成为他早期作品的主旋律。《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干里,有的说没的做怎知不容易,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从小接受长征的教育,现在又踏上“新长征”征途。很明显地表达了“长征”这一传统的继承,但在新长征的征途上,我们该怎么走,还得自己去思考。在这个新的时期,“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是这一代人的真实处境,包括当时的国家应该怎么走,都是当时大家所迷惑的。因此每个人的首要使命就是要寻找自己精神上的根据地,这个根据地就是他真实的自我,因此要“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充满了对理想追求的坚定信念。歌曲的前半部分刻画的应该是一个追求理想,非常阳光的热血青年形象,但后半部分,作品的主旨就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藏一藏,躲一躲,心说别着急急……求求风,求求雨,快离我远去”这两句很明显是在隐识长征当时的狼狈情形,作者似乎想让大家知道,我们所了解的长征也许并不是现在的讲大道理的人说的那样伟大和英明。该怎样客观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因此也才有“怎样说,怎样做,才真正是自己”的疑问。对于这一观点,作者自己也曾经这样解释过“所有那些讲大道理的人,或有权有势的人,或那些每天生活在蜜罐里的人唱甜歌蜜曲的人,你大红大紫,我们摇滚乐就是要捶你这帮人”。如果说《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还只是对传统的怀疑,对历史的真实的质问的话,那么崔健后面的两张专辑就是对传统的尖锐批评了,其中《盒子》以诙谐的语调讲述了一个关于理想的寓言“我的理想是那个,那个旗子包着的盒子,盒子里装的是什么,人们从来没见过”当我们所接受的“忠于”式教育的时候,我们的理想就在红旗指引的方向,但那前面是什么,我们从来没见过。当你要为了理想而奋斗的时候,它是那么的“乌托邦”,就象一个美丽的肥皂泡在前方飘荡。这注定是一个美丽的“传说”,一个悲剧式的结果。“骄傲的胜利者最有力量,他一屁股地坐在那盒子上……可是我的身体在这呢,被这带血的旗子和腿挡着”。理想应该是或崇高或伟大或美好的,但现在却被胜利者用“屁股”坐着,“我们”的处境就可见一般了。而且就在我以为我到达了理想的彼岸的时候,却发现“还是没找到我要的”。而且是“突然我的理想在叫掰它不是来自前方而是来自后面”。当我们沿着“胜利者”指引的方向前进的时候,竟然发现那是虚无缥缈的。作者用一个荒诞的故事,用无情嘲弄的语言,表达了一个严酷的现实,刻画了一个人性被压抑,理想被“设计”,“没有自我、没有光明”的思想者、探索者的形象。表达了处在“被压抑”、“被设计”的生存环境里的思想者的迷惘和反抗。
“快让我哭,快让我笑。”是因为你已经没有可以哭笑的能力了,才导致没有感觉。如果这部作品还只是一种隐晦的描写和述说的话,那么在《解决》这张专辑里就有对麻木更直接、更深刻的宣战了。在《像一把刀子》里,崔健唱到:“手中的吉它就像一把刀子,它要割下我的脸皮,只剩下张嘴”为什么用“吉他”,因为崔健作为一个摇滚乐的艺术家,他只能用他手中的武器来改变他所面临的社会。这就像鲁迅只能用手中的笔去改变社会一样。为什么要割下“脸皮”,因为脸皮是最常见的、最容易伪装的地方,当然这里的“脸皮”只是一个象征所指,更应该关注的是人们内心的麻木,所以才有后面的“这时我的心就像一把刀子,它要穿过你的嘴,去吻你的肺”。只有当对社会的麻木深感切肤之痛时,才会有如此强烈的改变社会的愿望,也才有对麻木的如此无情地鞭鞑。
我们身边麻木的人表现得也许并不那么明显,但我们身边甚至我们自己凑合着过的人却很多,只是谁都没明白自己真正的处境。崔健就真实地记述了这样一群社会的《混子》:他们没有经历过社会的磨难“我们没吃过什么苦也没享过什么福”;也怕吃苦“真要是吃点苦我准会哭鼻子”;自以为有本事但“说起严肃的话来总是结巴兜圈子”;看不到未来“若要问我下一代会是个什么样子,那我就不客气地跟你说,我管得了那么多吗?”;而且没有理想“新的时代到了,再也没人闹了,你说所有人的理想已被时代冲掉了”。当这种“白天出门忙活晚上出门转悠,碰见熟人打招呼,怎么样?嗨,凑合。”这样的人普遍存在于我们身边的时候,一个热爱生活、一个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人,就不得不站出来振臂高呼了:“我爱这儿的人民,我爱这儿的土地,这跟我受的传统教育没什么关系,我恨这个气氛,我恨这种感觉,我恨我生活除了‘凑合’没别的目的”。作为一个思想者,崔健一直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冷静的观察和思考着社会的种种弊端。他就像一个医生一样,一直在给我们诊断出很多问题。当然要求一个艺术家去解决社会问题恐怕是不现实的,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从现在开始,每天少说一句谎话,到一百天的就是一场革命”。此外还有:为精神价值的缺失而痛心疾首的《九十年代》、反映生存状态缺乏生命力的《春节》、当今非常流行的《网络处男》、有反映农村问题,痛斥城市人的劣根性的《农村包围城市》等。
对民族命运的关注,是崔健的作品对现实的切入点之三。这一点在他的他的第5张专辑《给你一点颜色》里表现得格外突出。在还没听到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已经听到了对它的很多评论:一是反对其在音乐风格上的改变,二是反对其反叛精神的丧失。但当我仔细的听过几遍之后,我才觉得错的应该是那些随便发表评论的人。前文我们也讲到过,90年代后,西方的摇滚乐已经不知道该走向哪里了。作为中国摇滚乐的旗手,崔健也一直在尝试着进行改变,探索着前进。因此这张专辑摇滚乐的风格已经减弱了,以Rap音乐为主。音乐表现上少了些许抗争的呐喊,多了几分中年的深刻和成熟。文化上在承接以前的思想的同时,多了一份对民族命运的关注。在解读《超越那一天》这一文本的时候,我们不得不首先了解它的创作背景。否则,对这部作品将有完全不同的解读,尽管另外的解读方式和结果也许没错。这张专辑于2005年3月发行,但这张专辑的大部分作品都完成于2003年前,其中《超越那一天》还是在1997年为纪念香港回归所作。但把它放至现在和台湾问题联系起来也许更加紧密。“妈妈有一天突然回来站着,盯着我半天然后跟我说,说我有个亲生的妹妹还活着”文本中的“妈妈”是我们共同的“妈妈”。“你说有一天她将永远的回来”表达了统一祖国的坚定信心。“我终于找到了答案,你为何如此冷酷,为何对我如此的严格,因为你想让我超过那个伤害你的人”。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这么多年会遭受那么多的耻辱和委屈。“我发现了一个潜在的危险,就是越长时间的误解将带来,越出乎意料的演变”,这里崔健是一个忧国忧民的民族主义者,因为他担心香港或者台湾问题拖得越久,就越难以解决。尽管我和“妈妈”之间也有矛盾,但在民族统一的问题上,我和“妈妈”还是具有高度一致的态度。
崔健这样描述过他的摇滚乐:“我的摇滚乐表达的是一种社会所需要的思考、一种理性,在你最顺的时候,在你最不顺、最萧条的时候,这个社会总是需要一群人理智地看待它,这种看待是黑色的,它诚实地说出问题,让你觉得社会很有意思,帮助你有所发现,但并不是为了逗你笑就隔鼓你……”摇滚乐反映人类情绪的极端敏感和社会生活的高度真实。也正是这个特征,使摇滚与周围通俗音乐的流行狠狠地划清了界限。纵观近半个世纪的摇滚乐历史,摇滚精神是“争自由、要革命、反抗上帝、蔑视权贵、嘲弄假道德……”,一句话,摇滚精神就是“RockandRoll”,就是“乐与怒”。这种摇滚精神的所在,也是摇滚乐赖以生存的基础。崔健的歌词也正是循着这条艰难而崎岖的道路在前行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