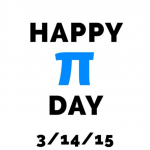人生中的小哥哥陪伴我们长大
小时候我经常希望有个哥哥,带我上学放学给我买零食,下雨时带伞接我天冷时送防寒衣物给我,我被人欺负他义无反顾的冲上去替我报仇,我难过他买胖胖的熊仔哄我开心,我失恋他去收拾甩我的男生。

哥哥(篇一)
出生在河北省南和县大会塔村的我,8岁就离开了河北老家独自在外闯,能有现在像童话一样的经历,或许只能用“傻人有傻福”来形容。生命中遇到贵人和机遇是我必须承认的,但“傻福”背后挂满的泪花,也许只有我和哥哥才看得到。
老实说,我从小就羡慕哥哥。哥哥是家里的老大,比我大4岁,什么都是他用过的才轮到我用;他很会读书,做起农活体力又比我强,父母都更喜欢他。有时我甚至猜想,我8岁向父母提出要去嵩山少林寺做俗家弟子学武术,父母居然答应了,也许就是因为家里有哥哥而他们对我并不太在意。
当然,父母同意年幼的我去少林寺,一方面是家里穷,那时家里只有6亩地,要供哥哥、姐姐和我读书不容易;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原因是,8岁的我已经认准自己笃定像李连杰一样会武功,能拍电影。
家里人中,哥哥最舍不得我走。他以为,我去学武功是因为总被村里的孩子们打想报仇呢。他就一个劲向我保证,以后一定好好保护我,不让我受欺负!但对“拍电影”的执拗,让我最终还是去了少林寺,一待六年多。
在少林寺学武非常艰苦。几年里,我只有两次在过年时回过家,父母都没来少林寺看过我,只有哥哥隔年暑假会来陪我处处。每次来回的路费,就是哥哥攒上一年多的零用钱。
因为父母不识字,我给家里写的信都是哥哥给我回复。记得有一次,我给家里寄了张自己剃光头、穿着僧人武服的照片。两星期后,我收到哥哥的回信。信里,哥哥画了一张父母、哥哥和姐姐站在家里麦田边的“全家福”。我知道因为家里穷,哥哥没法让想家的我得到“全家福”照片,就费心思地画这么一张给我。看着“全家福”里一家人甜甜的笑靥,我却大哭了一场。
后来,在北京“漂”了两年多,我才接到第一部主演电影《盲井》。我往家里打电话时,哥哥十分“愤怒”地吼道:“你这些年跑到哪去了,一个电话也不来,以为你死了!”哥哥说完,我们哥俩辛酸地号啕起来……
2003年,我凭借在《盲井》中农民矿工的本色演出居然获得了第40届金马电影节最佳新人奖!我把奖杯带回村子时,哥哥幸福地掂着“金马”说:“宝强真是傻人有傻福!”可拿到这个大奖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没人找我拍戏,只能演武行和替身,我灰心极了。哥哥劝慰我:“你得了奖总会有人看到的,只是电话还没打来!”
哥哥说对了。又过了两个月后,我接到冯小刚导演的电话:他就是通过朋友推荐看了《盲井》,决定选我来演《天下无贼》中的“傻根”的。从此,我的事业渐渐打开了局面!
随着片约增多,我的工作日益繁重起来,生活更没规律了。在老家一家建材公司做会计的哥哥为了照顾我,放弃了稳定的工作和与嫂子团聚的生活,来到北京。其实我有自己的公司和经纪人,哥哥来我身边,就是默默无闻地做个“勤务兵”。
拍完《士兵突击》从云南回到北京后,我曾一度很怅然。这部戏无论是时间和精力,是我演戏以来投入最多的,比如:有场拍和战友在水里扛枪的戏,我差点被淹死,我的手和腰也因演这部戏受了伤。但我心里还是没底,担心这部连女演员都没有的戏不被观众认可。
一回到北京,哥哥就陪我看没经剪辑的录像带,看着看着他就哭了,他跟我说:“许三多的成长故事和你真像,真实的故事一定会受欢迎的!”
现在,一路有着“傻福”相伴的我成了一名“草根偶像”,哥哥不断提醒我,永远不能泯灭“草根的心”。去年农忙,他还拉着我回老家收麦子。我们哥俩在地里割着金灿灿的麦子,哥哥扬起汗涔涔的笑脸说:“宝强的事业也到了丰收年!”我会心笑了,哥哥一直是我事业麦田的细心守望者呀!
哥哥(篇二)
1977年母亲病危时,我坐在病床边,握着母亲的手,问母亲还有什么要嘱咐我的。
母亲望着我,眼角淌下泪来。母亲说:“我真希望你哥跟我一块儿死,那他就不会拖累你了……”
我心大恸,内疚极了,俯身对母亲耳语:“妈妈放心,我一定照顾好哥哥,绝不会让他一个人待在精神病院里……”
当天午夜,母亲走了。
办完母亲丧事的第二天,我住进一家宾馆,让四弟将哥哥从精神病院接回来。哥哥一见我,高兴得像傻小孩似的笑了,他说:“二弟,我好想你。”
算来,我竟20余年没见过哥哥了,而他却一眼就认出了我。
我不禁拥抱住他,一时泪如泉涌,心里连说:“哥哥,对不起,对不起……”
我帮哥哥洗了澡,陪他吃了饭,与他在宾馆住了一夜。哥哥以为他从此自由了,而我只能实话实说:“现在还不行,但我一定会尽快将你接到北京去。”
一返回北京,我就动用轻易不敢用的存款,在北京郊区买了房子,简易装修,添置家具。半年后,我将哥哥接到了北京,并动员邻家的一个弟弟二小一块儿来了。二小也是返城知青,居无定所,也没工作。由他来照顾哥哥,我给他开一份工资,可谓一举两得;他对哥哥很有感情,由他来替我照顾哥哥,我放心。
那三年里,哥哥生活得挺幸福,二小也挺知足,他们居然都胖了。我每星期去看他们,一块儿做饭、吃饭、散步、下棋,有时还一块儿唱歌……
但好景不长,二小回哈尔滨探望他的兄妹,一天不慎从高处跌下,不幸身亡。这噩耗使我伤心了好多天,我只好向单位请了假,亲自照看哥哥。
我对哥哥说:“哥,二小不能回来照顾你了,他成家了……”
哥哥愣怔良久,竟说:“好事。他也该成家了,咱们应该祝贺他,你寄一份礼给他吧。”
我说:“照办。但是,看来你又得住院了。”
哥哥说:“我明白。”
那年,哥哥快60岁了。他的头脑、话语和行动越来越迟钝,但没有任何具有暴力倾向的表现,相反,倒是每每流露出自卑来。
我说:“哥,你放心,等我退休了,咱俩一块儿生活。”
哥哥说:“我听你的。”
哥哥在北京先后住过几家精神病院,有私立的,也有公立的。现在住的这一所医院,据说是北京市各方面条件最好的。
前几天,我又去医院看他。天气晴好,我俩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我看着他喝酸奶,和他聊天。在我们眼前,几只野猫慵懒地横倒竖卧。
我问:“哥,你当年为什么非上大学不可?”
哥哥说:“那是一个童话。”
我又问:“为什么是童话?”
哥哥说:“妈妈认为只有那样,才能更好地改变咱们家的穷日子。妈妈编那个童话,我努力实现那个童话。当年,我曾下过决心,不看着几个弟弟妹妹都成家立业,我自己是绝不会结婚的……”
“我认为,我是你们的班长,我要替家里也替你们去做最难的事。当年,对于咱们家,有孩子考上大学是最难的事……可惜,我没完成班长的任务,我让爸爸妈妈和你们失望了……对不起……”
他看着我苦笑。原来哥哥也有过和我一样的想法。自从生病48年来,他第一次说了这么长的话。我心一疼,黯然无语,呆望着他,像呆望着另一个自己。
哥哥起身将塑料盒扔入垃圾桶,又坐下后,看着一只猫反问:“你跟我说的那件事,也是童话吧?”
“什么事?”我的心还在疼着。“就是,你保证过的,退休了要把我接出去,和我一起生活。”想来,那保证已是六七年前的事,不料哥哥始终记着。听他的话,也显然一直在盼着。
哥哥已老得很丑了。头发几乎掉光了,牙也不剩几颗了,背驼了,走路极慢,比许多六十八九岁的人显得老多了。而他当年,可是个一身书卷气、儒雅清秀的青年,从高中到大学,追求他的女生很多。
我心又是一疼。
我早已能淡定地正视自己的年纪,但对哥哥的迅速老去,却是不怎么容易接受的,甚至有几分悸恐、恓惶,正如当年从心理上排斥父亲和母亲无可奈何地老去一样。
“你忘了吗?”哥哥又问,目光迟滞地望着我。
我赶紧说:“没忘,哥你还要再耐心等上两三年。”
“我有耐心。”他信赖地笑了,话说得极自信。随后,目光望向远处。
其实,我晚年的打算从不曾改变——更老的我,与老态龙钟的哥哥相伴着走向人生的终点,在我看来,倒也别有一种圆满滋味在心头。
网()
站在时光尽头的你(篇三)
只因你曾许我将来,我便甘心,荒芜了现在。
——摇光
开阳哥哥:
见信如晤。不知道你看到我写下这样开头的时候会不会笑我,可是我周围的人都是这么写的,我不过是学来的而已啊。要是你也到了这个奇怪的世界,那你一定会明白的。开阳哥哥,你好不好呢?不知道这个世界上会不会有人相信两个私奔的星星的故事,但那其实又有什么关系呢?
开阳哥哥,你一定不知道我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掉进了一个小女孩即将出世的身体,我和她谈判了很久,她才愿意让自己的身体带着我的灵魂出生,以至于后来她晚生了好多天。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最先看到的不是你,却是清光姐姐。哦,对了,这个世界上的人们管清光姐姐叫月亮。我第一次离这么远看我们生活过的天空,和安详温婉的清光姐姐。一切都很美好,除了你不在我身边。
这个世界的人们好像总是会被很多东西“绑架”。不知道你听到这个词语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他们追求很多东西,比如和谐,比如爱,等等的。所以很多人会为了爱而去做一些事情,而去奋斗。比如说吧,就像玄武伯伯觉得挣好多钱,买好多衣服,住好大的房子这样的生活才会好,所以他就要求北辰哥哥要达到他的要求,而北辰哥哥又很爱自己的父亲,所以他就会很辛苦地去做这些事情。而他自己并不知道他是不是喜欢,他只是去做就好了。还比如说吧,玉衡哥哥喜欢到处走,他想要去与我们隔了十万万光年的太微宫,可是朱雀阿姨舍不得他去,因为有可能他会回不来,而朱雀阿姨还等着他来照顾,所以玉衡哥哥就哪里也去不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他们被爱,或者另外一些标准或者规则给绑架了?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我凭什么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我要等你找到我。所以即使有时候觉得这个世界不可理喻,会觉得想要摆脱我所认为的牵绊(别人认为的责任),你没有来之前,我不会轻举妄动,我会乖乖地,等着你带我去另一个世界。
我总是很想念我们以前在银河里面去玩的日子,我也很喜欢我们居住了好几万年的天空,因为大家都那么安详,天枢哥哥和天璇姐姐总是那么温和,还有我们慈祥的玄武伯伯和朱雀阿姨。我们只要发光就好了,不用为了很多事情而担忧。那个时候,我们一起手拉手,就会变成一把勺子,你总是站在我前面,握着我的手那么温暖而坚定,而那时候的我,站在勺柄的最末端。很多时候我们会去逗另一边最遥远的北辰哥哥玩。等我到了这个世界之后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的人们管我们叫北斗七星,管北辰哥哥叫北极星。以前的时候我喜欢站在天上看下面,黑乎乎的,有时候会有亮的光,而现在,我喜欢在晚上抬头看,因为那就像回家一样。天气特别好的晚上,我还会看到我们七个人依旧手拉手的样子,然后一个人傻笑。很多时候也会看见北辰哥哥依旧一个人孤孤单单地挂在天上。那个时候我就会想念你。
今天我骑着车,穿过一个学校的校园,落下来的黄叶随着我一起往前飞。那个时候太阳还是红色的,天很蓝。我穿着红色的衣服沉默着穿过那个美丽校园静谧的清晨。黄叶落了一地,期间我看到一群蚂蚁,然后我停下来给他们让路。也会有风忽然吹过来,灌满了我红色的风衣,我觉得我快要飘起来了。我很想念你。我还记得当离开我们长久以来居住的天空的时候,强大的冲击力和摩擦力让我觉得很难受,是你紧紧抱着我不让我摔出去,我还记得你紧蹙的眉头,还记得你心疼的眼神,还记得你坚实的臂膀,可是我醒过来的时候你不在。你说要带我去走很远很远的路,带我我做灿烂的流星,带我去看美丽的夜色,看曾经天上的我们。
你说要带我喂马砍柴周游世界,你说要和我听风看雨垂钓赏花,你说要带我拾阶而下涉水还乡,你说要带我去那遥不可及的将来,你说……可是现在,我徒步走了这么许久,依旧没有找到你。
真的有点害怕站在将来的尽头还是看不到你……
兄长(篇四)
我的兄长大我6岁,今年已经68周岁了。从20岁起,他一大半的岁月是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他是那么渴望精神病院以外的自由,而只有我是一个退休之人了,他才会有自由。我祈祷他起码再活10年,不病不瘫地再活10年。我也祈祷上苍眷顾于我,使我再有10年的无病岁月。只有在这两个前提之下,他才能过上10年左右精神病院以外的较自由的生活。对于一个48年中的大部分岁月是在精神病院中度过的,并且至今还被软禁在精神病院里的人,我认为我的乞求毫不过分。如果有上帝、佛祖或其他神明,我愿与诸神达成约定:假使我的乞求被恩准了,哪怕在我的兄长离开人世的第二天,我的生命就必须结束,那我也宁愿,绝不后悔!
在我头脑中,我与兄长之间的亲情记忆就一件事:大约是我三四岁那一年,我大病了一场,高烧。母亲后来是这么说的。我却只记得这样的情形——某天傍晚我躺在床上,对坐在床边心疼地看着我的母亲说我想吃蛋糕。之前我在过春节时吃到过一块,觉得是世上最好吃的东西。外边下着瓢泼暴雨,母亲保证说雨一停,就让我哥去为我买两块。当年,在街头的小铺子里,点心乃至糖果,也是可以论块买的。我却哭了起来,闹着说立刻就要吃到。当年10来岁的哥哥,于是脱了鞋、上衣和裤子,只穿裤衩,戴上一顶破草帽,自告奋勇,表示愿意冒雨去为我买回来。母亲被我哭闹得无奈,给了哥哥一角几分钱,于心不忍地看着哥哥冒雨冲出了家门。外边又是闪电又是惊雷的,母亲表现得很不安,不时起身走到窗前往外望。我觉得似乎过了挺长的钟点哥哥才回来,他进家门时的样子特滑稽,一手将破草帽紧拢胸前,一手拽着裤衩的上边。母亲问他买到没有。他哭了,说第一家铺子没有蛋糕,只有长白糕,第二家铺子也是,跑到了第三家铺子才买到的。说着,哭着,弯了腰,使草帽与胸口分开,原来两块用纸包着的蛋糕在帽兜里。那时刻他不是像什么落汤鸡,而是像一条刚脱离了河水的娃娃鱼。那时刻他也有点儿像在变戏法,是被强迫着变出蛋糕来的,变是终归变出来了两块,但却委实变得太不容易了,所以哭。大约因为觉得自己笨。
母亲说:你可真死心眼儿,有长白糕就买长白糕嘛,何必多跑两家铺子非买到蛋糕不可呢?
他说:我弟要吃的是蛋糕,不是长白糕嘛!
还说,母亲给他的钱,买三块蛋糕是不够的,买两块还剩下几分钱,他自作主张,也为我买了两块酥糖……
妈你别批评我没经过你同意啊,我往家跑时都摔倒了……
我已经几顿没吃饭了,转眼就将蛋糕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
而母亲却发现,哥哥的胳膊肘、膝盖破皮了,正滴着血。当母亲替哥哥用盐水擦过了伤口,对我说也给你哥吃一块糖时,我连最后一块糖也嚼在嘴里了……
是的,我头脑中,只不过就保留了对这么一件事的记忆。某些时候我试图回忆起更多几件类似的事,却从没回忆起过第二件。每每我恨他时,当年他那种像娃娃鱼又像变戏法的少年的样子,就会逐渐清楚地浮现在我眼前。于是我内心的恨意也就逐渐地软化了,像北方人家从前的冻干粮,上锅一蒸,就暄腾了。只不过在我心里,热气是回忆产生的。
麦可多哥哥(篇五)
风从西北方向伸出众多大手,沟崖边的杂树被摸成了光杆子,一些枯黄的叶片带着极不顺畅的呻吟流浪在高原上。处于朝气蓬勃年龄段的麦可多,再也没有多余精力去关注初冬天气的此般巨变。在这个阳光微弱的午后,当我一声接一声呼唤时,气若游丝的麦可多凹陷进去的眼皮挣扎了一下又挣扎了一下,两条黑丝线一般的缝隙终于开启,我确切地感受到了他那像被黄油抛光的瞳孔,至少摄掠了我身体抑或脸庞的某些部分。我一边紧急向他更近距离靠拢一边慌乱阻止由他鼻孔不断流淌的汩汩鲜血。麦可多失血太多以至于像老牛一样倒伏而下没有什么力量支撑站立起来,他头朝外脚向里被家里唯一的土炕收留,但是炕坯炕塄以至脚地的一小部分几乎都沾染上了黑红黑红的液体。鲜血有极强的凝固性,不久就似胶一般粘住了麦可多业已褪掉本色且补丁摞补丁的贴身衬衣以及覆盖肢体的棉被铺陈炕席之上的毛毡,他那双绝望又杂有渴望成分的眼窝,如果不是我不停地擦拭恐怕早已被血液围困,他单薄得若白纸般的嘴皮似乎被何锐器扎刺,只是颤颤巍巍蠕动却不能打开。显而易见麦可多神智又出现了清晰,但是直到今天我也不能确认彼时彼刻是不是人们讲的那种回光返照,反正当时那对熟悉的眼睛一经放射出亮光,我即认定他的情况并非糟糕透顶并非不可救药也并非到了要向世人告别的地步,可不然麦可多头颅生硬地向左向右转动。麦可多大约希望瞅见什么呢?人或者物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我当时心生着急痛恨自己的无计可施无能为力。然而好景不长,麦可多的清醒伴随着他放弃观察而结束,大概他明确知悉眼面前唯有一个茕茕孑立的我时,眼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度闭合了。这是他有生以来最末一次看世界。他永远关上了心灵窗户。与此同时冥冥之中我黑暗而凌乱的脑际忽然闪现一抹敞亮,我对麦可多临终的寻寻觅觅如梦初醒,原来他那是寻梦的延续,他在等待一个年轻女性的出现。我们这个只有两位男孩存在的烂脏家庭未有属于本家女人走出走进打理里里外外,这是麦可多存储弥久的心事,他多么希望这个特别任务在这种特殊时刻由我这个刚刚荣任大学教师的人庄严完成。可是缘分未到的我形单影只的我让麦可多彻底失望了。我感到麦可多很生气后果很严重。所以在后来无数次面对麦可多孤独坟墓的日子,我后悔万端自责无限,总觉得不是疾病不是神魔不是老天爷,而是我这个被麦可多一手抓养成人却不曾有一点一滴回报的蠢弟麦可少一手酿成了他的少亡。
在我一岁麦可多十岁那年家里人口锐减至一半,我兄弟俩猝然成为孤儿。麦可多后来拿平静的语气给我讲述悲惨故事,我从中了解了之前我不知道的一切,而这空当与我能够记住事理的时间天然衔接。家破人亡的危难时刻,是麦可多用麦面荞面豆面玉米面糜子面等等杂七杂八的面糊糊把我这个皮包骨头的小老鼠救活。重担遽然而降,日月繁复生活还需继续,麦可多不得不成为生产队年龄最小的劳力,除过岁初年尾其余每一个白天都得出去挣工分,至于我这个累赘他无法携带生产队也不允许拖拽,放诸院子吧恐刮风恐下雨恐降雪恐日晒恐跌崖恐狼出没恐花鹁叼咬,麦可多为保险起见,为了安全打发无穷无尽的时光就把我关在屋子里。屋子里如夜如锅煤子如非洲土著居民的脸颊般漆黑。漆黑当中一面土炕就是我一整天的活动区域,盘桓在上吃喝拉撒兼及运动和静止,自由极受限制。怕我跌炕塄怕我翻栏槛怕我掉进大大深深的后锅,麦可多又效仿邻居的普遍做法用指头粗的线绳绑缚住我的腰际。线绳线绳细而长,线绳线绳不长眼,多少次又多少次我被线绳缠脖,一回再一回我从死神的紧紧钳制中脱逃。漆黑境界给予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在那些聚少离多的漫漫年月里,当与极快速做饭极快速照料我的麦可多短暂接触意识刚刚舒缓,我的心弦立马就又紧张,别离的恐惧逼仄得我不寒而栗,而当麦可多哄骗谩骂我进入绳套之际,当干涩的屋门吱吱喔喔声中关闭之际,当我双眼像被黑布蒙蔽身边毫无敞亮可寻之际,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肥猪挨刀子般歇斯底里。严酷的生活将麦可多驯化得心硬如铁,他只是象征性把我沟蛋子一拍俄而在肩膀处狠狠一推继之转身而出健步如飞。麦可多在重复这些动作的从头至尾,丝毫不曾犹豫不决于心不忍。囚徒般生活月月重月月年年复年年,直到我真切知晓怎样躲风避雨远离沟壑赶驱猛禽完全能够分辨利害冲突的年龄,麦可多才勉强同意将我解放出来。俗话说牙有咬舌头的时候更何况两个年龄相差较大的人,我和麦可多的矛盾常常不期而至。也不完全是我调皮捣蛋耍二杆子,其实麦可多给我灌汤汁时期我很顺从很听话,他让我张嘴我便开启上下嘴皮,他要我吞咽我则咕咕嘟嘟喉结蠕动。大约我被解开绳套不久就有些叛逆有些嚣张,当麦可多硬要我穿上磨脚把骨的一向子鞋时,我起初抵挡后来干脆拿鞋底砸他的头。虽然我知道此别扭物系因我母亲过世而哭白了头发的外婆所纳,外婆视力不好神智有时清楚有时模糊,她常常搞不妥当鞋子弯弯理应相对相应,却又时常察怜我们偷偷弄了布票把鞋子很快做成捎来。外婆操一双小脚,亲自走我家无异于一次长征。一直向西沿着国道走八九十里,再沿着省道走四五十里,穿过一个深深的大峡谷,爬上一个累死牛的黄土高坡,尔后下山往沟垴走至头,外婆即使如何慈悲怎么念想我们也跋涉不完这样漫长的路程,只能通过顺路的人不断捎带东西来表达柔情蜜意,但是鞋子这次经由了麦可多之手我就有理由找他的不是,麦可多被打了个鼻青脸肿,他通过以牙还牙方式坚决维护了外婆和他自己的尊严。错过初一错不过十五,我终于等得发泄不满的极佳机会,那天凌晨麦可多烧火时候兼干了别样事情,结果蒸出的玉面黄黄馍坚硬无比,一块块面砖头谁也啃不动,我悲从中来边向天堂的爹妈哭诉边像丢石块那样,容易地将馍馍撇向窑外。麦可多乍初惊诧后头委屈得泪流满面,他制止不了我的狂怒就看样学样胸脯起起伏伏叫爹娘,他甚至拉哭腔说日子难过得很受不了了不想活了。麦可多这一番话语让我吃了一惊,他如果轻生我有何方何能依靠谁人苟延残喘,惶恐里我慢慢收束哭声躲避槐树下枕只布鞋抽抽噎噎,任凭后来主动示好的麦可多轻声软语赔不是,我都端了脸闭着眼一言不发,即使再后来麦可多用筷子撬开我的嘴巴把酸汤面一口一口喂进去犹如我幼小的时候,我还是相当的苦大仇深威风凛凛。陇东老家的人把我如此对待麦可多的行为叫拧势,一般要持续一定的时日,立马缴械投降显得极没面子极没城府,我这次却绷不住脸面,终于有一天麦可多没话找话时我哑然失笑,麦可多也不失时机地回敬一阵笑,我奔向麦可多小拳头雨点一般暴打他的肩膀胸怀,麦可多喜出望外就势拥抱我轻轻拍打我的屁股和后背,他激动地说好了这下好了,我则趁机吓唬他说你可再不敢惹我了再不能讲死呀活呀没深没浅的话了,麦可多数十遍点头承诺,我们和好如初。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胜利。麦可多此后做事精细如巧妇,他蒸馍时把面发得很涨,他擀面时将面揉劲道,他炒菜时调盐刚合适,他几天之内变着花样做吃食,他一针一线缝缝补补。每每见此我就嘻嘻发笑,麦可多知道我因何而笑可是从来不去说破。
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