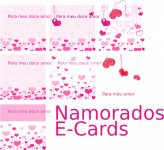披上袈裟那一天
“后来的我会做些什么呢?”,过去,我常常对着不算蔚蓝的天空跟那几片稀薄的白云发问。以各种可能的答案来猜测自己未来的命运,以思考来安抚那些四处冲撞的迷茫。可是那时的我依然不能判断出自己在迷茫什么,或者其实我无法深入地思考下去,因为那时的我更相信现实的裁决。直观,有效,任你挣扎叫喊的裁决。

看到自己曾经画出的字的形状,感觉有种小学生的幼稚。我想这并不代表那时的我开始恢复从前的澄澈。也许它仅仅是某种决定前的回光返照。现在我似乎依然能感觉到那时的自己正被某只神秘猫咪的目光锁定,它的耳朵紧紧地向后收起,四肢也开始出现轻微地骚动,显然它已经做好了捕食的准备。对于以往自己每一次可能的改变,我想我是有过这样的处境的。
此刻,当我跪在金黄色的蒲毯上,对着那些面目慈祥而尊贵的佛像双手合十,我依然在问自己“后来的我会做些什么?”。这样的追问在这种时候变得迫切。因为突然间很空洞的感觉铺天盖地地压过来,而我并没有任何迎接的准备。我不知道这是否说明自己其实尘缘未了,我也不知道这是否可以算作我为自己选择的一次新生。但是此刻,我只想得到一个答案将这空洞的感觉统统塞满。我觉得它们会在我身上裂开,渗出很多很多暗红色的血,那种死气沉沉地暗红,一点一点,笃定地蔓延,让人心灰意冷,然后窒息。可是我只能跪在那里,没有挣扎,也没有后悔。我早已无路可退。师傅娴熟地拿着剃刀操纵着我散开的头发,我似乎听到它们下落时拥挤的声响。一簇一簇,就那么轻飘飘地覆在我的右侧心房,一层又一层,那小小的位置。很痒很痒,因而感觉不到其他的疼。
起身,从凌乱的发丝上走开。头顶上已然多了几颗香灰留下来的灼热。所有的记忆似乎就通过这种机械式的仪式被浓缩,然后被封印进了那几颗模糊又分明的斑点里。开心的,不开心的,所有的。天气很清爽,整个人也很轻爽。天空依然不算湛蓝,云依然只有那么几朵。而我终于不再问,那个问题。
此前跟姐妹们讨论过自杀的方式,说:如果某一天可以为自己选择一个死法,我希望那个过程是迅捷的,并且可以无知无觉。于我而言,上吊,服毒,割腕或者跳楼的过程都未免太过于漫长,期间或许还有无法证实的反悔。相比之下,虞姬那般的死法似乎就比较合适。至于她到底割的是气管还是动脉,我已经忘了生物老师的说法。只知道电视上并没有出现血流如注的画面,只能推测割的是气管罢。可是究竟它是跟颈动脉和食道穿插交错,还是只是平行地毗邻而居,我还没有强烈的意愿去证实。死,分明是如此纠结的一件事,很多人却一而再,再而三,乐此不疲。她们都认为这难以理解。这也间接地杜绝了我自裁的可能。
佛说爱人,却常常令自己遭受苦难。从某种程度上理解,这种行为却是把自己归于非人的范畴。那么“众生相”“众生平等”呢?所谓的“代人受过”“舍身”之类,我也并不认为那是爱人的途径。佛与人,或者僧众与人,应该更像是一种父子关系,而非母子。不是任劳任怨,不是化解,而是引导,启发,教授。带着诸多蠢蠢欲动的疑问,在剃度后的几日里,功课之余我常常顶着脑袋上的那几颗新鲜的斑点勤奋地翻阅庵内的佛家经典,以求寻到答案。师傅对于我这般“虔诚而勤奋”的弟子甚是欣慰,大有日后授我衣钵之意。可是我依旧没有得到答案。
我认为自己并不具备出家人大彻大悟的天资。我只是个被道教化了的佛教徒,有着现代人界限不明的暧昧态度,并没有信仰。不过大而空的哲理倒是可以信口拈来,想来将来开悟众人定然不会辱没了师傅得道老尼的名号。可是,我始终开悟不了自己。在无可救药面前,除了超度佛也无能为力。
前年,我参加了好姐妹们的婚礼。花样繁多,实质一致的仪式:两个人的幸福,一群人的热闹。其实也并不是什么适合婚嫁的年份,只是大家都到了适合做这件事情的年纪。于是这么多人按部就班,开花结果。当然,除此之外还因为她们拥有爱,跟爱着彼此的人。而彼时的我,正拥有着在漫长岁月里也无法消融掉的爱意跟需要去关爱的人,还有一些零散的回忆,因为未曾被实现而固执地存在。总之,那是一种漫长而绝望的爱,在一个封闭的环形里流动,没有开始,也没有停止。因为没有出口,也就不存在消耗。只是它们的颜色因为这种滞留,终究还是被加进了时间元素。我开始沧老,我拥有着的爱也是。后来它们都变得很旧,很旧。
去年,我又听说了一场婚礼,后来也有一封请柬送到我的手上。戏剧化的安排让人有种历尽沧桑的错觉。我以为那个环形系统终于有了可以破碎的理由。然而,直到我在婚礼上跟随众人送上千篇一律的祝福的时候,它依旧没有碎裂的迹象。它只是在听到那句“祝你们永远幸福”的话之后,终于停止流动,然后那个空间被迅速胀满。不痛不痒,坚硬地卡在心脏的入口,任凭外面的血液冲撞,纹丝不动。
曾经幻想过很多美好的东西,人,情节,却唯独想象不出自己幸福的模样。这是个危险的信号,让人警惕而绝望。也曾认真地考虑过自己是否应该去谈一场恋爱,能够死去活来的那一种。可是,我一直无法开始恋爱,从很早的时候便是如此。并不是无法遇见一个真诚而优秀的人,而是我本能地相信自己不会幸福。很多人无法理解。那些已为人妇的姐妹却因为我而变得恨嫁。而恨嫁的人往往只想得到别人的好,而不去理会那些好是否被需要。我珍惜这种好,并且心存感激。但是我更加尊重,因而无法坦然接受。我知道我无法放弃自己的感受,因为有一种理想的态度在里面,越是执着,反而变得自私,无法做出妥协。之前,我就是这样不肯让爱自己的那些人有一点点好过。
于是,在所有好姐妹的婚礼之后,在那场婚礼之后,我开始计划出走,去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做一个新的人。最后却只是留下几封苍白而简短的邮件,然后关机,拔掉电话卡。就这样不负责任地走掉,不知道之后有多少人会气得跳脚,不知道会有多少人会因此而记恨我,不知道又有多少人会偶尔想念我。现在的我仍然无法知道。一些人或许会忘记我,而我,或许忘记所有人。
后来,在某一处对外开放的深山,我跪在金黄色的蒲毯上,对着那些表情雷同的佛像敬上三柱细香。然后,我有了一个师傅跟一个法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