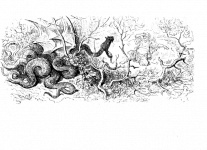一段旅程
编辑荐:旅程结束了,几分钟后,她就会看到她的家人在车站拥挤的人群中推开他们欢快的路。

当她躺在卧铺上,凝视着头顶上的阴影时,她脑子里涌动着车轮,把她越来越深地推到清醒而清醒的圈子里。那辆沉睡的汽车陷入了夜间的寂静之中.透过湿漉漉的窗玻璃,她看着突如其来的灯光,漫漫的黑暗.她不时地转过头,透过吊架上的开口,望着她丈夫在过道对面的窗帘.
她不安地想知道他是否想要什么,如果他打电话,她是否能听到他的声音。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的声音变得非常微弱,当她没有听见时,他感到很恼火。这种易怒,这种越来越孩子气的任性,似乎表现了他们之间难以察觉的隔阂。就像两张脸透过一张玻璃片互相看着一样,它们紧紧地在一起,几乎触碰到对方,但却听不见或感觉不到对方:他们之间的传导能力被打破了。至少,她有这种分离的感觉,她有时会想,她有时会从他补充他那句失败的话的表情中看出这一点。毫无疑问,这是她的错。她太健康了,不可能被疾病的无关之处所感动。她自责的温柔带着他的非理性的感觉:她有一种模糊的感觉,认为他无助的暴政是有目的。突如其来的变化使她感到毫无准备。一年前,他们的脉搏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指标;两人对一个永不枯竭的未来都有着同样的挥霍信心。现在,他们的精力已经步履蹒跚了:她的力量仍然领先于生活,抢占了无人认领的希望和活动区域,而他的力量却落在后面,徒劳地挣扎着赶超她。
当他们结婚时,她有如此多的生活负担需要弥补:她的日子就像粉刷过的教室一样光秃秃的,在那里,她把毫无营养的事实强加给不情愿的孩子。他的到来打破了环境的沉睡,扩大了现在,直到它成为最遥远的机会的外壳。但不知不觉地,地平线缩小了。生活对她怀恨在心:她绝不会被允许展开她的翅膀。
起初医生说,六周的温和空气会使他恢复正常;但当他回来时,这个保证被解释为当然包括在干燥的气候下的一个冬天。他们放弃了漂亮的房子,把结婚礼物和新家具藏起来,去了科罗拉多州。她从一开始就讨厌那里。没有人认识她,也没有人关心她,也没有人会怀疑她有多好的匹配,也没有人羡慕她的新衣服和名片,这对她来说仍然是个惊喜。他的病情还在恶化。她觉得自己被困难所困扰,逃避不了那么直接的性情。当然,她仍然爱着他,但他渐渐地、不确定地不再做他自己了。她结过婚的那个男人很强壮,很活跃,很有主见:那个男人,他的快乐在于清除生活中的物质障碍;但现在是她在保护她,他必须不受强求的影响,给他滴的水或他的牛肉汁,尽管天空正在落下来。病房里的例行公事使她迷惑不解;这种按时给药的方法,就像一些无法理解的宗教木乃伊一样,似乎是无精打采的。
有时候,当她本能地对他的处境产生怨恨时,她仍能在他的眼睛里发现他的旧我,因为他们在他软弱的浓重的媒介中摸索着彼此。但这些时刻已经变得罕见了。有时他把她吓了一跳:他那沉陷的无表情的脸似乎是一个陌生人的脸;他的声音微弱而嘶哑;他那薄薄的双唇微笑,不过是肌肉的收缩。她的手避开了他湿软的皮肤,因为他的皮肤已经失去了熟悉的粗糙的健康:她偷偷地盯着他,就像她可能看到了一只奇怪的动物。当她感到这是她所爱的男人时,她感到害怕;有几个小时,告诉他她所遭受的痛苦,似乎是她从恐惧中解脱出来的人。但总的来说,她对自己的看法比较宽容,反映出她可能和他在一起太久了,当他们再次在家的时候,她会有不同的感觉,她周围都是她那健壮而活泼的家庭。当医生们终于同意他回家时,她多么高兴啊!当然,她知道这个决定意味着什么;他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他要死了,但是他们用充满希望的欢快的话来掩饰事实,有时,在准备的喜悦中,她真的忘记了他们旅行的目的,于是急不可耐地提到了明年的计划。
离开的那一天终于来了。她有一种可怕的恐惧:他们永远也逃不掉;不知怎么的,在最后一刻,他会让她失望;医生们会保守他们惯用的背信弃义,但什么也没发生。他们驱车到车站,他被安置在一个座位上,膝盖上铺着一块地毯,背上放着一个垫子。她从窗户出去,向熟人挥手向她以前从未喜欢过的熟人挥动着毫无悔意的告别。
头二十四个小时过去了.他苏醒了一会儿,他向窗外望去,观察汽车的幽默,这使他感到好笑。第二天,他开始疲惫不堪,对那个满脸雀斑的孩子用口香糖块冷冷地瞪着他,感到很烦。她不得不向孩子的母亲解释,她的丈夫病得太重,不能被打扰:这位女士收到的一份声明显然得到了整个汽车的母性情感的支持.
那天晚上,他睡得不好,第二天早晨,他的体温吓到了她:她确信他的病情正在恶化。这一天过得很慢,不时地被旅行带来的小烦恼所打断。她看着他疲惫的脸,在它的收缩中追踪电车的每一次嘎嘎声和颠簸声,直到她自己的身体因同情的疲劳而震动。她也感觉到其他人也在注视着他,不安地徘徊在他和一双带着疑问的眼睛之间。那个满脸雀斑的孩子像只苍蝇似地围着他,糖果和图画书没能把她赶走,她把一条腿绕在另一条腿上,不动声色地看着他。搬运工在路过的时候,含糊其辞地提供帮助,这可能是由于慈善的乘客们感到“应该做点什么”而引起的;一个戴头盖帽的紧张的人听起来很担心对他妻子的健康可能产生的影响。
几个小时在沉闷的忙碌中缓缓前进。黄昏时分,她坐在他旁边,他把手放在她的身上。触碰使她大吃一惊。他似乎在遥远的地方给她打电话。她无可奈何地望着他,他的微笑像一种身体上的剧痛一样从她身上掠过。
“你很累吗?”她问。
“不,不太好。”
“我们马上就到。”
“是的,很快。”
“这次-明天-”
他点点头,他们默不作声地坐着。当她把他扶上床,爬上自己的卧铺时,她想让自己高兴起来,以为不到二十四小时他们就会到纽约来了。她的人都会在车站迎接她-她想象着他们那满脸焦急的圆脸正挤在人群中。她只希望他们不要太大声地告诉他,他看上去气色很好,很快就会好起来的:与痛苦长期接触所产生的微妙的同情使她意识到家庭感情中某种质地的粗糙。
突然,她觉得她听到了他的呼唤。她拉开窗帘听着。不,只是一个男人在车的另一头打鼾。他打呼噜的声音很油腻,好像是经过羊脂似的。她躺下试着睡觉.。她没听见他动吗?她开始颤抖.。沉默比任何声音都更让她害怕。他可能不能让她听到-他现在可能会给她打电话.是什么让她想到这些事的?这不过是人们所熟悉的一种倾向,那就是过度劳累的头脑把自己牢牢抓住在它的不祥预兆范围内最无法忍受的机会.她伸出头来听着,但她无法分辨他的呼吸和她周围的其他两对肺的呼吸。她很想起来看看他,但她知道这种冲动不过是她焦躁不安的发泄,而对打扰他的恐惧限制了她.他的窗帘不断地移动使她放心,她不知道为什么;她记得他曾祝她愉快地晚安;她再也无法忍受她的恐惧,这使她费尽力气把这些恐惧从她那听起来疲惫的身体中抹去。她转过身去睡觉。
她呆呆地坐起来,凝视着黎明。火车冲过一片光秃秃的小丘,挤在死气沉沉的天空下。看上去像是创造的第一天。汽车的空气很近,她推上窗户,让刺骨的风进来。然后她看了看她的手表:已经七点了,她周围的人很快就会激动起来。她穿上衣服,梳理着蓬乱的头发,悄悄地走进更衣室.当她洗脸和调整衣服时,她觉得更有希望了。对她来说,早晨不高兴总是很困难的。她的脸颊在粗糙的毛巾下燃烧得很好,她的太阳穴周围湿漉漉的头发扎成了强有力的向上卷须。她的每一寸土地都充满活力和弹性。十小时后他们就会回家了!
她走到她丈夫的铺位上:是时候让他喝一杯牛奶了。窗户的阴凉处落了下来,在罩着窗帘的围场的黄昏里,她只看到他躺在一边,脸离她很远。她靠在他身上,把窗帘拉上。当她这样做时,她摸了他的一只手。感觉很冷.。
她弯下腰,把手放在他的胳膊上,叫他的名字。他没有动。她又大声地说了起来;她抓住他的肩膀,轻轻地摇了摇。他一动不动地躺着。她又一次抓住了他的手,它像一只死东西一样,从她的跛行中滑落了下来。死东西?.。她喘不过气来。她一定看到他的脸了。她向前一靠,急忙缩手缩脚地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把他翻过来,那是一种令人作呕的不情愿的肉体。他的头往后一仰;他的脸看上去又小又光滑;他用稳重的眼睛注视着她。
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动不动地抱着他,他们互相望着。突然,她缩了回去:渴望尖叫、喊叫、飞离他,几乎压倒了她。但是一只强壮的手抓住了她。上帝啊!如果知道他死了,他们就会在下一站下车-
她在旅行中看到了一幕可怕的回忆,一位丈夫和妻子的孩子在火车上死了,他们被推到了一个偶然的车站,这使她想起了一件可怕的事。她看见他们站在站台上,孩子的身体在他们中间;她从来没有忘记他们跟着后退的火车时的茫然的神情。这就是她会发生的事。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内,她可能会发现自己在某个奇怪的车站的站台上,一个人和她丈夫的尸体.除了那个!太可怕了-她吓得浑身发抖。
当她蜷缩在那里时,她感觉火车走得更慢了。当时就来了-他们正在接近一个车站!她又看见丈夫和妻子站在孤独的站台上,用暴力的姿势拉下阴凉处,遮住丈夫的脸。
她感到头晕目眩,倒在床边,远离他伸出的身体,拉上窗帘,使他和她被关在一种阴郁的暮色中。她试着思考。她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掩盖他已经死的事实。但怎么做?她的思想拒绝采取行动:她不能计划,结合。她想不出什么办法,只能坐在那里,紧紧抓住窗帘,整天.
她听见搬运工在整理她的床;人们开始在车里走动;更衣室的门被打开和关上。她试图唤醒自己。最后,她尽最大的努力站起来,走到汽车的过道上,把窗帘拉得紧紧的。她注意到,他们仍然轻微地分开了汽车的运动,并发现在她的衣服上的一个别针,她把他们绑在一起。现在她安全了。她环顾四周,看见看门人。她以为他在监视她。
“他还没醒吗?”他问。
“不,”她摇摇晃晃地说。
“他要的时候,我把牛奶都准备好了。你知道你叫我七点前给他的。”
她默默地点点头,爬到座位上。
八点半,火车到达布法罗。这时,其他乘客都穿好衣服了,铺位也已折叠起来,准备一天了。搬运工在被单和枕头的重担下来回地走来走去,一边走过,一边瞥了她一眼。最后,他说:“他不是要起床吗?你知道,我们被命令尽早补好铺位。”
她害怕得冷了。他们刚进入车站。
“哦,还没有,”她结结巴巴地说。“除非他喝完牛奶,否则你不去拿吗?”
“好吧,只要我们重新开始。”
火车开动时,他又带着牛奶出现了。她从他手里拿了下来,茫然地坐着,看着它:她的大脑慢慢地从一个想法移动到另一个想法,仿佛它们是在一场汹涌的洪水中远远分开的踏脚石。最后,她意识到搬运工还在期待地徘徊着。
“我会把它给他吗?”他建议。
“哦,不,”她站起来喊道。“他-我想他已经睡着了-”
她等着看门人走了,然后拉开窗帘,从后面溜了下去。在半默默无闻的地方,她丈夫的脸抬起头来,就像一个长着玛瑙眼睛的大理石面具。眼睛很可怕。她伸出手拉下盖子。然后,她想起了另一只手里的那杯牛奶:她和它有什么关系?她想举起窗户,把它扔出去,但要做到这一点,她必须靠在他的身上,把她的脸靠近他的脸。她决定喝牛奶。
她拿着空玻璃杯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过了一会儿,搬运工回来拿。
“我什么时候把他的床叠起来?”他问。
“哦,现在不行-还不行,他病得很重。你就不能让他像现在这样呆着吗?医生希望他尽可能多地躺下来。”
他挠头。“嗯,如果他真的病了-”
他拿起空玻璃杯,走开了,向乘客解释说,窗帘后面的聚会病得还起不来。
她发现自己是有同情心的眼睛的中心。一个微笑亲切的母亲坐在她旁边。
“听说你丈夫病了,我真的很难过。我家里病得很厉害,也许我可以帮你。我能看看他吗?”
“哦,不-不,求你了!他不应该被打扰。”
这位女士宽容地接受了拒绝。
“嗯,你当然是这么说的,但你看上去好像你在疾病方面有过很多经验似的,我也很乐意帮助你。你丈夫走这条路的时候,你一般会怎么做呢?”
“我.我让他睡了”
“睡得太多也不太健康,难道你不给他药吗?”
“是的”
“你不叫醒他吗?”
“是的”
“他什么时候服用下一剂?”
“不是两个小时-”
这位女士看起来很失望。“好吧,如果我是你,我会试着给它更多的时间。这就是我对我的家人所做的。”
在那之后,许多面孔似乎压在她的身上。乘客们正在赶往餐车的路上,她意识到,当他们走过过道时,他们好奇地瞥了一眼已关上的窗帘。一个长着突出眼睛的灯笼人站在那里,试图透过褶皱之间的分界线,射出他突出的目光。那个满脸雀斑的孩子从早餐回来,用一只黄油的离合器拦住了过路人,大声低声说:“他病了;等售票员过来要票。”她缩到角落里,向窗外望着飞扬的树木和房子,那些毫无意义的象形文字是一张无休止地展开的纸莎草。
火车不时地停下来,新来的人一上车,就轮流盯着关上的窗帘。越来越多的人似乎经过了-他们的脸开始与她脑海中涌动的图像奇妙地融合在一起.
一天晚些时候,一个胖子把自己从迷雾中解脱出来。他有一个皱褶的胃和柔软苍白的嘴唇。当他把自己挤到面向她的座位上时,她注意到他穿着黑色粗布,打着一条肮脏的白色领带。
“今天早上丈夫病得很厉害,是吗?”
“是的”
“亲爱的,亲爱的!这太让人难过了,不是吗?”使徒的微笑露出金黄的牙齿.
“你当然知道,没有什么比生病更重要的了。这不是个好主意吗?死亡本身不过是我们最粗俗的感官的一种蜕变。让自己敞开心扉,接受精子的涌入,被动地服从神圣力量的行动,疾病和溶解对你来说就不再存在了。如果你能说服你丈夫读这本小册子-“
她周围的脸又变得模糊了。她隐隐约约地记得,听到这位有雀斑的孩子的母亲和母亲争论不休地争论一次尝试几种药物或轮流服用的相对好处;那位母亲夫人坚持竞争制度节省了时间;另一位反对说,你无法判断是哪一种药物对治疗产生了效果;他们的声音还在继续,就像铃铛在雾中嗡嗡作响.搬运工不时地提出一些她不明白的问题,但不知怎么的,自从他离开以后,她一定已经回答了,而且没有重复这些问题;这位母亲夫人每隔两个小时就提醒她,她的丈夫应该拿着他的药;人们离开了汽车,其他人把它们换了.
她的头在旋转,她试图在她的思绪掠过的时候抓住她的思绪来使自己稳定下来,但它们却像一片陡峭的悬崖边的灌木丛一样从她身边溜走了,而她似乎正在往下掉。突然,她的头脑又清醒了,她发现自己生动地想象着当火车到达纽约时会发生什么。当她想到他会很冷的时候,她就不寒而栗,也许有人会觉得他从早上起就已经死了。
她匆匆忙忙地想:-“如果他们看见了,我一点也不奇怪,他们会怀疑什么的。”他们会问题,如果我告诉他们真相,他们不会相信我-没有人会相信我!这将是可怕的“-她不停地对自己重复:”我必须假装我不知道。我必须假装我不知道。当他们拉开窗帘时,我必须很自然地向他走去-然后我必须尖叫。“.她有一个想法,那尖叫声是很难做的。
渐渐地,新的思想涌向她,生动活泼而又急迫:她试图把它们分开,抑制它们,但它们像她的孩子们在炎热的一天结束时那样,在她累得无法让他们闭嘴的时候,喧闹地纠缠着她。她的头变得迷茫了,她感到一种病态的恐惧,害怕忘记自己的角色,害怕用一些毫无戒心的话或表情来背叛自己。
“我必须假装我不知道,”她继续喃喃地说。这些话已经失去了意义,但她机械地重复着,仿佛它们是一个神奇的公式,直到她突然听到自己说:“我不记得了,我记不起来了!”
她的声音听起来非常响亮,她惊恐地环顾四周,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她说过话。
当她往下看汽车时,她的眼睛抓住了她丈夫铺位上的窗帘,她开始检查那些通过沉重的褶皱编织而成的单调的阿拉伯树。图案复杂难找,她凝视着窗帘,当她这样做时,厚厚的东西变得透明,透过它,她看到了她丈夫的脸-他的死脸。她竭力避免她的目光,但她的眼睛不动,她的头似乎被一个邪恶。最后,由于努力使她虚弱和颤抖,她转过身去,但这是没有用的;她面前的小而光滑的近处,是她丈夫的脸。它似乎悬挂在她和坐在她前面的女人的假辫子之间的空气中。她做了一个无法控制的手势,伸出手把脸推开,突然,她感觉到了他光滑的皮肤的触碰。她忍住了一声,半个人从她的座位上走了出来。那个戴着假辫子的女人环顾四周,觉得她必须以某种方式证明自己的行动是正当的-她站起来,从对面的座位上拿起她的旅行袋。她打开了袋子的锁,仔细看了看,但她的手碰到的第一个东西是她丈夫的一个小瓶子,在最后一刻,她匆忙地把它塞在那里。她锁上包闭上眼睛.。他的脸又出现了,挂在她的眼珠和眼睑之间,就像戴着蜡染的面具贴在红色窗帘上.
她吓得浑身发抖。她是昏倒了还是睡着了?几个小时似乎已经过去了,但天还很宽,她周围的人都和以前一样坐着。
一种突如其来的饥饿感使她意识到,从早上起,她就什么也没吃一想到吃的东西,她就感到恶心,但她害怕又晕倒了。她想起包里有几块饼干,就拿出一块来吃了。干面包屑使她窒息,她急忙从丈夫的酒瓶里吞下一点白兰地。她喉咙里的灼热感觉起到了抗刺激作用,暂时缓解了她神经的隐痛。然后,她感觉到一种轻柔地偷来的温暖,仿佛一股柔和的空气吹拂了她,成群结队的恐惧松开了他们的紧握,在她周围的寂静中退去,一种平静的感觉就像夏日里宽敞的宁静一样。她睡着了。
透过她的睡眠,她感觉到火车急躁的奔波。似乎是生命本身,用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把她扫地出门-把她扫入黑暗和恐怖,以及对未知日子的敬畏。-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静止的-没有声音,没有搏动…。轮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死了,就躺在他旁边,面无表情。多么安静啊!-可是她听到脚步声,那些要把他们抬走的人的脚.她也能感觉到-她感觉到突然的长时间的震动,一系列的强烈冲击,然后又一次陷入黑暗:这一次死亡的黑暗-一股黑色的旋风,它们像树叶一样旋转,在狂野的螺旋中旋转,数百万的死者.
她吓得跳了起来。她的睡眠一定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冬天的一天已经淡了,灯也亮了。汽车很混乱,当她重新拥有自己的时候,她看到乘客们正在收拾他们的包裹和行李。那个戴着假辫子的女人从更衣室里带了一株病常春藤植物,装在瓶子里,基督教科学家正在扭转他的手铐。搬运工用他不偏不倚的刷子穿过过道。一个没有人情味的人,戴着一顶金腰带的帽子,要她丈夫的票。一个声音喊道:“拜格盖奇快车!”当乘客们交出支票时,她听到了金属的叮当声。
不一会儿,她的窗户被一片漆黑的墙挡住了,火车驶进了哈莱姆隧道。旅程结束了,几分钟后,她就会看到她的家人在车站拥挤的人群中推开他们欢快的路。她的心脏扩张了。最可怕的恐怖已经过去了.。
“我们最好现在就把他扶起来,不是吗?”搬运工摸着她的胳膊问道。
他手里拿着她丈夫的帽子,正沉思着把帽子转到他的画笔下。
她看了看帽子,试着说话,但突然汽车变黑了。她举起双臂,挣扎着抓住什么东西,脸朝下,头撞在死者的床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