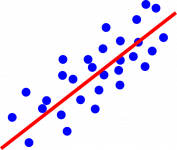“假姑娘”过年
在上世纪人民公社年代,洪山区和平公社东南部,有三个以庙命名的大队,即候驾庙大队、下马庙大队、落王庙大队。

相传,四百多年前,有“平民作风”的明朝正德皇帝喜好微服私访,一日驾临武昌时,红日西坠,天色向晚,需在此权过一宿。当地富户闻讯纷纷前来接驾,此后该地人丁兴旺,风调雨顺,于是修建三庙祭祀这位天子,把等候皇帝之地称为“候驾庙”,皇帝驻驾之地称为“下马庙”,其安歇之地称为“落王庙”, 三庙从此闻名四乡。
几百年后,这些庙宇周围形成了三个一字形排列的自然村落,犹如三条巨龙自西往东逶迤于长江与东湖之间。再往东,便是闻名遐迩的中国第二钢都——武钢。
文革期间,这三座庙宇均毁于一旦,现在,其周围的多数自然村落也因修建四干道和商品房而拆迁,年轻村民一夜之间与“富二代”、“官二代”一样,个个成了令人刮目相看的手握上千万资产的“拆二代”,这是后话,本文暂按不表。
本故事的主人公为候驾庙大队的“拆一代”,这一代人则没有“拆二代”那么幸运,他们生不逢时,命运多舛,思之令人怆然。
候驾庙大队包括犁头尖、杨家旗杆、常家墩、田家墩、石家墩、赵家墩、王家墩等自然村落,一两个墩为一个小队。 一百多户人家的一百多栋泥墙草顶房屋稀稀疏疏地摆布在庙宇的东西两头,与民房相比,庙宇显得十分壮观,青砖布瓦,宛如龙首。为避长江水灾,房屋多建在几米高的土墩上,房屋前后是堆土墩形成的水塘及杂乱无章地生长着的野草和刺槐、桑、杨柳、梧桐、水杉、苦楝等树木,有的粗大如盆,有的却细如麻杆。
一九五八年腊月二十一日早晨八时许,候驾庙大队七小队队长王大毛将吊挂在刺槐树丫上小段钢轨敲得当当响,扯起喉咙叫着: “开工啦,女将割菠菜,男将……”他喊声如破锣,震得肖腊梅家的一堵破泥墙哆哆嗦嗦,晃晃悠悠。
身怀六甲的肖腊梅瘦骨伶仃,身穿油布雨衣,脚蹬套鞋,手拿小铲子迈出家门。屋外,细雨霏霏,寒风凛冽,菜地茫茫。风雨歪斜地吹打到她那张皴得开裂的蜡黄的脸上,似刀割,如针锥,牙齿地不停地打着颤。她挺着便便大肚,迈着鸭步,一双小脚在泥泞的小路上蹒跚着,穿着打满补丁的破棉衣的身体在风雨中扭动着。她最后一个扭到菜地,参加抢割菠菜,以便赶在春节前卖到城里去。临近收工时,肖腊梅感到肚子阵阵疼痛,羊水顺着她的双腿往下流,她要临盆了。
在同伴的搀扶下,她艰难地回到家中,丈夫王苕货叫来接生婆刘巧英,又忙着烧开水,全家忙成了一锅粥。
刘巧英专事接生,不务农活,吃东家,喝西家,长得白皮嫩肉,胖面肥腰。
五十岁的肖腊梅这次是生第六胎,前五胎生的都是“光头和尚”,个个调皮捣蛋,不甚念书。这次她“轻车熟路”,不到半个时辰,随着其一声大叫,本故事的主人公随即呱呱落地。
“快端热水来!”接生婆叫喊着。
“生了个……”王苕货边端水边问。
“恭喜!恭喜!是一个带把的。”
“唉,又是个讨债鬼,今后拿麽事给他们吃哦。”王苕货哀声叹气。
俗话说:“五十五,生个拨浪鼓”,老六生下来只有三斤四两,皮包骨头,像只刚生下来的小狸猫。
该给孩子起名字了。名字好起,因为老大叫大傻子,依次二、三、四、五傻子,老六自然就叫六傻子啦。在这个地方,给孩子起傻子、苕货这些土掉牙的名字,不是因为孩子真的傻或苕,而是希望他们聪明,好养,是以为“贱名者长生”的心理使然。除了叫傻子、苕货的以外,还有叫坏货、泥巴、狗子、猫子、甚至还有叫粪桶的……但这一流风遗俗在本世纪已悄然消亡。
时间如水往前流淌,转眼就到了一九六六年腊月,小孩愁生不愁长,六傻子一晃八岁了。
老天爷专门作弄人,肖腊梅认为女孩对母亲贴心些,想生个姑娘伢,可偏偏生了六个“光头和尚”;有的人想生个儿子承接香火,又偏偏生了一大堆女孩。
肖腊梅思女心切,就把六傻子打扮成姑娘伢,穿花衣服,扎揪揪辫,加之六傻子瘦小体弱,倒蛮像一个姑娘伢的,他自己也爱和姑娘伢们一起玩跳橡皮筋、踢毽子、躲咪猫之类的游戏,于是,六傻子这个名字渐渐被人们淡忘,大家都叫他“假姑娘”。
“假姑娘”长着一张白净瓜子脸,脑袋大得出奇,嘴唇薄如刀刃,腮上几乎无肉,腮帮子冻得通红通红,恰是深秋的红富士,一双丹凤眼深凹着,双耳如扇,双腿如柴,穿着一件花棉袄,活像一个稻草人。
还有几天就要过年了。王苕货每天都在为年货发愁。年饭总要凑弄几个菜吧。家里的六个“光头和尚”,个个饭量大得惊人,像从饿牢里放出来的,肚子就像无底洞,总是填也填不饱。平日里计划粮食不够吃,就用白菜萝卜熬粥,萝卜缨腌菜是家中的一道主菜,还有臭腐乳、臭瓜皮什么的……
家里好不容易喂了一年的两只下蛋老母鸡和一只阉鸡前几天突然咯咯咯地怪叫,血红的鸡冠子变得蔫吧发乌,继而口吐白沫,爪子不停地伸缩着,长着芦花色漂亮长毛的屁股左右摇摆了几下,便直挺挺地倒下不动了----发了鸡瘟。正是:“破屋更遭连夜雨,漏船又遇打头风。”
“这年怎么过啊?”王苕货蛾眉紧蹙地嘟哝着。
除夕夜到了,年饭摆上了桌子。王苕货从里屋拿出一小挂鞭炮,说道:
“放鞭吧,谁来放?”
“我放!” “光头和尚”们异口同声地答道。
“让‘假姑娘'放吧。”爸爸一言九鼎。
这种好事自然会落到最小的孩子头上。鞭炮噼里啪啦一下子放完了。“光头和尚”们蜂拥而上,在硝烟和纸屑中抢夺那些断了引子的鞭炮。“假姑娘”一下子扑倒在地,瘦小的身体压住一个未爆炮竹。“假姑娘”抢到那个炮竹,就像抢到一个金元宝,满脸堆笑,像喝醉了的猴子似的一蹦老高,将其拿在眼前左看看,右看看,探究其未爆炸的原因。突然,“嘣”一声巨响,炮竹爆炸了。“假姑娘”被这突如其来的爆炸惊得三魂荡荡,七魄悠悠,两个眼圈就像被人涂上了浓浓的墨汁,视觉变得模糊起来;捏炮竹的三根手指头顿时失去了知觉,慢慢肿起,宛如刚刚洗净的细胡萝卜,整个人犹如一只干瘦的大熊猫。
待到“假姑娘”上桌吃年饭时,唯一的荤菜是一碗“夹干肉”,碗中的肉早已被哥哥们抢得精光,在爸爸的呵斥下才给他留下了一块豆腐干,毕竟家中半年多没沾荤了。他拿起筷子,拈起那块豆腐干,眼睛湿漉漉的,委屈地抽噎着,扒了一口饭,眼睛里的泪水再也夹不住,扑簌簌地往下流……
大年初二是给娘家人拜年的日子。一大早,王苕货携肖腊梅带着“假姑娘”这个“脚胯子”去给家住黄家大湾的岳父岳母拜年。黄家大湾位于东湖东南侧,距候驾庙七八里路程,只有一条湖边小径相通。
是日雪后初晴,伴着湖边蜿蜒的小路泥泞不堪。远处,武钢的几个高大的烟囱张着一张张大嘴,肆无忌惮且不知疲倦地喷吐着黑烟、黄烟、灰烟和白烟,这些五颜六色的烟气,将紫红的朝霞涂抹得乌七八糟,犹如一只只脏兮兮的手,一起抹到了如花似玉的美少女的脸上;近处,一只母牛带着几个月大的牛犊啃着田埂上的枯草根,牛犊隔三岔五地咧着大嘴,龇着白牙“嗯吗嗯吗”地叫着,就像年幼的小孩在母亲面前撒娇一般;紧挨田埂的路上,摆着一大一小两堆热气腾腾的牛粪。
一向寡言少语妈妈这时开言了:
“老幺,我给你打个谜语好不好?”
“好!”“假姑娘”一蹦三跳。
“仔细听好:‘苦竹岭上一乘磨,皇帝老子不敢坐。'”
肖腊梅辛辛苦苦生了六个儿子,其中五个见了书就头疼,唯独“假姑娘”伶俐乖觉,读书如同吃饺子,毫不费劲。只见他的眼珠滴溜溜地转了两下,大脑壳晃了三下:
“牛粪!”“假姑娘”脱口而出。
肖腊梅龇出一口黄牙,笑了。
湖边小径曲曲折折,路旁阿娜垂柳折折曲曲,柳枝光光秃秃,柳芽儿半开不开,好似一群群妖姬艳女做化疗后落光了秀发。光秃的柳枝在寒风中微微颤抖着,向这一家三口打着招呼。
“假姑娘”的鼻子冻得通红,宛如一粒可爱的小山楂果,鼻尖上挂着清鼻涕。童趣盎然的他忽而捡起一块大石头,猛地砸进湖中,湖面溅起高高的水花,犹如洒下一堆碎银;忽而拾起一块瓦片,侧弯着身体,使劲向水面甩去,瓦片好似开足了马力的摩托快艇,箭也般的向前飞去,湖面泛起一条长长的蜻蜓点水般的浪花,“一、二、三……八、九,唉……”瓦片终于在水面支持不住,晃晃悠悠地沉入水底。
日挂树梢,黄家大湾那几十栋茅屋隐约可见。外公外婆家的那间低矮破旧的茅屋立在村子最北端,孤零零的,十分显眼。外婆正打着手罩,眨巴着眼望着他们呢。
外婆年近八旬,瘦骨嶙峋,佝偻着腰,像一只蒸熟了的大龙虾。她嘴唇瘦薄,遮不住牙齿。
外公小外婆一岁,形容枯槁,胡子扎煞,眼窝深陷,一根根白发直竖着,像刺猬的毛刺,白发下两点磷火般的目光闪闪烁烁,糜烂的眼角夹着两团黄色的眼屎。他双手抄在棉袄袖笼里,嘴上叼着劣质香烟,不停地咳着,时而往地上吐一口浓浓的绿痰,犹如一摊摊吃了绿果子的乌鸦拉的屎从天而降。
“快给外公外婆拜年!”王苕货满脸堆笑。
“外公外婆新年好!”
几个勉强听得清的音节极不情愿地从性格内向的“假姑娘”口中蹦了出来。
突然,一只双耳耷拉着的花土狗从屋里窜了出来,圆瞪着两只闪着绿光的狗眼,龇出长短交错的犬牙,朝着“假姑娘”他们狺狺狂吠,样子十分骇人。“假姑娘”猛地闪到爸爸身后,双手扯住其衣角,觳觫着。
这时,一阵“哦,哦……”唤狗声从隔壁人家传来,只见一年轻妇人在给婴儿端屎,一抛黄橙橙的稀屎摆放在婴儿的屁股下面,一股热气往上冒着,犹如倒落在地上的一碗刚出笼的蒸鸡蛋。花土狗顿时撇下“假姑娘”他们,向那抛美食冲去。
外婆用她那弯曲的、枯柴一样的手给姑娘、女婿、外甥各端来一杯茶后,就到灶前忙饭去了。“假姑娘”接过茶杯,只见杯中漂浮着几片劣质的花红茶叶,白瓷茶杯用成了黄黑色,杯子内壁上的茶垢足有半寸厚。
外婆家养的两只鸡躲过了鸡瘟,但“躲得过初一,却躲不过十五”,她杀了一只阉鸡过年招待客人,母鸡留着下蛋。
午饭时分,肖腊梅端着一碗热腾腾的藕煨鸡汤,搁放到堂屋正中的三条腿摇晃一条腿欲断的黑黢黢的八仙桌上。“假姑娘”独自一人在堂屋内踢着毽子。
忽然,一股浓烈的鸡汤香味扑鼻而至,他有一年多时间没闻到这种诱人香味了。“假姑娘”停止踢毽,口水顺着他那薄薄的唇角直往下流,他那双深凹的丹凤眼四处睃巡着,发现其他人都在灶房,便蹑手蹑脚地来到桌旁,他那只长满冻疮的被炮竹炸肿了的小爪子,飞快地伸向了他早已瞄准好的目标——两只用线系在一起的大鸡腿,将其塞进嘴里,歪着头大啃起来,嘴里发出吧嗒吧嗒的响声。吃完鸡腿,又吃鸡翅,他用袖子揩了一下鼻涕,又吃了几块藕,最后端起碗来,吸吸溜溜地喝了大半碗汤,实在是吃不下了,汤已经漫到其喉咙管了。
待到肖腊梅将第二碗菜端上桌时,桌上一片狼藉,一大碗鸡汤所剩无几,只有一大堆鸡骨头和到处洒泼的鸡汤。她气得顿足捶胸,大声叫着,声如响铃,酷似母狼:“这怎么得了啊,那用线连着的两只鸡腿是只能看的呀,不能吃的呀!”原来,当地拜年要拜倒初七八,这才初二,以后客人来了就没有大菜招待他们了,那两只鸡腿是“看”菜,只有初七八最后来拜年的人才能吃。“假姑娘”见闯了大祸,边打着连串的饱嗝,边往外溜。这要在平日,他少不了挨一顿毒打,但在过年期间,大人一般是不会打骂小孩的。
吃过午饭,该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阵阵北风迎面吹来,“假姑娘”的饱嗝变成了馊嗝,肚子咕咕直叫,馊嗝如雷,臭屁如鼓,走了不到半里地,开始屙稀,长期缺少油水的肠胃见了鸡汤这样的“稀客”必然留不住而滑肠,那只花土狗嗅味追来,将那抛稀屎吃得干干净净,仰头望着“假姑娘”,以示谢意。又走了不到百米,“假姑娘”腹部绞肠刮肚的疼,又屙了更稀的一抛屎,花土狗见状,又追上来吃了。“假姑娘”一路走来一路屙,花土狗一路追来一路吃;人屙了八九遭,狗吃了七八次。人屙得晃晃悠悠,狗吃得摇头摆尾;“假姑娘” 两眼发黑,踉踉跄跄,倒在爸爸怀中。
“唉,这个年过得……”肖腊梅喟然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