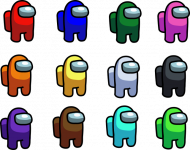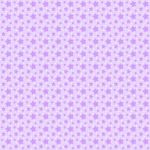恩怨两家人(二)
四

我爷平时广交朋友,家里也常有客人,我爷还专门为客人预备了一个大房子,远来客人还可以在这里多住一些时日。我家附近一伙胡子的首领名叫李金龙,因为和我爷同姓李,姓氏后面又都带着一个“金”字,就与我爷作了把兄弟,也成了我家的常客。最近他与伙内几个兄弟起了争吵,赌气离开那里,到外面散散心,就来到了我家,并要我家住几日,我爷接待了他。
就在李金龙来我家之前,住在外村的我爷岳父家里的人捎来话,说我的岳父病了,恐怕活不了多久了,老爷子想闺女,要叫我奶去陪陪他。老爷子是一个高寿老人,已经九十多岁了,而我的岳母,在二十多年前就去世了。我爷是一个大孝子,对岳父岳母很好,就像一个亲儿子,听到这个消息,当天就和我奶在一起,去看望老爷子,并把我奶留在老爷子身边,嘱咐我奶安心地照顾老爷子,不要惦记这边的家,等到老爷子的病好了再回来,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明白,老爷子的病是不会好的,所谓病好之日,也就是老爷子离开世界那一天。我爷刚从他岳父那里回来,就遇到了另一件事:镇子里“杏花红”酒坊的老板来找我爷,说他们老家那边出了事,家里摊上了“官司”。他的老家在河北,和我爷也算是同乡。他回河北老家,他的“杏花红”自然开不下去了,要卖给我爷,价钱当然是“出血”价,他之所以要将酒坊买给我爷,第一是因为我爷买得起,第二是看准了我爷的人品,最重要的是,他与我爷是同乡加朋友,我爷曾经帮助过他。
“杏花红”酒坊所卖的酒的名称叫“杏花红”,酒坊因酒而得名,“杏花红”的名字香飘周围百余里,在当地很有名气。我爷就爱喝“杏花红”,当地的酒坊虽多,只有“杏花红”才是他杯中之物。仅凭对“杏花红”的喜爱,我爷就买下了酒坊。买下“杏花红”后,我爷每天要亲自去料理酒坊,了解酒坊的管理和“杏花红”的制作,就像了解他的老朋友。
我奶去娘家未回,我爷每天去酒坊,家里只有我爹和我娘,还有一个不请自到的客人李金龙。李金龙在我家是早晚两顿酒,白天一壶茶,闲着没事,院里院外地乱转。他里转外转,有一个人进入了他的眼中,那就是我娘。那时我娘三十多岁,尚有年华,也是被村里人夸赞的漂亮媳妇,这在长年苦守山寨的李金龙的眼里,成了灼目的光斑。他一时贼性大发,打起了我娘的主意。他先是表现出对我娘过份的亲热,整天“侄媳”、“侄媳”地叫着,接着就有了猥亵的语言,我爹不在时,又有了动作,吓得我娘不敢离开我爹半步。接下来,李金龙不把我爹放在眼里,在我爹面前,对我娘浪言浪语,粗俗下流,毫不掩饰调戏之意,对李金龙的这钟禽兽之举,我爹又气又怕,无奈之下,告诉了我爷,我爷听后 ,脸色是青的,只淡淡地对我爹说一句:“你要保护好你的媳妇!”第二天,他又去了镇上的酒坊。第二天晚上,他又听到了我爹同样的倾诉,他回复我爹的,还是那句话。第三天晚上,我爹见到我爷时,几乎要哭出来了,显然,李金龙的行为,开始变本加厉。就在这天晚上,胡子团伙里来了一个人,把李金龙叫走了。
我家屋子的最西端,放着一个破箱子,箱子与墙角之间,有一个空隙,那里夹着一把刀,这把刀是从老一辈人传下来的,刀长大约三尺左右,刀头很宽,往后变窄,刀上生满了锈,平时家里人都把它当作了废铁,但由于是祖传的,也没舍得扔掉,现在我爷把它找了出来,吃完晚饭,就磨这把刀,一连磨了两个晚上。我爷磨完这把刀,就把我爹叫到一旁,对我爹说:“过几天,欺负你媳妇那个人,还会到咱家来,他再欺负你媳妇时,你就用这把刀把他杀了。” 我爹听说叫他杀人,吓得浑身哆嗦。我爷对他说:“你只管把他杀死,以后的事由我来处理!”我爹仍然身上发抖,不敢接那把刀。我爷对我爹说:“你眼前有两条路,你选其中的一条:其一,是你带着你的媳妇,远走高飞,走到我永远看不见的地方,从此你不再是我的儿子,我李金梁没有这样窝囊的儿子,但是我的孙子你不能带走!其二,是你把那个人杀死,你就永远是我李金梁的儿子!”我爹的双手颤抖着,接过我爷手里的刀。
几天后,李金龙果然又来了。他看见我奶仍然照顾老父未归,我爷仍然去镇里料理他的酒坊,家里只有我爹和我娘,胆子越发大了起来,他声称自己忘记带烟土,他的烟瘾又犯了,现在行动不得,叫我爹到村里的王寡妇家里为他取一块烟土。村子里王寡妇是他的相好,被他包养,这是全村人都知道的。王寡妇家里放着烟土,以便他在王寡妇家里时使用。我爹出去了。李金龙开始对我娘猥亵调戏,我娘哭了起来,我爹突然转了回来,手里拿着我爷磨得亮亮的那把大刀。李金龙不但不害怕,反倒厚颜无耻地叫我爹去砍他,我爹的眼睛充满了血丝,把刀高高举起,刀在空中颤抖着,但没有砍下来。李金龙得意地叫嚣着。
“还不动手!”我爷在门外大喝一声,一个箭步闯了进来。看见我爷,李金龙一跃上了炕,用身体撞开窗户,跳了出去。整个动作,比猴子还敏捷。
闯进屋子里的,有三个人,除了我爷,还有我爷的两个兄弟,三个人的手里,各端着一支枪。那时,很多人家是有枪的。
李金龙拼着命往山下跑,我爷和他的两个兄弟在后面追,一边追一边开枪射击。此时,李金龙只有逃跑的份儿,没有还击的份儿。他朝山下村子里的王寡妇家跑,他想那里也许是他的避风港。他跑到王寡妇家门前时,敲门的手还没举起来,就倒在血泊里,他已经身中数弹。
五
打死了胡子头领李金龙,我爷名声大震,被编成了故事,在妇孺口中传诵。而我爷自己心里明白,他闯下了大祸:打死李金龙,他的同伙不会善罢甘休,会找上门来报仇的。那些日子,我爷日夜提防胡子来报复,把我二爷、三爷两家人,叫到自己家,三户人家,住在一起,三个男人,枪不离手,夜间睡觉,一个男人在窗前警戒,另两个男人,合衣枕枪。一天夜里,院子外面的柴垛突然起火,我二爷、三爷要去救火,我爷阻止了他们,叫他们端着枪,守在窗口,而女人和孩子,全都趴在地上。眼见着大火把柴垛烧成灰烬,我爷就是不准家人去救火,就这样,三家人一直在屋子里守候到天亮。事后,我二爷和三爷问我爷为什么不去救火,眼看着一整垛的干柴被烧掉了,我爷说,如果那是把火是胡子放的,我们救火的人暴露于火光之中,是在明处,而胡子却在暗处,我们岂不成了胡子的活靶子?我二爷和三爷,只能暗自敬服,我爷虽是一个农民,临危之时,却有大将的风范和智谋。
一场大火,虽然给山上的三家人带来了惊恐和不安,但接下来的日子,一直是风平浪静,这使我爷和全家人都放松了警惕,然而,在两个多月以后,传来了使我爷的精神完全崩溃的恶耗__我爷的大儿子,也就是我的伯父,在回家的路上被人打死了,他身上留下的是枪伤,身上有几处伤痕,其中的两颗子弹,分别击中了胸部和头部。我爷听到我伯父被打死的消息,当时就昏了过去,半个小时后,在家人的哭叫声中醒来,醒来后再也没说话,几天过去了,他没有说一句话。他心里明白,打死我伯父,就是李金龙的那伙胡子干的。这个判断随即得到了证实,我爷在城里所开的店铺里的伙计说,那天,有一个陌生人给正在城里主持商业经营的我伯父传话,说我爷病了,叫他赶紧回家,我伯父闻讯后立即离店回家,不想在半路死于非命。
我爷作出一了个决定,他要卖家产,雇用军队,剿灭这伙胡子。在我伯父和我爹两个儿子之间,我爷最喜爱的,其实还是我伯父。我爹性格懦弱,在他看来难以成大气,而我伯父的性格却像我爷,做事有一股闯劲,而且很有心机,所以我爷把外面的一切商务经营都交给了他,而把我父亲留在了自己的身边。我伯父不在了,我爷的一切希望也都破灭了,他此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为我伯父报仇,这是一个无法阻止的念头,别人更是难以拦阻。
在我家附近的县城里,驻扎着一个团的军队,可是这个县的百里方圆内,却有大大小小三、四伙胡子,而这些当兵的,却每天闲着没事干。军队,官府,胡子,三者之间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共同遵守着一条游戏规则,政匪不争,兵匪不争,相安无事。这个团驻扎县城一年多,没有剿过一次匪,而胡子们把他们的活动范围,也转移到离县城稍远一点的地方。
我爷知道,这些穿着军装扛枪的,凡事因利而动。我爷去找赵敬义,请他到县城与那个团长搓合此事,因为多年的政客生涯,已使他在官场上的关系之网如老树之根,处处伸展,层层盘绕,认识的,不认识的,都有沟通的渠道。赵敬义面带难色,但他还是应允了。他告诉我爷,见了那个团长,不能说是雇用他的部队,那样会花很多钱的,而且,现在也不许搞这一套,只能说钱是孝敬给他个人的,请他个人来帮忙。
这个团长以他私自用兵会掉脑袋为由,对我爷来了一个狮子大开口,要二十万块银元。经过讨价还价,确定为五万元。五万元,对于这个团长来说,是他靠在战场上玩命,几年也搞不到的钱财,而对于我爷,却足以使他倾家荡产。
这个团长提出来,在他出兵剿匪之前,还要有一些铺垫,因为剿匪虽属军队的正常行为,但亦需有上级的指令,非他这个团长所能擅自决定。所以他叫我爷组织当地百姓搞一个要求政府剿匪的请愿活动,这样,他就有了出兵的口实。好在我爷在当地很有威望,这种不流血不流汗的人情还是有人送的。那一日,我爷买了两只肥猪,又架起了几个大锅,凡去县城参加请愿的,都可饱餐一顿猪肉。为了这顿猪肉,很多老人和孩子都来了。请愿的队伍声势浩大,使小小的县城沸腾了一番。锣鼓既已敲响,接下来就是正戏了,这时,我爷突然要求那个团长把他抓起来。这正是我爷的聪明过人之处,因为他知道,经过这样一番折腾,胡子已有所准备,很难一举将其歼灭,于是他要演一场“苦肉计”,以麻痹胡子。
剿匪行动取得“胜利”,是必然的结果,打死了一些胡子,另一些的胡子溃散跑掉了,这些胡子从社会中来,再次散入社会,混迹于三教九流,于是我爷走上了漫长的查访之路,他想从逃跑的胡子口中找到杀害我伯父的直接凶手。一年后,我爷回来了,他从一个胡子口中得知,那次截击我伯父的胡子共有三个,一个是元凶,两个是随从。我爷打听到了那两个随从的下落,但那个元凶,却杳无踪迹。从此,我爷把寻找打死我伯父的元凶,作为他最重要的事情。
六
自从我爷买掉家产请军队剿匪,已经伤了家中的元气,再说,我爷的心思都在为我的伯父报仇上,再也无心经营,咱李家的家业从此衰落,而赵家却时来运转,再耀门庭: 在家赋闲多年的赵敬义,一天从报纸上看到了一个人的名字,这是本省省主席的名字。这个人的名字,使他燃起了重返仕途的希望。此人名叫徐臻,是他官场上的老熟人,而且两个人的私交也不错。赵敬义去找徐臻,徐臻念及情面,接待了他。徐臻对赵敬义说: “这几年你呆在家里,没给伪满做事,这事做对了,要不你就完了,不会有今天了。你找我也是找对了,我这个省主席官不算太大,但还能供的起老朋友吃饭,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 徐臻因人施政,专门为赵敬义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做海上警察局,派赵敬义去当局长。海上警察局,顾名思义,这是负责海上安全和辑查走私的机构,其权力是具有弹性和可伸缩的,其大无边,其小无事可管,全凭掌权人的运作,这是一个想不发财都难的地方。从此,赵敬义在家乡再度名声大震,人们虽然不知道海上警察局长的实惠,但都知道海上警察局长的地位和权力。
赵敬义有一个儿子,是他的大老婆生的,比小雯大八岁,在县城里的中学读书,这也是全县的唯一的一所中学。在这所中学读书的还有我的姑姑,我爷的头脑比村子里所有人的头脑都开放,叫我姑像男孩子一样去读书,所以也上了县城中学。青石村一共有三个读过中学的,一个是赵敬义的儿子,另两个就是我爹和我姑。赵敬义的儿子长得很帅气,就像年轻时的赵敬义,而我姑姑长得十分秀美,这是继承了我奶奶的遗传基因。两个人既在同一个学校读书,又是同乡,如同桃李同园而栽,光艳相映,芳香互递,两个人不免彼此留意,情窦初开,但这只是一种朦胧的爱情,羞涩与男女授受不亲的礼教,像一张柔纱,把两个人的情感遮裹起来。倒是双方的两个老人,将这张柔纱揭开了一角。那是我爷和赵敬义在一起饮酒,谈起在同一所学校读书的两个孩子,两个人冒出了两家要结成儿女亲家的话,不过,两个人的话到此为止,并没有深说。后来,我姑和赵敬义的儿子都中学毕业了,我姑的读书生涯到此为止,而赵敬义的儿子将要继续升学深造,由于国内事局混乱,他要送儿子到国外去留学。
听说赵敬义的的儿子要到国外去留学,我姑神不守舍,茶饭不思,我爷看在眼里,同时我爷也很喜欢赵敬义的儿子,就去找赵敬义,想把我姑和赵敬义儿子的婚事定下来,最好把婚事办了,然后两个人一起出国,我爷还表示,原意拿出二百块大洋资助他们出国。咱家的家境虽然大不如从前,但挤出二百块大洋来还是没问题的。但这件事被赵敬义拒绝了。我姑和赵敬义儿子的婚约,是由两个老人用舌头签定的,为这份婚约作见证的,就是一碗浓酒。当时两个人都带着醉意,在酩酊酒醉中,我爷记在了心里,而赵敬义只是挂在了嘴上。记在心里的,就像在土里生了根,挂在嘴上的,就像叶子挂在树梢上,秋风一吹,就无影无踪。赵敬义是以孩子年龄太小,读书其间不宜成婚为理由拒绝我爷的,其实心里还是觉得赵李两家的孩子并不相配。这件事对我爷的打击很大,不仅打击了他为女儿谋求幸福的愿望,也打击了他的自尊心,他对赵敬义的怨恨就是从这件事上开始的。
我想我姑也一定找过赵敬义的儿子,如果说伤害我爷的那个人是赵敬义,那么伤害我姑的人就是赵敬义的儿子。从那以后,我姑的精神状态一天不如一天。赵敬义儿子出国留学后,我姑天天都下山,去青石村的村西口。村西口有一条路,路边有一排白杨树,村里人进城,出远门,都走这条路,赵敬义的儿子去国外洋学堂读书,也是从这条路上离开的。我姑就站在路边的白杨树下,眼睛呆呆的,茫然地望着路的尽头。那时正是秋天,路口的风很硬,树上的叶子也开始飘落,秋风撩乱了我姑的头发,树叶打在她的脸上,她唱着当时流行的《四季歌》:“正月到来雪满窗,大姑娘窗前绣鸳鸯……火车好像无情棒,打得鸳鸯各一方……”她一遍又一边地唱着,歌声凄婉,余音回荡。如果说唱红这首歌的周璇是金嗓子,那么我姑就是银嗓子,而且,就容貌而言,我姑长得比周璇还要美!一群孩子围着我姑,大人们站在远处指指点点,看来,我姑真的是疯了。我爷受不了这个场面,把我姑拉回家。我姑一次次往山下跑,我奶和我妈看不住她,无奈,我爷就用一条铁链,把我姑锁了起来。我姑的疯病更重了,头发披散着,脸也不洗,眼睛直直的。看到我姑这个样子,我奶每天都流几次眼泪。在我奶和我姑面前,我爷是不流泪的,他心里难过,就骂我奶,骂她生了个没出息的闺女,其实,在没有人的时候,他也流了很多眼泪。
自从我姑病了以后,我爷常常站在我家西边的土岗上,一个人对着村子的方向,大声喊叫着。我爷的这个举动,使得家里人都觉得奇怪,我奶叫我悄悄到我爷身边,听他在说什么。我在山上绕了一个弯,绕到我爷的后面,我听见他是在骂赵敬义:“赵敬义,你这个势利小人,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的爹爹,不也是一个小掌柜的吗,你的爷爷,不也讨过饭吗,你当了官,你就了不起了……” 我爷大声骂着,越骂越激愤,好像赵敬义就站在他的面前。我把我看到的情况告诉了我奶,我奶吓坏了,以为他也疯了,叫我一定把我爷拉回来。我妈对我奶说:“我爹不会有事的,就叫他喊吧,不喊反倒把他憋屈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