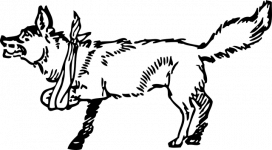在谎言中进行的特别救治
这是一个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农村的故事:面对一个假装的急诊病人,接诊医生不但不予以揭穿,反而与他结成同盟,还将谎言再加工继续把瞒骗进行到底。

从这个故事里,我们或许会窥视到在那非常年代里那些挨过整或担心会轮到自己挨整的人们对政治运动的恐惧和无奈,还有在分田到户后的农民对自己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拼搏,更有面对婚姻遭到摧残的年轻男女对真爱的执着和痴情。
“请饶医师赶快回医务所,有急诊病人来了”。正在我们场部广场上看电影的我听见放映队的老陈在放映机的广播里叫喊。马上站起来向外面挤,等我从人群里挤出来时,就看见药房里的刘大姐已站在放映队的发电机旁等我。由于发电机声音太响,我走过去大声问她:“什么样的病人?”
“我只看见是用竹制摇椅抬了一人来。”她也大声回答,接着又问“要不要叫上小戴去收费呢?”
“哦,不是说抬来的吗?那还不是要住院的,收费等出院时再收也可以呀!要么等会看情况再说,我们先走吧。”
说着我们就向医务所走去。在半路上看见从朦胧的月光下对面走过来一个高瘦的人影。她老远就叫:“是饶医师吧?”我边走边答应着说:“是的。”
待走近我们时,她说:“真是不好意思,好不容易看一场电影,又要让你们给我儿子看病,耽误你们看电影了。”
“没关系。你儿子怎么了?”我边走边问她。
“他今天下午突然呕血,呕得全身都是血呀,真是吓死我了。”说着这位母亲就嘘嘘哭泣起来了。
看她这焦急的模样,我们就小跑着奔向医务所。
一进医务所的大门,在月光下就看见在一张竹制摇椅里躺着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旁边一位年约70多的瘦小的老年人焦急地在来回走着。我们进去后在刘大姐刚点着的烛光下,见那年轻人满身都是暗红色的血,尤其是脸的下半部及脖子上最多。就连他躺着的摇椅上也有不少同样的暗红色血迹。见此状我心里着实一阵紧张。这位母亲也看出了我的紧张就急切地问:“我儿子的病很严重吧?不会出大事吧?”在此同时病人的父亲那一双求助的眼神也在呆呆地望着我。我只好紧张地回答说;“是很严重,你们也知道我们医务所里就这样的条件,所以必须转到县医院去抢救。”
“转县医院?天哪!这80多里路怎么去呀?”这位母亲睁大眼睛望着我。
“那当然是用车子送了。”我说。
“到哪里去请车子呀?”这母亲急得在那里直搓手。
我想了想说:“要么打电话请县医院出救护车,要么看我们场的解放牌汽车会不会去。”接着我就吩咐刘大姐带这位母亲到场部看解放牌在不在家或者打电话向县医院叫救护车。
听我说完这些。这母亲就急得哭着与刘大姐一起奔出医务所,而这位父亲就在孩子旁边默默低下头继而就蹲下去。至此我就转身准备给病人做些检查。首先我想检查血压,了解患者失血严重到何种程度。然而当我打开手电把血压计放在病人身边准备给他测血压时,突然发现竹制摇椅上的血没有凝块,再抚摸他脸上脖子及身上其他部位也无凝结的血块。此时我明白了这些暗红的“血迹”并不是血。那不是血又是什么呢?难道是红汞?想到这里我镇定下来了,继续给他做相关检查,他的心率、血压、体温、呼吸以及神经深浅感觉反应都正常,他的神志明明是清醒的。但就是推之不动呼之不应,他为什么要这样呢?用装病来对付自己年老的父母?或者他是一位智障者?其中究竟有什么蹊跷呢?
当我正在此猜测时,他的母亲跟着刘大姐急匆匆地回来了。刘大姐告诉我们说:“我们场部的解放牌出差还没回来,县医院没有救护车来,怎么办呢?”此时我再次仔细地打量了这位母亲。在她那乱如鸡窝的白发下是一张瘦削的脸膛和一双惊恐的眼睛,高瘦的身材上穿着像是被水浸透而又破旧的衣服,两只裤脚卷过了膝盖,手和脚上粘满了泥土,转过身再看这位光着头眼眶里含着眼泪的父亲,不仅身材瘦小,背也驼了,在那露出同样是浸满汗液破旧衣服外面的手脚也是粘满了泥土,看来他们都是刚从田地里干完活过来的。面对这对又累又饿的老人,我心里一紧,心想这时如果把他们儿子装病的真相告诉他们就实在是于心不忍。
“饶医师,救护车来不了,又没有车子送去。那我儿子不是没救了?”这位母亲急切的哭叫声将我的思绪拽了回来。
“哦,我刚才检查一下,你儿子是有病,但是不是很严重呢?我想先向你们了解一下他以前呕过血吗?还有他以前还得过什么其他的病?脑子没受过伤吧?或者说平时脑子还清楚吗?”
“他的身体一贯很好,没有什么病,脑子怎么会受伤呢?平时脑子好用着呢!更没有呕过血。”他母亲抢着回答。
“他今天是跟你们在一起干活时突然呕血的?”
“不是的,我们两老口今天在田地里插秧到月光露出才收工回到家里,看见近几天不太吃饭生闷气在家躺在竹制摇椅的儿子全身是血,就吓得顾不得做晚饭,就急忙用绳子将竹制摇椅捆好,又将儿子抬了近5公里路,途中歇了十几次,才到你们医务所来。”又是由她母亲向我代诉。
听到这里我心里又一阵痛楚。不得不在心里向喊出“可怜天下父母心”的人发出由衷的折服。
“经过我刚才的检查和你们诉说的情况来看,病情不会是很严重的,所以今晚不必转县医院了,我们会尽力医治他的。”为了稳住这位母亲我不得不如此答复她。
由于考虑到我们的病人几天不太吃饭,要给予一些维持生命的输液治疗。我就吩咐刘大姐准备进行救治,我在开处方时,悄悄地将我发现的情况也告诉了她,同时考虑到这一对老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而嘱咐她暂时不要将这层纸捅穿。
“你们这么大的年纪,为什么不叫村里其他的人帮忙抬呢?”当我们给我们这位病人挂上输液后,我还是很好奇地问。
“自从去年我们农村分田到户,为了搞好自家的生活家家都很忙,尤其是现在‘双抢’期间,恨不得一个人分成两个人来干活。像这几天有月光的晚上,田野里禾斛的打谷声要响过11点钟,早上不到两点就又要到秧田拔秧。再说人家的年轻人都在忙,而我儿子在家不干活已有好几天了,不好意思叫人家帮忙了。”还是由他母亲回答我。
当我再次看到这位母亲憔悴的面孔时,就想到了他们二老还没吃饭呢。
“哦,你们到现在还没吃饭,饿坏了吧?”我边说边拿出饭菜票吩咐刘大姐到场部食堂去搞两份饭菜来。
“哦,不要,不要。我们倒是不很饿。只是我的儿子这几天没好好吃过饭又呕了血哪!”
“你的儿子没关系,因为我们已经给他输液了,里面有维持生命的东西,不会饿坏的。”
“我儿子真的无大碍?”
“是的!今晚在此住一晚,明早天一亮就可以回家。”我响亮地肯定回答。
“那这比让我们吃任何东西都好。”
过了好一会,刘大姐双手空空败兴回来了。原因是食堂里的人说已经没有饭菜了。“那还不是他们不愿意放弃看电影。”刘大姐嘟囔着。
“算了,那这样吧,大娘,你们就回家去吃饭吧,从你儿子这段时间输液的情况来看还好,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我们会照看好的。”我以商量的口气对老人家说。
“不用,我们年纪大了,一餐饭不吃无大碍的,只要我儿子能很快好起来就好了。”
“那不行,不光是你们得要去吃饭,你们的儿子在打好吊针后很可能也要吃点东西的。”
“这样啊,那好。老头子,那我们这就回去搞饭吃。”这位母亲说着,那父亲也点点头。
等两位老人家走后,我对刘大姐边做眼色边说:“等输液完了我们还要检查病人的鼻腔和口腔,看看血是从哪里出来的,如果他一时还不清醒不能配合,那你就准备一根大号针头刺他的人中或指头就会醒的,因为那是相当痛得哟!”
“好的,我这就去找出来先消毒备用。”刘大姐会意地笑了笑答应着。
待三瓶输液结束后,我拿起鼻腔扩张器和一根压舌板来到他的身边,先用手推了推他的身子,仍然不动。那我就用鼻腔扩张器在手电光的照射下伸进他的一侧鼻腔,刚进去一点就稍加点力撑开扩张器,他的头就不得不向后缩。见此我就故意说“现在醒了。”看完鼻腔无异。就撤下鼻腔扩张器换上压舌板说:“你现在能不能张开嘴,让我看看口腔吧。”此时他就无奈但还是无语地慢慢把嘴巴张开。口腔咽喉当然也无异常发现。为了能让他开口说话,我就又故意叫喊:“刘大姐,大号针头消好毒了吗?病人还是不能说话,可能还是不太清醒,快拿过来刺一下他的人中或指头吧。”我刚一喊完,我身边的人就轻轻哼了一声说:“你刚才把我的鼻子弄的太痛了。”并用手轻轻揉那被我弄痛了的鼻子。
你撑不住总算说话了,我心中暗暗窃喜。你知道吗?我这些动作只能在你老爸老妈不在场时才可以使用的哟!
“你清醒了就好,还有哪里不舒服?”我轻声问道。
“还好。我早就要小便,实在是憋不住了。”
待他小便后,我就指着那些暗红色的“血迹”笑着对他说:“伙计,其实你根本没有昏迷,也没有什么病,而且这些根本就不是血,你能骗得过医生?”
“不是……血,是……是……什么?”他红着脸结结巴巴地说。
“是什么,应该问你自己呀!兄弟,你这是为什么呢?看你那老爸老妈那么年老又那么瘦弱,在干完强体力劳动后,又饿着肚皮抬你近10里路到这里,你也听见了,途中他们歇了十几次了。你就那么忍心在摇椅上躺得住吗?我们看了都想哭,更何况作为他们亲生儿子的你呢?”我说这番话凶巴巴的,当然也没有好脸色给他。
他低下了头坐在摇椅上。良久,他轻轻地哭起来了并说:“我也实在是没办法呀。”
“没办法就装神弄鬼,用红汞替代出血来糊弄亲爹娘?”
“我……我……”他紧张地一边说着一边用眼睛看着刘大姐。
这意思我当然明白,他是看刘大姐在这里不便明说。于是我就吩咐刘大姐回家去休息。
看着刘大姐走出了医务所,他接着说:“我死得心都有,我还害怕真的出血?”
这下严重了,该我紧张了。一个年仅23岁的小伙子竟然会有死的念头。
“为什么?因为爱情?”我试探性地轻轻问道。
他点了点头红着脸说:“是的。我与邻村一个叫红莲的女娃相恋,我们互相真心相爱,但我妈和已出嫁的几个姐姐都极力发对,理由是她家是富农成份,怕以后会影响我家及后代。我俩为此曾多次在无人处抱头痛哭,我还想喝农药了却此生,她劝我不要走极端,说我们会有感动上帝的那一天。”
“那你爸是什么意见呢?”因为他只提到他妈和姐姐反对,洏没提及他父亲反对。
“我爸?你也看见了。他忠厚得就像是一个哑巴人,家里的事只有我妈说了算,她按李铁梅的说法是家里的‘一把手’呀!”
“那你前几天也是为这事在家生闷气?”
“前几天红莲哭着告诉我说已有别村的人到她家说媒了,她父母劝她死了跟我在一起的心,就嫁到别村去。一听到这话我就像是五雷轰顶,怎么办呢?几天来想来想去就想以我大出血来摧毁我爸妈不接受红莲的顽固意志,因为我是他们唯一的儿子。我原想在这没有电灯光的夜晚会蒙混过去,没想到在你们这里就过不去。我爸妈他们知道真相后也就吓不倒了。唉!你说我该怎么办才可以与红莲永远在一起呢?”
“这件事你问我,那就真是问道于盲了。因为我虽然比你年长6岁,但还没处对象呢。”
“那我求你将我今天装病的事在我爸妈那里再瞒几天,看我和红莲在这几天里能不能再想到办法来。可以吗?”
“这……这……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那你至少不能在体力上再折磨他们哪。他们实在是太可怜了。”我很为难地说。
“其实今天躺在他们抬的摇椅上,我内心一方面有强烈的忤逆犯罪恐怖感,另一方面又有对他们死力阻挠我追求幸福的泄愤感。另外我要不弄出点大动静来他们是不会拐弯的,有好几次我想自残,但红莲都痛哭极力反对。所以我今天所为实在是无奈之举。以后我向你保证不会再如此在肉体上损害他们二老了。”说着他眼眶里又涌出了眼泪。
“那等你爸妈来了看情况,能帮你说上几句就说几句看看。”
正在说着,我们似乎听见外面有脚步声走过来。
“可能是我爸妈回来了。”他边说边就势又躺进了摇椅里。
真的是他们二老进来了。
“哦。吊针打完了,还好吧?”她是面向他儿子问的,因为她看见她儿子的眼睛是打开的。可她儿子却把脸扭向另一边。
“早就打完了,现在可以让他吃点东西了。”我只好代为回答。
“那好吧,我带了一大碗饭,另外打了几个鸡蛋做了一个汤过来。”
也许是实在太饿了吧,这个小伙子马上接过他妈送到他面前的饭菜竟狼吞虎咽起来了。
看着儿子这副吃相,他父亲只轻轻地说:“你慢点吃呀。”他母亲也高兴地问我:“饶医师,你这是用了什么药,我儿子竟好的这么快?”
“你儿子很可能是由于这几天在家生闷气而闷坏了胃,再加上这几天没吃饭就引发胃出血了,这次是你们发现的及时,不然是有生命危险的。”我脸上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
“那这病以后还会发吗?”母亲着急地问。
“以后不要让他再生好几天的闷气和饿肚皮就可能不会再发了。下次再发作就没有这次轻飘了。”我这样肯定回答的时候,发现我们的病人正躲在那硕大的饭碗后面的阴影里向我眨眼睛微笑呢。
“那可就要难死我们两老口了!唉!我们这条犟牛又实在太犟,怎么办呢?老天爷呀!”这母亲焦急地叹着气。
“究竟是什么事?竟有比要你儿子的生命还重要?”我背向着这位母亲给我们的病人送回去一个偷偷微笑并问着。
“事情是这样的,反正现在他自己人也在这里。而这里人又不多,我就跟你说吧。我家的这条犟牛就是要与王家的红莲成家,说句实话,红莲这女娃水灵而又乖巧,论长相与人品都比我儿子强。我也喜欢她,但就是不能娶她进门。因为她家是富农成份,那就是四类分子家庭呀。一来运动就是挨整挨斗的对象。而我们家是世代贫雇农。与他们家联姻,那我们家在社会上就抬不起头。而且会永远影响我家的后代呀!等我们死了埋进土里,都会遭后代子孙责骂的。不同意他们的婚事,听你这般说,儿子的生命又有危险。怎么办呐?这不是很难为我们老两口吗?”这母亲说着又哭起来了。
我们大家都沉默了好一会后,我想了想首先打破了这阵沉默说:“我看这事也难也不难。”
“怎么不难呢?”他母亲立即停止了哭泣并问我。
“是这样的,我先说难吧,你家贫雇农与富农联姻,不说别的,就说一个人看见岳父岳母在台上被挨斗,做女婿的心里那苦闷那痛苦确实是一般人难以承受的,而且这样的事是会经常发生的。……”我说到这里,就被一个声音打断了。
“这没什么难的,大不了,他们每次挨斗后,我们去看望他们安慰他们。或许我心里会好过些。”我们的病人望着他的母亲抢着说。
“你别急,伙计,我还没说完呢,还有以后你家的人就不能入党提干了,恐怕连基干民兵也别想干了……”说到这里又被他打断了。
“要入党提干干嘛,我就是要做一个普通老百姓,过自己的小日子。”
“说真的,你要有思想准备,你个人就像你自己说得那样,永远只能是一个老百姓没有了前途。”
“我们种田的人要什么前途,难道我的锄头棍会被人捋掉了?”
“你既然有如此之决心,那就不难了。”我也被他冲撞得苦笑了。
“听他瞎说什么呀!你是可以不要前途,那还有我们的子子孙孙呢?他们都跟你一样不要前途?还得在每次运动中挨整挨斗。你就不怕他们责骂你?”他母亲此时大概忘记了他的儿子还在“生病中”竟如此责问他。
“话也不是这么说的。”我听她这么一说,就明白这位老人家主要是怕挨整挨斗的事会轮到他们家,所以对有些东西她老人家还是混淆不清的。也是为了解围,我就以启发式的口气对他母亲说,“这大概对你家的子孙后代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你老人家想想看,他们联姻是成份富农的女儿嫁到你贫雇农的男方家,只会使她丈夫受到一些连累。而他们子孙的家庭成份应该还是贫雇农呀!所以对你们的子孙影响应该不是很大。反过来如果是贫雇农家的女儿嫁到富农成份的男方家,那这贫雇农女儿的子孙就只能是富农成份了,那就差得多了。是不是?”
“哦,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这点呢?他自己不要前途是他自己的事,我们子孙没有大的影响,那这事就可以好好考虑了。”她母亲自言自语地好像有点明白了。
“但你们家影响还是有的,因为那些干部也可能会在他们的心目中将你家打入‘另册’的,那起码在目前那些诸如光荣先进之类的事是不会轮到你们家的吧。”
“这些与我儿子的性命相比来说又能算的了什么呢?更何况他自己都不顾及这些,而我们两老口子都是一只脚踏进了棺材里的人,还会想要那些东西么?”看来这老人家可能基本想通了吧?!
“妈。你想通了?答应我们了?”她儿子这时竟兴奋得也忘记了自己还在“生病”跳到她母亲跟前摇着着母亲的手问道。
“等我回去再好好想想。”他母亲推开他儿子的手说。
“我今晚不在这里住院了,我这就回去,我完全好了。”这小伙子又高兴得转身跳到我跟前与我拥抱起来了,并眨着眼睛对我说。“谢谢你,饶医生,你不但治好我的病,还治好了我妈脑筋里近年来的老顽固。也许你就是我红莲所说的上帝派来的那个人吧!我们全家都会永远记得你给予的巨大帮助的。”
我摇着头说:“不要那么说,如果你妈通过今晚的说服能彻底改变对你们这件事的态度,我就真的要好好祝福你与红莲有情人终成眷属。”
次日他带着红莲到我们医务所来再次表示感谢。看他那神气样,他恐怕不光是来致谢的,顺带还有向我们炫耀他那水灵而又乖巧的心上人的吧!后来他们结婚时还给我们送来了喜糖,看他们那喜滋滋的样子是多么幸福呀!再后来他们生了孩子,那做爷爷奶奶的又给我们送来了涂了红颜色的喜蛋。看着他们二老笑眯眯的脸膛,我想他们肯定还不知道在那个晚上我与他儿子给他们上演的双簧吧!
饶华梁(退休后居住在上海工作的女儿家地址:上海杨浦区包头南路629弄6号楼301室电话:021-552310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