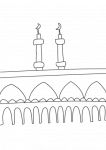砖厂往事(上)
年轻时候的经历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甚至是刻骨铭心的,终身难以忘怀。

我们这一代人,知青生活就是一段终身难以忘怀的经历。
一
1968年12月22日,晚八点正,新闻联播播放了一条最新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从此一场声势浩大的上山下乡运动就此展开,一直持续了近十年。
我本已参加工作,由于最新最高指示的发表,单位不敢留用,23日一到单位,管人事的就把我叫去办理辞退手续。从此我就成了无业游民。在城里晃荡了一个多月后,只好报名下乡了。
69年初,第一批知青下乡我报名下去了,下乡时还未满19岁,在生产队干了一年农活,评工分跟妇女一个档次,只算半劳力,与我上下年龄的小伙子都比我的工分多,心里有点不爽。我不但要跟他们一样出工,收工后我还要自己现煮饭吃,经常他们出工了,我还没有吃饭。
第二年,春节后,生产队长问我:“社办砖瓦厂缺个炊事员,拿月工资,每月三十块钱,给队里交二十块钱副业款,愿不愿意去?”拿月薪,每月三十元,给队里交二十元副业款,还可以剩十元自己用,比在生产队挣工分强多了!我当然愿意去哦!二话不说,立刻卷起铺盖,带上洗漱用具,还有心爱的收音机,就到砖瓦厂去了。
砖瓦厂在长江边一个叫二沱的地方,站在厂里的地坝,上下几十里都在视野之中。长江从西边紫黛色的群山之间汹涌奔来,在砖厂下面的沱里打个旋就涌进下游的峡谷去了。峡谷里,两岸悬崖壁立,山上林木蓊郁,那是公社办的林场。长江宛如一条青绿色的带子镶嵌在两岸绵延的群山里,静静地流淌。厂前面,高高的山崖下是一片银灰色的沙滩,由于这里土质软,在江水的冲刷下,年深月久便形成了一个大沱。上下游的河道都较狭窄,唯有这里的河面特别宽阔,每逢上游有轮船下来,上行的轮船就必须停在沱里避让,这时沱里就有短时间的热闹与喧嚣,轮船过完了,又恢复一片宁静。
建砖瓦厂的地方以前是坟园,因为这里的土质适合烧砖,所以就在这里建了砖瓦厂。名为厂,其实才十几个人,加上管理人员:一个支书,一个会计,一个出纳,还不到二十个人。工人每天所干的活就是装窑、出窑。两个砖窑,轮换着烧,工人每天都有活做。
制作砖坯是附近生产队那些半大的娃儿,他们在生产队做活挣工分很少,不如在砖瓦厂做砖坯挣钱划算,做一块砖给一分钱,手脚快的一天可以做五六十块砖,就能挣到五六角钱。
烧窑是另外请的师傅,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每逢装满一窑砖瓦要烧制的时候,师傅就带着徒弟来了。徒弟是两个年轻小伙子,一个姓何,排行老二,叫何二娃;另一个姓张,矮矮胖胖的,叫胖墩儿。两个徒弟年纪约十八、九岁。烧砖一般要连续烧好多天,昼夜不停地往窑洞里面加碳,烧几天以后师傅就来看一下。师傅一来砖厂,厂里就是好酒好菜招待他吃喝,完了,就到窑子上面那个观火口去看砖窑里的火色。烧砖瓦的技术就是要会看火色,窑子里炉火千变万化,有时像正午的太阳红的发白,甚至白的耀眼,有时又像早晨刚刚冒出山脊的太阳红的鲜艳,如朝霞般美丽。如炉温过高不及时压火砖瓦会烧成瘤子,就报废了;炉温低了又烧不透,也不行,就要把火加大。啥时候该压火,啥时候该加火,师傅从来不说,因为这是技术,过去,技术是不会轻易传授别人的,俗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烧一窑砖瓦师傅可以得到两百块钱的报酬,徒弟则一分钱都没有,吃饭还自己带粮食煮,盼望的是熬两年后,自己能独立看窑挣钱!于是每次师傅到窑顶上看火色徒弟都是跟在师傅后面,小心翼翼地陪着师傅站在窑顶边,徒弟边看火色还要看师傅的脸色,揣摩师傅的心思,希望能得到师傅的一点技术指导,然而师傅面无表情只是默默地看,啥子都不说。窑子里面炽热翻滚的火苗,红红的炭火如龙腾虎跃,似凤凰涅。默默地看一会儿后就下来,回到办公室聊天,直到离开时才招呼徒弟:“把火压小点”或“把火加大点”。就这样熬了几年,看窑的技术似懂非懂,总是出不了师,总是只能给师傅打工。师傅呢,轻轻松松的拿钱,徒弟心里怨恨死了,也没有办法。何二娃跟着师傅烧了四年窑了,按理早该出师了,可是师傅就是不吭声。二娃儿悄悄对我说:“再这样下去,不想学这个技术了,不如回生产队挣工分。”
二
在社办砖瓦厂当炊事员也不轻松。
砖厂的工人都是自己带粮食来,交给伙食团,带来的粮食五花八门,包谷、红苕、豌豆、胡豆样样都有。用这些杂粮煮饭很麻烦,首先要把包谷磨成面,洒水拌匀了倒进甑子里蒸上大气,同时用另一个锅煮豆子,煮熟以后备用。包谷面蒸上大气,蒸一会儿后,又要倒出来再次洒水拌匀,叫打“回趟”。然后把煮熟的豆子捞起来拌在一起,拌匀了又倒进甑子里继续蒸,直到蒸熟为止。打“回趟”时水加少了,蒸出来的饭很干,按规定的分量称,就要亏本;如果打“回趟”时水加多了,工人又有意见,因此打“回趟”的时候,要边洒水,边用手捏,捏成一团了松手能散开,而不成面粉,就合适,否则就还要洒水,如果散不开,就是水洒多了。
刚开始做这种杂粮饭没有经验,第一次包谷面的水加少了,饭很干,亏了。第二次水又加多了,他们嘲笑我煮的饭,“抓一把能甩过河”
厂里还规定每天早上和中午要煮两斤黄豆的菜豆腐,给工人下饭,既是汤又是菜。因此,从早上五点起床,就开始捅火做饭,把包谷面蒸上,豌豆煮在锅里,就开始磨黄豆。石磨有点大,一个人推吃力。推几下又去添一瓢豆子,乘机又歇一下,因此要当搁些时间。
做完早饭接下来又要开始做午饭。
就这样一直要忙到午饭后才有点时间休息一下。然后又要推磨,磨包谷,准备第二天要蒸的包谷面。
晚上我不煮饭,由工人自己安排,想吃啥子就煮啥子,这段时间我就轻松了。
每个星期有两次政治学习,晚饭后,支书拿张报纸来让读一篇报上的文章。
休息的时候没有书看,实在是无聊,只有听收音机,或在附近转转、散散心,看天上流云飘飞,看河里来往的木船。下水船总是行驶在河中间,顺激流飞驶而下,上水船则紧靠着河岸如蜗牛般艰难的缓缓上行。自己目前的处境就正像沿河岸上行的木船,吃力地行进在人生的河道里;又像天上飘飞的流云,漫无目的游荡,不知何去何从。河里的行船还有前行的方向,而我呢?却不知驶向何方?飘向何处?
当然,如有精力和兴趣,也可以挣点外水,那就是从砖厂运砖到坎下的河边,运一个墩子(两百块砖)五角钱。那时候在城里做一天小工才八角六分钱呢!
刚来的时候,觉得挑砖到河边挣五角钱还不错,运一个墩子可以挣五角,运十个墩子就可以挣五块。一天只运一个墩子,一个月就可以挣十五块钱了!这样我一个月就能积攒到二十五块钱,那时候父亲一个月的工资才十八块钱,父亲该多高兴啊!
然而挣外水的想法很快就打消了。
看起来从砖厂到河边不远,实际有三百多到四百米,我一次最多能挑三十口砖,有一百五十多斤重。一个墩子需要挑七次才能挑完,一下午只能挑三次就累的不行了。更恼火的是,担那么重下陡坡,两只脚只打闪,搬了一个墩子到河边,两只腿胀痛了好几天,从此再也不干了。下午闲暇时还是到处转转,或听听收音机。
收音机是自己做的,没有盒子,全部零件固定在一块胶合板上,后面用导线连接,十分简陋,我叫它板板收音机,虽然样子丑陋,但是音质不错,且声音洪亮,为了使低音更浑厚有力我用皮鞋盒子做了个共鸣箱,听起来音质可以与台式收音机媲美!在物资与文化都十分匮乏的年代,没有其他娱乐,听收音机就成了唯一的乐趣。
初春的下午,太阳暖烘烘的,坐在地坝里,边晒太阳,边听收音机,十分的惬意,忘记了烦恼,心完全沉浸在美妙的音乐里。
那时候收音机里除了新闻节目外就只有八个【样板戏】翻来覆去的播放。样板戏里我最喜欢听两个芭蕾舞剧的音乐,尤其是【红色娘子军】的“琼花独舞”、“万泉河边”,还有《白毛女》里面的“北风吹”、“扎红头绳”更是百听不厌。
那天下午,我坐在地坝里,边听收音机边看河里的行船,从地坝那头走来一个女娃儿,年纪约十六、七岁。
“大哥,请问,李鑫在哪儿?”
我打量了她一眼。这女娃儿长的很清秀,鹅蛋脸,眉毛浓浓的,双眼皮,大眼睛黑亮黑亮的,个子中等,身材苗条,两根辫子又黑又长,辨梢扎着红毛线作的头绳,穿一套兰卡叽布的列宁服。心里暗暗惊讶“好漂亮!”
“你找李鑫?”
“嗯。”
“他可能在砖窑那儿。”我指了指屋背后那个地方。
“你是?……”我望着她, 心想她是李鑫的啥子人呢?媳妇还是妹妹?
她赶忙说:“我是他的妹妹。”
说完,转身飞快地走了,两根粗辫子在背后一甩一甩的,扎在辫梢的红毛线活像两只红蜻蜓在背后飞舞。望着离去的背影,目光好久才收回来。
三
李鑫也是来砖厂给生产队挣副业款的,年约二十岁,身材高大壮实,在学校读书时就是校篮球队的主力运动员,现在是家里的全劳力,他力气大,一次能挑四十块砖,两百多斤重,是砖厂里数一数二的大力士。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就回乡务农了。不爱说话,只会埋头做活路,做事踏实,又爱帮忙,经常受到砖厂领导的表扬,砖厂里的人也都喜欢他。
刚到砖厂的时候,我不会煮杂粮饭,还是他教的我。
李鑫已找了媳妇还没结婚,因为家里房子窄,没有房屋作他的新房。他要结婚就必须得另外搭一间房子,为此给生产队长说了,允许他到社办砖厂做工,挣点钱积攒起来好买材料起屋。他劳力好又勤快,在砖厂每月可挣到四十多元,交队里三十元副业款了还能剩下十多元。
据李鑫说他们有五兄妹,他是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最小的弟娃是老幺,才三岁,那天来的那个是老二,家里都叫她二妹子。
二妹子小学毕业后家里就再没让她上学了。老汉儿说:“女娃子读那么多书做啥子?认得到几个字就行了。今后反正都是做家务带娃娃。”于是二妹子就只好在家里帮妈做事,喂猪,煮饭,种自留地,带弟弟。
生在农村的女娃儿命运就是如此,长大了生儿育女做家务就是她们人生的任务,不能再有其他追求。
四
日复一日,每天都是忙着煮饭推磨,不觉得天气就热起来,只能穿夹衣了。
好像没过多久吧,她又来了。
那天,正忙着煮午饭,进来一个人,扭头一望,又是是她——李鑫的妹妹,今天穿一件红底白花的衬衫,蓝色的卡叽布裤子,担了一副箩筐,里面装的包谷,脸红红的,满是汗水,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了,额上的刘海也被汗水沾在了头上。
“大哥,请你帮忙称一下,这是我哥这个月的口粮。”
我走过去提了一下,有点重,取过秤一称,净重八十斤。
“你好得行!担这么重,累不累?”
“不累。”
她望我腼腆的笑笑,脸上立刻现出两个深深的酒窝,浓浓的眉毛下一双大眼睛黑亮黑亮的。
把她担来的包谷收了,我就开始推磨,磨黄豆。
“来,我帮你添磨。”她马上走了过来,抓起饭瓢就帮我添磨。
“那当然好哟!谢谢!”我擦擦脸上的汗水,欣然同意了,这会儿就想有人帮忙呢!
我推磨,她添豆子,虽然磨子有些重,但有人说话了,也不觉得了,一会儿就把黄豆磨完了。我去端灶上的甑子,把蒸了第一次的包谷面倒出来洒水,她就帮我把另一口锅里煮的豆子捞出来,等我把包谷面的水拌匀了,就把煮熟的豆子和在一起,又倒进甑子去蒸。接下来,就淘洗白菜。我洗菜是把水从缸里舀到木盆里,洗三次,她见了,把衣袖往上一卷,说声“我来。”伸手就把引水来的竹筒从水缸上面移到外面,直接让水流进木盆里,边洗边冲,很快就把白菜洗干净了,捞在筲箕里,边滤水,边就取过砧板切起来,“喳喳、喳喳。”几分钟就切完了。她的动作好快,实在令我佩服。
“你们家离这儿远不远?”
“不是好远,十几里路。”
“担这么重走了十几里路!不得了!”
“没得啥子,挑这么点东西算啥子嘛?农村忙的时候天不亮就上坡做活路,太阳都好高了才回去吃早饭,吃了饭又上坡了,下午太阳偏西了才回来吃中午饭,午饭后休息一会儿又上坡一直要做到天黑尽了才收工,那才累呢!”她说话好快,像吐枇杷仔。
农忙季节那个累我深有体会。
“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突然,卧室里的收音机响起了《白毛女》的音乐。我忘记了关收音机,先一直在播放新闻,没注意,突如其来唱响了,我和她都愣住了。马上我和她又都沉浸在优美的音乐里了。
我进去端出那个丑陋的板板收音机,放在饭桌上。
《白毛女》播放完了,她连连赞叹:“好好听呀!”
她歪着头左看右看,望着板板上那些花花绿绿的零件自言自语的说:
“好怪呀!就这些东西能放出那么好听的声音!”
“这是你做的?”她转过脸,浓浓的眉毛下一双大眼睛盯住我,问道。
我说:“嗯”
“你会做收音机?”她感到很惊奇。
“这有啥子嘛!依样画瓢,照图施工,只要认得到字就得行。”
她望望收音机又望望我,一双大眼睛眨了眨,忽然像发现了啥子?
“哦,我晓得了,听哥哥说你是城里来的,是知青,你姓成!”
“啥子知青哟,跟你一样的农村社员!”
她望我笑了笑。“不是知青,啷个会装收音机呢?”
一笑她脸颊上就现出两个深深的酒窝,好可爱!
“这倒不一定,你看了书也一样能装收音机!我就是照到书上的图装的。”
“我不得行,没得你聪明!”说完,她又望我莞尔一笑。脸上两朵红晕像两朵桃花,红晕里还有两个酒窝。
“听你哥说,你读过小学?”
“读过。现在没读了。”
“你不读书了,在家里做啥子呢?上坡种田挣工分?”
“要做的事多了,喂猪、煮饭,放牛,放羊,砍柴,种自留地,样样都做。农村里的事情做的完吗?”
“你好能干哟!你会做那么多事!哪个能找到你这样的媳妇,那真是好福气!”我开她的玩笑。
“你乱说!”她的脸立刻红了,连耳朵都红了,嘴巴一翘,狠狠地在我背上捶了一拳头。
“你应该继续读书才好!”
“爹不让我读了。爹说女娃儿读那么多书做啥子,长大了反正都是种田,操持家务。”
“你这么聪明能干,不读书好可惜哦!”
“也没得啥子,你读了书,还不是下乡种田来了!”
她的话点到了我的痛处。一时无语了。
是啊!本来是有机会上大学继续读书的,可是,这场运动把继续读书的梦破灭了。发动运动的时候说是搞三年,现在三年早已经过了,运动还没有结束的迹象,招生、招工都没有任何消息。不晓得运动到何时才是头?
不过我很快就消除了不愉快的情绪,继续跟她聊天。
“只读完小学还是不行,起码要读完中学。”
“爹不让我读,我也没办法!”
“听你哥哥说你们姊妹好多哟!”
“是的,我们有五姊妹,哥哥是老大,我是老二,……。”
“家里还有其他人吗?有爷爷奶奶吗?”
“没有。爷爷奶奶,他们在自然灾害那几年都死了。”
“听说你哥哥找了媳妇啦?”
“找了,还没有结婚,家里还没有给他起屋,家具也还没得。看明年得不得行?”
“你哥劳力好,力气大,又勤快,在砖厂每个月都能挣四十多块。一年就是好几百了!”
“哪里会哟?给生产队交三十块钱的副业款,就只剩十几块了!一年只存的到百多块钱。哥在这里做了几年了,还没凑够起屋的钱呢!”
“你们生产队要交这么多副业款啊?”
“不交这么多,就不让来,有啥子办法?”二妹子显出无奈的神色。
午饭后,她就回去了。望着远去的背影,不知为什么竟有点怅然若失,是因为她漂亮?还是因为她能干?说不清楚
五
开春后很久没有下雨,那天半夜忽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如注,狂风一阵阵呼啸,似乎要将屋顶掀翻,不一会儿外面的积水就从厨房的门缝灌进了厨房,一道闪电划过,猛然发现雨水就要流到我睡觉的卧室门口了,我赶紧翻身下床,抓起厨房里铲煤的铁锨从灶膛里铲了几铲炉灰堆在卧室门口,筑了道堤将水拦住。还好,狂风大雨只下了一会儿就停了,可是这一折腾睡意全消,看床头的闹钟时间才半夜两点过点儿。早上五点我要起来做饭,怎么办?于是我就用数的办法催眠,不知过了好久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睡梦中猛然听见有人喊:“天亮了呢,你还不起来做饭啊?”听声音是厂里喂牛的丁大爷。
丁大爷喂的是一头大水牛,头上一对角像两把大弯刀,水牛是砖瓦厂里专门给砖坯池里和泥的,那是一头成年壮牛,牛的脚掌有一个海碗那么大。和泥的时候丁大爷就把水牛牵到泥塘来回转,牛的四只大脚就把泥踩的又细又黏,只需一天就可以把泥和好,这个工作是人做不了的,制作砖瓦的泥是黄泥巴,又叫粘土,十分地粘稠,只有水牛才能和的了那泥巴。
我睁眼一看,啊!果然天己大亮了!糟了,床头的闹钟早己响过了,由于自己睡的太沉没有听见。时间己是六点多了。赶紧下床,衣服也顾不得穿,抓起铁锹就跑到砖窑上从窑洞铲红炭倒进厨房的大灶里,二娃儿看到我慌慌张张的样子,听说我是起床晚了,也赶紧抓起他的铁锹帮我铲。灶膛的火加好了,他又帮我把两口大锅抬上灶。一口锅煮豆子,一口锅蒸包谷面。正在忙乱中,就有人敲着饭碗来了,一看豆子才下锅,包谷面还在洒水,就说俏皮话,接着工人陆陆续续地进来了,围在灶台边敲着饭碗说风凉话,情急之下我赶紧跑到支书那里请他帮我解围。
支书是个五十多岁的老人,他在砖瓦厂里是威信最高的,没人不敢听他的话。果然,支书来到厨房,只说了一句:“早饭还在煮,你们先到窑子上赶早做一会儿活路,饭好了来喊你们。不许围在这里。”大家尽管不情愿,还是悻悻地离开厨房到砖窑上做活路去了。
支书解了我的围,心里十分感激他。
工人们走了,我又开始按部就班的煮饭,包谷面蒸上甑子了,就转身架磨子磨黄豆。
刚磨了一会儿,二妹子来了,上身穿一件鱼肚白的衬衫,下穿一条浅灰色的裤子,脸红扑扑的,一对大眼睛透着十分的灵气,两根长辫子拖在胸前,微微隆起的胸部,更显出少女窈窕的身材。
“又给你哥送啥子来了?”我首先招呼她。
“给他洗铺盖。”她腼腆地一笑。脸上两片红晕像两朵桃花,一笑就现两个深深的酒窝。
“你好勤快哟!”我边往磨眼里添黄豆,边夸她。
她抿嘴一笑。眼睛飞快地把伙房里一扫,“你这是弄晌午的呀?”
“哪里哟!今天起来晚了……”我把今天早上发生的事说了,她哈哈哈大笑。
“来,我们两个人推,快些!”她舀一瓢豆子添在磨眼里,就马上走过来抓住推杆帮我推几转,然后又去添一瓢豆子,又抓住推杆推几转。多一个人推磨轻松多了,速度也快多了,很快就把黄豆磨完了。
“行了,行了,快去给你哥洗铺盖吧!”
“不忙,我给你把白菜洗了切了,再去。”
直到我这里确实没啥子事了,她才转身离开。走时顺便就把洗菜的大木盆提去了,我把一包白猫牌的洗衣粉递给她。她不要,她说有皂角是一样,我还是硬塞给她了,我说洗衣粉洗得干净些,而且方便。
早饭煮好了,立即跑到砖窑喊工人们回来吃饭。接着又开始煮午饭。由于早晨起来晚了,一上午都没有停歇,直到午饭后,收拾完伙房,我才松了口气。
今天太阳大,雨后的太阳特别晒人。不想到外面转,就在卧室里摆弄收音机。装粮食的木柜就是我的桌子,没有书也没有报,就只有一个板板收音机搁在那里。广播电台下午一般都是播放文娱节目,几个样板戏翻来覆去地放。
转动旋钮,搜了几个台,都是放的京剧,不感兴趣,又继续搜,终于收到一个台在放芭蕾舞剧《白毛女》,刚刚才开始,还在播放序曲。
“成哥!”
二妹子来了,她来还我的洗衣粉,我接过来顺手放到了窗台上。
“你坐嘛!”我拖了根板凳给她。
她犹豫了一下坐下了。
“成哥,你在听啥子?”她好奇的盯着收音机问道。
“芭蕾舞剧白毛女。”
序曲完了,接下来就是欢快优美的“北风吹”主旋律了。我们都不说话了,完全沉浸在欢快优美的音乐里了。
听完了北风吹和扎红头绳,后面就是地主逼债,音乐立刻转为紧张、急骤。
“成哥,还是放先那个吧!那个好听些!”
“这是电台播放的,它播啥子,就只能听啥子。你想反复的听,只有用唱机放唱片才得行!”
“唱机、唱片是啥子?”二妹子大眼睛望着我问道。
于是我就给她说唱机是个啥子东西,唱片又是啥子模样。
“你们城里人的名堂硬是多,晓得那么多东西!”二妹子一脸十分羡慕的神情惊奇的望着我。水灵灵的大眼睛,红扑扑的脸蛋,长长的黑辫子,好可爱!